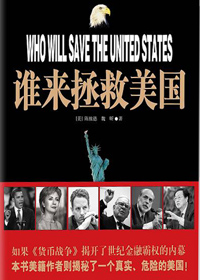拯救与逍遥(出书版)-第51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但是,上帝的国在福音书中并非遥远得不可企及的天堂,而是基督的身位那样近在咫尺。基督的上帝倾身惠顾人类的不幸处境,通过基督的受苦亲临人类的卑下。“永生”不是“永恒”,永生的含义是在上帝国中的重生,“永恒”却是一个宇宙论的概念。①伊凡、乔依斯、加缪都把“永生”与“永恒”搞混了。为什么会搞混?关键在于无视基督。理性的上帝是没有基督的上帝,在理性的上帝面前,人的自由意志才变得尖硬而脆弱。
圣经说过,上帝创造人的时候,并没有赋予他自由意志,因为上帝知道人承受不起善与恶的选择。理性的灵魂被说成人性的尊严和价值所在,是启蒙理性主义说的,不是圣经说的。相反,圣经说人的自由意志是人偷吃知识树果子的结果,善由此成为人的自愿行为,同时,人的恶也是出于自愿,而不是外力所迫。人自己离弃了上帝,只有靠人营构的知识来担当善与恶的生命抉择,因而善恶抉择也是由人的自由意志来决定的。
①参汉斯?昆:《论永生》1983年版。
但理性的人即使有了知识,最终发现自己承负不起善恶抉择,于是就把这一困窘归咎于理性的上帝。永恒福祉本来是上帝与人的原初关系,如今成了人追寻的永远消退着的福祉,人的关涉善恶抉择的自由意志成了追寻永不可企达的永恒的支点。
人的自由意志本来就企达不了永恒福祉,人背离上几帝以后,永恒福祉就成了上帝通过基督事件白白给人的恩典。如今,自由意志在伊鲍里特一类人那里反倒成了拒绝上帝的依据。由于启蒙理性把基督事件判为神话传说的虚构,就消除了自由意志的卑下与上帝的卑下(基督)的必然关联,人的自由意志的卑下就变得孤苦零丁了。
这就是卡夫卡的处境。当梅思金认同了伊鲍里特的基督最终没有战胜自然法则的感觉,他身上的卑下就失去了基督的卑下,陷入“瘫痪无力和绝望的状态”。卡夫卡的作品几乎不再提到基督是偶然的吗?梅思金失去基督,就成了卡夫卡。由于自由意志的怯弱,由于心灵对恶极为敏感,上帝国就有如永远无法企达的神秘城堡,卡夫卡便成了双重意义上的苦役犯:既不能依据自由意志去创造自由的生活,又无法摆脱世界的恶,生命成了无法承受的没有尽头的过程。
《诉讼》的德文原文是Prozess,即“过程”之意。这已经点明了主题:一场没有终结、没有指望的追寻存在透明性的过程就是人卑下的自由意志的真实处境。
罪的含义本来是神义性的,既表明人脆弱、欠缺的天性,又表明人背离了神圣天父的庇护。人一旦失去了基督这一中保,罪仍在人身上,却得不到说明,人想靠自己的自由意志抹去自己身负的罪,结果总是因此陷入恶。
如果把《诉讼》看作一场法律上的罪过及其澄清过程,或个人与庞大官僚机构周旋,就根本搞错了。作为一位表现主义作家,卡夫卡始终通过象征和隐喻来思索。在他那里,象征和隐喻已从一种言词的修辞功能扩展为整个叙事结构,日常的与神性的既径渭分明,也水乳交融。在(诉讼》中,法律的诉讼过程与宗教平性的澄清过程叠合为一个符号,其全部秘密在结局的前一章(在大教堂)充分显示出来。
约瑟夫?K与乔依斯的斯蒂芬有同样的感受。人的存在被“先验地”判了罪(如果没有神义的规定,斯蒂芬沉迷于肉欲不是自然而然的?),由于自由意志的卑下,山于失去了上帝的卑下(基督);上帝的世界成了一个理性王国,有如一个宗教法庭。约瑟夫?K的整个生活都在宗教审判的阴影下喘息,到处都有法官的影子,法院的神秘存在与供人悔罪的教堂毗邻,而“大教堂的面积真是大得出奇,似乎已经到了人类可以忍受的限度”。①K没有耐性,不得不打破教堂的宁静,卑下的自由意志促使他无意留在这里。如果我们还记得梅思金经历的令其瘫痪的感觉,记得阿辽沙的信念惊恐和最终走向人间,K的意愿就不难理解了。感觉已成熟为思想,卑下的自由意志要自寻人的正常生活。K作出决断:设法摆脱这件案子,让它就此永远了结,过不再受案子困扰的自由生活。
①卡夫卡:《诉讼》,外国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214页(以下随文注页码)。
法的大门只对K一个人开放,因为只有他才想了结这场诉讼,想得到没有任何困扰的自由。反过来说更清楚,只有失去了上帝的卑下而又不能吞下恶的事实的人,才会有这样的生命感觉,生命成了需要摆脱的诉讼。
对于能吞下恶的事实的人,要得到没有困扰的自由,并非一定要进法的大门。跨越一条界线就可以了。上帝给人的自由意志规定的界线,也就是伊凡、斯塔夫罗金的自由意志跨越了的界线。卡夫卡迈过这一界线,梅思金就会返回拉斯柯尔尼科夫的立场,阿辽沙就会站到伊凡的立场。基于恶的事实,要跨越这一界线不难理解。当神父说,对守门人的每一句话不必承认都是真的,只需把这一切当作必然来接受时,K不得不提出抗议:这是一个可悲的结论,因为守门人的受骗对他自己没有什么危害,但对乡下人却危害极大,因为这是把谎言变成了普遍原则。由于失去了基督中保,K只有求诸于自救,自己澄清自己的无辜,尽管这样一来K可能只有坦然存下恶的事实。
K向神父告辞,他不得不走了。他如何走呢?
K紧挨着神父,在黑暗中,他连方向都辨不清。他手中拿着的那盏小灯早已熄灭。一个银色的直立圣像的光泽在他面前闪了一下,立刻又消失在黑暗中。K为了让自己不至于完全指靠神父,便问道:“现在我们是不是来到大门附近了?”“不是”,神父说,“我们离大门远着呢。你想要走了吗?”虽然K正好当时并没有想到要走,他却马上说:是的,我得走了。……“好吧”;神父一边说,一边向K伸出手来,“那你就走吧”。“不过我一个人在黑暗中认不出路来,”K说。“左转弯靠墙走”。神父说,“然后沿着墙一直朝前走,干万不要离开墙,这样你就可以找到大门了”。伸父才离开他几步,K就高声嚷了起来:“请你等一等!”“我等着呢”,神父说。“你对我还有什么要求吗?”K问。“没有什么要求”,神父说。“你刚才对我真好”;K说,“你向我解释了很多道理,可是现在却好像没有什么关系似的就让我走了”。“可你一定要走嘛”,神父说:“噢,是的”;K说,“你要知道,这是出于无奈”。(《诉讼》,页230)
这就是卡夫卡的处境,或者说梅思金和阿辽沙的结局:在黑暗中没有基督的光就辨不清方向;但神父主动伸出了手。基督圣像本身发光,K看不见而已,他心里的那种“瘫痪无力和绝望的感觉”使他感觉不到光。K离开教堂出于无奈,而无奈的出走仍然需要神父的指引,界线终于没有跨越,尽管也是出于无奈。K像狗一样被杀死时,他仍然眷念那“一束从法的大门里射出来的永不熄灭的光线”。
他的目光落在采石场边上的那幢房子的最高一层。好像有灯光在闪动,一扇窗子突然打开了,有一个人模模糊糊出现在那么远、那么高的地方,猛然探出身来,双臂远远伸出窗外:那是谁?是个朋友?是个好人?是个同情者?是个乐善好施者?是单独一个人呢?还是所有的人全在?还会有人来帮忙吗?是不是以前被遗忘了的论点又有人提了出来?当然,这样的论点肯定有。逻辑虽然是不可动摇的,可是它无法抗拒一个希望继续活下去的人。他从来没有看到过的法官究竟在哪里?他从来没有进去过的高级法院又究竟在哪里了(《诉讼》,页236237)
希望竟是以这样一种令人绝望的形式透显出来。K怎么不死得理直气壮一些?为什么不像伊鲍里特那样去死,或者像基里洛夫、里厄医生那样,反抗像狗一样被人杀死?清醒的逻辑告诫人们,为了生存的权利。宁要恶的事实,也不要模模糊糊的希望,不是才合乎人的自由意志和理性?K张开手指,举起双手,让屠刀在自己的心窝里转两转,不是侮辱了生命的至高权利?
八
现在,该来看看曹雪芹的“新人”形象的结局了。
绕了一大段弯路才进入这问题,绝非写作手法的精心安排,而是所关涉的问题本身的要求。曹雪芹的新人重新回到“石头”,世界,问题随之又来了:这位新人本来就想要走出石头世界,返回石头世界出于迫不得已,在石头世界中呆下去决不会舒畅。是否还有希望挪开这块石头?曹雪芹的新人已经尝试过给无情的世界补情,由于石头心的缘故,补情归于失败。如果挪开大荒山的石头,又该用什么来填充世界的根基?这些问题可能想得太远了些,至少,挪开这块石头的希望毕竟值得尝试一下。
挪开这块石头的艰难尝试可以这样进行:一个人用自己全部生命的力量把石头顶起来,让后来的精神从石头缝隙中穿过去。如果真的有人这样尝试了,顶起石头的英雄会不会被石头的压力扭曲、甚至被同化为石头、被石头性吞噬?如果这位英雄自己肩起石头是以化为石头为代价,否则就没有力量肩起石头,人们从他身下匍伏而过会不会被石化呢?即便这位英雄肩起了石头,人们进入新的天地仍会以石头为路标,那么,他所指引的新的天地是否仍然是一个石头世界?既然这位英雄是靠自己的自由意志肩起石头,他的牺牲会给后来的人们带来新的生命品质?
这些担忧可能都是多余的顾虑。毕竟,历史上有多少人有勇气和毅力肩起石头?能肩起石头已经堪称伟大。
令人惊喜的是,中国精神史上出现了这位肩起石头的英雄:曹雪芹新人形象的补情精神真的发展为肩起石头的硬骨头精神。像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笔下人物历史地现身为现世的人一样,曹雪芹笔下的人物也历史地现身为现世的英雄,他就是在青年时代立下“我以我血荐轩辕”的夙志的鲁迅,直到现在,他依然是我们的精神旗手。
……觉醒的人……各自解放了自己的孩子,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孩子们——引者]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坟?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
与西方精神史一样,中国精神史上有大才华的诗人代不乏人,然而,能身为一种精神风范的诗人总是极少数,屈指可数,甚至好几代风流人物过去了,也难遇见一位这样的诗人。在中国精神史上,能身为精神风范的诗人,屈原、陶渊明、苏东坡、曹雪芹之后,可能非鲁迅莫属。2O世纪留下大量作品的诗人不在少数,又有谁能像鲁迅那样竖立起一种精神?
这是一种什么精神?
鲁迅首先是一个觉醒的人,甚至他的仿徨、苦闷、阴冷,都是觉醒的表达,在他看来,历史要求他有这样一双觉醒的冷眼。“觉醒”在这里意味着什么呢?“觉醒”都是针对蒙蔽而言的,曹雪芹的新人最后不是“觉醒”了吗?鲁迅觉醒的冷眼正是曹雪芹新人形象的结局,也是鲁迅使命的开端。鲁迅传承了曹雪芹新人的使命,只是使命在此已由为无情的世界补情转变为把无情的石头肩起来。鲁迅与曹雪芹的新人在气质上具有共同的基础,曹雪芹的新人在红楼情案终了时已经变成石头,石头做成了鲁迅的骨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