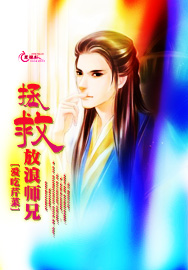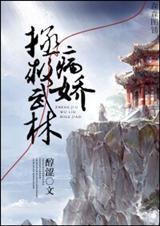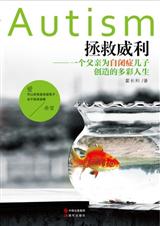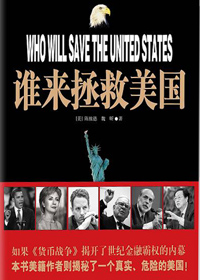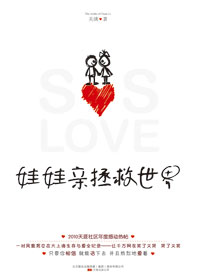拯救与逍遥(出书版)-第36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解脱无需再以解救为前提,是因为个体心性确立起来的绝对根据是超世间的绝对无我之空:无我无欲心则休息,自然清净而得解脱,是曰“空”。这个心性的“本来面目”没有任何宗教价值的规定,行为没有当与不当、善良与险恶的区别,北宗的“诸恶莫作”、“诸善奉行”的规定变得毫无意义。这不就是“自性清静”勾销佛陀身位的结果?印证真妄的个体本心是否确实禀有佛祖传下的本心,已经不再是一种“教”的规定,这种规定完全没有必要了:“平常心是道”。佛陀的大慈悲行动针对现世中的一切无用性,疾病、死亡、冷漠、伪善、腐化、欺骗的救恩,也一同被“自性清静”勾销。吹捧禅宗对宗教性之世俗化的改造,把勾销宗教形态视为伟大创举的人(诸如铃本大拙)真的有佛家情怀、佛家的大智慧?
更奇妙的是,一些以为凡西洋的好东西中国都有的学者把维特根斯坦与禅宗扯在一起。①据说维特根斯坦学说与禅宗都倡导超越语言,两者的高明可以相互印证。这种肤浅的拉扯实在轻率得可怕。
维特根斯坦的“不可说”神秘与禅宗的“第一义”毫无共同之处。首先,维特根斯坦划清语言的界限,是要限制自然科学知识(可说的)侵入宗教信仰,“哲学的正确方法实际有如下述:除去可以说的(即自然科学的命题)之外,什么也不要说”(《逻辑哲学论》,6。53)。这里所谓的“可说”,指经验世界的事实。“关于哲学问题的大多数命题和问题不是错误的,而是无意义的。因此我们根本不能回答这类问题,而只能确定其无意义。哲学家的大多数问题和命题都来自我们不理解我们的语言逻辑”(《逻辑哲学论》,3。325)。所谓“不可说”,只是表明涉及伦理、审美、宗教的事情,不可用自然科学式的知识说,而非这些价值形态没有意义,宗教、伦理、审美的事情必须以属己的方式说(显示)。所以,维特根斯坦称基尔克果为伟大的哲学家,高度重视托尔斯泰、特拉克尔、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言说,自己也大谈福音。②相反,禅宗的“不立文字”一开始就把剃刀指向宗教、伦理的言说,它要清除的根本不是自然科学知识对宗教、伦理意义的侵害,甚至根本就没有面临过这类问题。“不立文字”清除的恰好是维特根斯坦要守护的价值关切。禅宗把印度佛学中的宗教思虑清除得干干净净(这就是伟大的中国化)、把对世界意义的关怀消除得干干净净,宗教性的无所渭意义反而成了有意义。
①参冯友兰:《新理学在哲学中之地位及其方法》,见《三松堂学术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546页;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03页;李一哲:《禅学阐微》,台湾文史哲出版杜,第174页。
②参维特根斯坦:《文化和价值》,华中科技咨询公司1984年版,第40-49页。
宗教和伦理问题,不能靠理性思辨解决。印度佛学的思辨虽然烦琐,最终意图仍然是取消理性思辨,以便把宗教的生命感觉接纳进来。禅宗勾销印度佛学宗教的理性思辨,不仅抹去佛学思辨的“表诠”,而且以“遮诠”为口实,把任何现世意义的思虑清除干净,非宗教性的无虑取代了佛学的宗教性思虑。丧失了宗教性思虑,还谈什么超越?
据说,维特根斯坦与禅宗对不可言的本体有一种共同的关怀和兴趣。即便说禅宗的性空是一种本体,但是什么性质的?“犹如虚空,无有边畔”(《坛经?般若品第二》):“不生憎爱,亦无取舍,不念利益、成坏等事,安静闲恬,虚触澹泊”(《景得传灯录》卷五,《慧能传》)。如果这也能称之为宗教性本体,难道可与维持根斯坦所关切的本体同日而语?对于维特根斯坦,本体是超越的意义世界,上帝是其标志:“上帝和生命目的?我知道,这就是世界。……生命的意义,也就是说,世界的意义,我们可以称之为上帝。上帝的符号可以作为一位父与我们联系起来”。①如此本体难道与性空为本的本体是一码事?
①维特根斯坦:《1914-1916笔记》,1906年版,第165页。
上帝是超验的意义,生命和世界只有从上帝那里才能获得自身的意义(禅宗的“自性”恰恰引不出任何意义),有限的个体必须关切生命的意义、世界的意义、自我的意义以及意志自由和死亡,也就是必须面对现世的恶。“相信上帝意味着,对世界的事实还不能漠然置之,相信上帝意味着,生命有意义”(维特根斯坦:《1914-1916笔记》,前揭,页167)。这种宗教关切与禅宗的“自性”关切有一致之处?难道面对现世的恶竟与“自性清净”、“犹如虚空”有一致之处?“禅通并妙用担水及砍柴”(庞居士偈)难道与“Das Gebet ist der Gedanke an den sinn des le bens”(析祷就是思索生命的意义)有相同的意义?这两种追求生命的透明性的方式可以相互印证?“不离烦恼”、“不出魔界”的规定,要求“事无逆顺,随缘即应,不留胸中”;“宿习浓厚,不加排遣,自尔轻微”;”凭风浪起”、“心如古井”。对于维特根斯坦,所谓“不朽”意味着,人面对现世的恶负有甚至不能用死来解脱的责任;所谓上帝的信仰意味着,人应意识到自己的罪,恶是罪的结果,只有上帝能承负。①禅士何曾有过维特根斯坦那样的对人类责任“锐利甚至痛苦的敏感”?维特根斯坦何曾哪怕一次宣称过对恶的世界应该无所住心?解脱与解救真的没有宗教意义上的根本差异?解脱和解救所引导出的生命感觉真的没有本质差别?难道解脱之超越(所谓“入圣超凡”)不会是一种伪超越?禅宗不仅“不思善、不思恶”,而且彻底破坏精神语言的明晰性,尤其要模糊询问宗教真实的语言的明晰性,抹杀任何区分和限定,在“非思量”中“难得糊涂”。相反,维特根斯坦首先要求澄清语言的混乱,尤其询问价值真实的语言的混乱,以便更清楚地思考应该如何生活。
①参马尔康姆,《回忆维特根斯坦》,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61页。
研究哲学如果给你的只不过是使你能够似是而非地谈论一些深奥的逻辑之类的问题,不能改善你关于日常生活中重要问题的思考,不能使你使用危险的词句时比任何一个……记者都更为谨慎(这种人为了自己的目的使用这种词句),习哲学有什么用?……如果要对或者力求对你的生活和别人的生活进行真正诚实的思考,就还要困难得多。麻烦在于思考这些事清并不紧张激动,倒常常令人不快。既然明显令人不快,就是最重要的。(马尔康姆:《回忆维特根斯坦》,前揭,页33)
难道维特根斯坦不该对世界的冷酷、残忍、邪恶以及人类深深的绝望怀有深切的关切?他应该像禅师那样把世界“空”尽,在”空境”中消闲于“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无门关》)?
道家的“安时而处顺,哀乐不能入”精神还过禅宗把佛学的宗教情怀践踏得不能再糟了。就算所谓庄禅精神高明得不能再高明,是否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破对待、空物我、泯主客、齐生死、反认知、重解悟、亲自然、寻超脱”的所谓审美精神比在现世恶的苦涩和烦恼中关切人类可怕处境的宗教精神更高明?①在一个恶无法消除的不幸世界中,“审美”的逍遥难道是问心无愧的?“庄禅精神”对荒唐、浑浊、冷酷、不幸的世界的变相肯定还需要发扬光大?所谓印度佛教的“中国化”真的了不起了庄禅式的“审美”态度究竟要把世界的恶强化到什么地步才安心呢?
①据说,“慷慨成仁易,从弃就义难”,因而审美式的视死如归高于宗教式的殉难(参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前揭,第215页)。其实,庄禅精神对死亡的态度根本就不涉及“义”,为“义”而死已不是庄禅精神。所谓庄禅式“从容就义”的说法根本就自相矛盾;再说,耶稣在十字架上殉难并非慷概,而是苦楚,审美式的“如归”高于“宗教式的殉难”从何说起?
四
再来看禅宗消解道家“适意”意志的后果。适意演进为禅意,意的意向性比境象更为“空灵”。安闲恬适、天然淡泊,据说构成了中国诗歌精神的重要特色。其实,通过把所有直观对象无化,不依恋任何现象的形式和精神的内容,仅靠淡泊无我的意向来构拟“鸟鸣珠箔,群花自落”,“寂而常照,照而常寂”的禅境,中国诗歌精神恰恰因丧失在世生命的内在热情而萎缩甚至枯寂了。
禅境作为无边畔的虚空,首先、且根本是一种生命感觉、生活方式、生存状态,所谓诗歌、艺术的境界论其实是一种生存论,任何美学上的探究其实都不着边际。与禅境直接相关的是禅心,要能领悟禅境首先得有禅心。如今道友信所看到的,禅心决不是人世间受苦的“自然的自我”,而是“逍遥的自我”。逍遥的自我不会觉醒,是被根本虚无所无化了的自我,要得悟禅境,岂不是首先要虚无化我的自我?虚无化的自我没有在世热情,没有在世热情,哪来诗?
禅意使得“意”的意向性境象更为空寂,无异于使道家的“适意”心更为空寂。如此空寂引导出什么意识后果?这种后果与曹雪芹的诗人使命有什么关联?
禅心与道家的“得意’”一样,必须由能够排除现世恶的关切意志来维持,因而,“无所住心”要求心体具有非同寻常的超强意志。“天然凑泊”要求的解脱一切界限和差异必须靠禅定的观照来达成,禅定与其说针对外在自然,不如说针对内在意志。只有先“空”去内在意志,才能禀得禅心:“天地可谓大矣,而不能置于虑空之外,虚空可谓无尽也,而不能置于吾心之外,故曰:以心观物,物无大小”(《长松茹退》)。于是,人的内在意志非得要“空”掉。
庄子要求破对待、黜聪明,虽然也重“吾丧我”,但更重视在内在视界中抹去现世牵缠(荣辱、祸福、死生、利害),“得意”的追求充分证实了这一目的。禅宗既然把“空”主体化,就更要求破除内在意态中的执,抹去“得意”的执。这样一来,对超常意志的要求更高了。禅宗的参禅、机锋、捧打就足磨炼破除“总”执的意志,如二程所说,天下之人唯是禅客最忙,念念是遁,镇日提心吊胆,放松不得。①
这种为破除“意”执而强化的意志因得与任何感性内蕴(道家所重的自然之“情”)断绝于系必然是枯寂的。所谓“担水砍柴”,正意味着在烦细的日常生活中也不能忘记枯寂感性内蕴枯寂的意志被禅宗泛化、日常化了。只要个体在现世时间的每一刹那都不离枯寂意志,刹那就是永恒(这与基督教精神在感清动荡的爱中感得至福大异其趣)。将陶渊明与王维稍加对照就能够体会出,禅诗比道家气象的诗更为冷寂、清虚。禅诗与其说充满禅味,不如说充满弹理,是打扫心地之后心如枯并的写照:“雁过深潭,影沉寒水,雁绝遗踪之意,水无留影之心”熊十力对这段禅偈解释说,雁过潭沉影,殊无意于遗踪,潭水澄清,亦无心于留影,此只见得所过者化,却不悟所存者神。儒佛之辩证在于此。②确实,儒家的热衷肠意志转化成道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