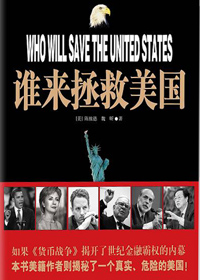拯救与逍遥(出书版)-第34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为了对神明的挚爱
我尊敬民众的声音。那么宁静
——因为它的虔诚
可是,为了神祗也为了人,
但愿它不要太醉心于沉静。
为唤醒沉睡需要有诗人虔敬祈告,祈祷才会守护圣灵的话语。荷尔德林把“祈告”视为诗的使命,“祈告”通过诗更新语言。“作为飘泊者的荷尔德林懂得,要在自由的田野里饮到清纯的水,就得靠近源泉”(伯塔克斯:《荷尔德林》,前揭,第345页)。荷尔德林追究命名、赠物、大亨、神性的含义,追问语言的本源,像一个漫游者深入到事物的源头。①荷尔德林在隐居中成为诗人后勇敢地突进到人迹罕至的境地,忍受历史中严重时刻的压力。
①这种从词源着手更新语言对海德格尔有很大影响,与“言不尽意”、“得意忘言”在体道意图上刚好相反。
置身于上帝的风暴中是我们的义务,
你们,诗人啦!以敞开的生命置身其中,
亲手捕捉那雷电中的闪光,
在歌声之中,慈父般地
把神明的赠品传递给民众。
作为诗人,荷尔德林“恨沉醉像恨严寒”,不能容忍无所住心的冷静。诗人应“热爱诸神并且热切地想到世人”!只有虔敬的人、心中有圣灵的人才能成为诗人。“不喜亦不惧”因而不知祈祷的灵魂不能成为精神冒险的诗人。荷尔德林在致友人的信中写到:
我的心渴望着在月光下与人、与物结为姐妹。我几乎相信,我实在是出于纯粹的爱才迂腐不堪。我并不胆怯,因为我害怕现实摧残我的情怀。然而,我确实胆怯,因为我害怕现实摧残我热忱的关注,因为我正是靠这种关注来与别的什么事情取得联系;我担心我内心中热忱的生命会被冰冷的日常生活冷却。①
①荷尔德林:《致诺伊裴尔》,见《西方文艺理论名著选编》,上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荷尔德林的忧心与陶渊明的忧心不是判然有别?两位诗人对现实的畏惧不是判然有别?一个要守护“热忱的关注”;“纯粹的爱”,一个要“去情无累”,不喜不惧;一个害怕心的寒冷,一个渴望寒冷。这两位大诗人要返回的本源呈现为截然不同的境界:陶渊明要返回无形无迹、无知无情的原始自然本体,返回混沌未开的本然性自然;荷尔德林要返回浸透着爱的温柔的神性本源,返回神灵光照的超自然性家园。
这种本质差异也体现在对大自然的热爱上。陶渊明崇尚天地人和合的自然,在那里,和谐和宁静是植物性的。荷尔德林崇尚有神灵居住和出没的自然,在那里,和谐和宁静都透显出神圣的温馨。自然的宁静和恬美的本质中有超自然性的爱:
沙沙的森林的和音,
陶冶过我
我在万花丛中
懂得了去爱。
在一个没有神圣尺规的大自然中,人真的会彻底摆脱恶的追逐而得安宁?连尼采也不相信这一点。
荷尔德林和陶渊明的不同去向突出了这样一个问题:隐遁生活是否必然得否弃历史时间中的生命感觉?是否必然是”恬然鼓腹”、“从欲为欢”?在陶渊明看来,否弃历史时间中的生命感觉合乎天意,这没有错,因为“天意”没有爱;在荷尔德林看来情形恰恰相反,也没有什么不好理解,因为这位诗人的上帝在爱的行动中显身。问题在于,如果因为世界的恶而否弃只能在历史时间中显身的爱的生命感觉,是否值得而且应该?正因为这个世界的恶是世界的基本要素,因而也是这个世界及其在其中有自己的自然生命的人无从规避的,人才需要祈求上帝,才需要在历史时间中靠上帝的救恩把人的生命感觉转变成爱,为爱受苦。道家的天意与基督的天意怎么会是一体的两面?
无可怀疑,陶渊明在隐逸中得到了解脱,生命找到了恬然自乐。但可以问,石头心肠真的有乐?是什么样的乐?对于陶渊明一类的诗人,这样的问题没有意义,恬然自乐已经超越了这类问题。
荷尔德林的隐遁走在精神分裂的边缘,进入了承负世界的恶的痛苦,在隐遁中追寻神性的圣爱:
他,作为神明的喉舌,
须及时遁匿。
这位诗人不可能恬然自乐,否则无异于承认现世恶的绝对力量,意味着人将过牡蛎一般的生活。人只能在上帝的爱中才能摆脱恶的纠缠:
挚爱永在!
大地恒移,
天穹常驻。
三 走出劫难的世界与返回恶的深渊
在这个地球上,我们确实只能带着痛苦的心情去爱,只能在苦难中去爱!我们不能用别的方式去爱,也不知道还有其它方式的爱。为了爱,我甘愿忍受苦难。我希望,我渴望流着眼泪只亲吻我离开的那个地球,我不愿,也不肯在另一个地球上死而复生!
——陀思妥耶夫斯基
无我原非你,从他不解伊,肆行无疑凭来去,茫茫著甚悲愁喜?纷纷说甚亲疏密?从前碌碌却因何?到如今,回头试想真无趣。
——曹雪芹
一
由于独特的际遇,曹雪芹的《红楼梦》有难以说尽的意味。中国古典文学史上,据说《红楼梦》独占“最高峰”,但自胡适、俞平伯提出《红楼梦》的残稿问题以来,追寻八十回以后的残梦,成了“红学”的主要支撑。本来就是一部谶书的《红楼梦》,因后三十回佚失而更为令人难以索解。①然而,根本问题仍然是:《红楼梦》的世界究竟是什么样的,如此令人情之所钟?
①关于《红楼梦》佚禹稿及其相关研究,梁明智《被迷大的世界:红楼梦佚话》,北岳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
我打算来讨论的,并非”红学”中的探佚派与百二十回本辩护派论争的问题。即使俞平伯晚年反悔与胡适“腰斩”红楼,承认程高续梦有功,仍然无法回避这样一个问题:程、高的意图不是曹雪芹的意图。但反过来,即使撇开程、高的续梦,仅据前八十回及脂评中的佚稿痕迹,曹雪芹的红楼世界究竟是怎样的,并非就不成其为一个问题。探佚派想要尽力搞清这一问题,似已命中注定离不开索隐。带着曹雪芹家族身世的历史故事走进“红楼”世界,领略其中三味,却不一定碰触到“红楼”事件涉及的思想史上真实的问题。
我要问的是:曹雪芹为什么带着深切的悲情走进“红楼”世界?究竟是一种什么生命感觉使得曹雪芹要构想这个价界?这个世界构想所展示的精神过程是如何发生的?
《红楼梦》必须作为中国精神史上的重大事件来看待,真正的探佚应该是带着精神史问题的索隐。相当明显的是:道家思想所确立的生命感觉给人带来的心智和情怀,再次成为中国诗人精神抉择上的困难。这一困难深深隐藏在曹雪芹展开红楼世界的精神过程之中。如果不是这样,“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至多成了一个家族兴衰的苦涩的内心表白:曹雪芹动用所有中国精神遗产来尝试的巨大努力,难道没有关涉到中国诗人的精神索质的重大问题?自屈原、陶渊明到曹雪芹,中国诗人的精神意识己有了一千多年的历史。到曹雪芹时,这一精神的历史进程为中国诗人的精神意识带来了什么样的突破?在曹雪芹那里,精神的生命感觉有没有遗留下一些问题要求他去解决?曹雪芹的精神结构,已经在苏东坡身上呈现出来了,但在苏东坡那里,这一作为生命感觉的精神结构仅仅在形成,在曹雪芹那里却是在毁灭。这一毁灭过程难道不值得“索隐”?
面临世界的恶,陶渊明寻求的出路是:放弃价值关切,以换取个我灵魂的安泰和清虚的石头世界。中国诗人能否在这个无情的石头世界中适性得意呢?也许,陶渊明在适性得意中有难言的无聊?
放弃历史时间中的生命感觉并非诗人的初衷,况且,清寂的世界是否能给人安慰,本身就可疑。诗人从恶的现实世界走向清寂的世界,又从清寂的世界返回现实世界,不少中国诗人一再重返儒家信念。陶渊明长期得不到后世诗人重视,说明什么?
问题并不在于历史始终是一个恶的场所,历史的现实构成与人的价值愿望始终存在着难以解决的分裂。问题关键在于,诗人应以什么样的精神意向对待这种普遍分裂。普遍分裂问题相当程度上可以说是天地间的个人无法解决的。然而恰恰诗人不能否弃解决普遍分裂的意愿,否则,诗人的写作是什么意思?
对于普遍分裂问题,道家和佛家严格说来都有“算了”心态,尽管这种心态依然可能成为一种精湛艰深的精神。大乘佛学要求菩萨在进入真如境界之前重返恶的现实,对劫难世界中的芸芸生灵有深切的关怀,如此大宏大愿,也不过要把人救渡到一个许诺解脱一切的真如之境。在佛学那里,最终的价值根据是圆成实性之空,是彻底的人生解脱。佛学通过深切的价值关怀使人进入彻底解脱的存在状态,道家精神何尝不是如此?与此不同,基督教精神并不知道有一个可以解脱一切的终极处境。耶稣的“大宏大愿”以不惜承受世间恶的爱把人领回到神圣者手中,而神圣者的救恩并没有解脱一切。基督教是爱的宗教,圣爱因承负恶而沉重,是救赎、而非解脱的爱。这就是为什么基尔克果说,无论世界荒诞残忍、还是阳光明媚,上帝就是爱。曹雪芹的精神意向中既没有大乘佛教的大宏大愿,也没有沾染过基督情怀,但也没有道家的“算了”心态。的确,《红楼梦》叙事几乎在一开场就唱出“好了歌”。士隐对“好了歌”注解说:“乱烘烘你方唱罢我登场,反认他乡是故乡;甚荒唐,到头来都是为他人作嫁衣裳”。但曹雪芹毕竟带人们到他乡走了一遭。红楼世界的展开本身就表明了这样一种生命感觉:人生无从解脱。这一感觉在庄禅精神中出现,还不算精神事件?
个人意志的确是自由的(有的人执意选择解脱的清虚而非救赎的沉浊,尤论如何,总之作出了精神选择。在有的哲人看来,解脱与救赎都是相对的;没有什么绝对的价值真实,选择什么都是合理的。对这种“算了”哲人来说,不是他自己对绝对的真实既聋又瞎,而是绝对的真实对他既聋又瞎。显然,任何哲学和宗教都无法左右人的精神气质的偶然构成。不过,我们还是可以循着价值现象学的道路追问一番,看着这些精神气质各自会遇到什么样的内在困难。这就是曹雪芹的“红楼”,世界能成其为一个问题的人类精神史背景。
二
道家信念给出一个“心如死灰”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个体必得领受清虚的孤寂。儒家的“热衷肠”倏突转换为“心如死灰”的石头心肠,无论如何过于唐突。何况,儒家的“热衷”意志消融到哪里去了?人的意志能量有“守恒原则”,如心理能量不灭,只能转换、不能压抑和消除,否则,必然导致心理性精神疾病。儒家的“热衷”意志遭到阻抑后,进入道家的清虚冷寂,究竟在何处安置自身?
为了让“热衷肠”意志变得“心如死灰”,道家发明了坐忘、无我、淡泊……这些毕竟都是消极办法。个体精神在清虚孤寂的自然时间中要得到心灵的安适,还需要积极的游心于意、即个体心智的适意游戏。“人生贵得适意”,成为个体精神作清虚孤寂的自然时间中安身立命的精神功夫。
在道家那里,所谓“意”既是一种精神感觉的意向性,又是一种大生命的“象”境。精神感觉(意、神)与外在自然的境界(象、境)的叠合,的确可谓“言有尽而意无穷”。“意”被看作最高的精神感觉:“可以言论者,物之粗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