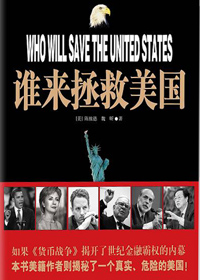拯救与逍遥(出书版)-第27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乐感与爱感的生命感觉差异极大,的确不可通融,在两者之间作出价值评判,应留给每一个人的心灵感受。需要澄清的是,爱感并不排除快乐,它本身就是快乐。只是,这种乐不是自怡其乐的乐,而是置身在上帝恩典的温柔之中的乐,严格地说,不是快乐,而是欢乐,有如神性节日中与上帝共在时的乐。在节日欢乐中,每一个体都把自己交付给节日的共在,其中的乐乃是相互领承的共感、共享的喜悦、爱与被爱的激流。爱感的乐就是圣灵降临的节日般的欢乐,就是每一个人把自己交付给圣爱的欢乐,是人人分享圣爱、以爱相触的欢乐。
乐感之乐是自然性的,不具有这种节日的性质,以个体生命为绝对中心收摄宇宙自然;所谓“天人合一”之乐(孔子的“童子二、三人”亦即自然,他们也是“我”的快乐的中介)都基于个我生命的快乐,没有上帝亲身参与的欢聚。无论乐感具有何等神秘、玄远的审美意义,只要世界仍然处于恶的裂伤之中,用卡夫卡的说法,只要受难仍然是“这个世界和积极因素之间的唯一联系”;审美主义的乐最终都得面对现世之恶。
五
现在回到诗人们的存在判断。
前面已经提到,中西诗人的逍遥和发疯都是一场“人的觉悟”,或者说对人世的荒唐和残酷觉悟的结果;由于文化精神的意向结构不同,这场觉悟的性质也不同。
在近代西方,莎士比亚笔下人物的精神分裂,据说是后来的西方诗人(而非笔下人物)精神分裂的先导。哈姆莱特疯了,因为他第一次以人的眼睛(而非上帝的眼睛)看到世界的混乱:李尔王疯了,同样因为他第一次以人的眼睛看到世界的荒唐。这两个人都说过许多“疯话”,但对这个世界来说,疯话却最为真实,爱德加——一个靠装疯来持守正义的人评论李尔说:“虽然他发疯了,他说出来的话却不是个无意义的”(莎士比亚:《李尔王》,前揭,页248)。
在哈姆莱特眼中,世界是一座庞大的牢狱,里面有许多囚室,地牢只有对于那些以为世界上根本就没有善恶可言的人,这个世界才不是牢狱。李尔感到,世上的罪恶都镀上了金,公道的枪刺戳在上面也会折断。区分善恶的人成了这个世界的因犯、没有伴侣的零落者;他的眼晴被当作灌园的水壶,去浇洒秋天的泥土。哈姆莱特和李尔口径一致地指控这个使残酷得不到说明的世界:
这个覆盖众生的创穹,这一顶壮丽的帐幕,这个金黄色的火球点缀着的庄严的屋宇,只是一大堆污浊的瘴气的集合。①
当我佗生下地来的时候,我们因为来到了这个全是些傻瓜的广大的舞台之上,所以禁不住放声大哭。(《李尔王》,前揭,页249)
①莎士比亚:《哈姆莱特》。人民文学出版社l977年版,第52页。
哈姆莱特和李尔在这场觉醒中领悟到什么?人性的邪恶、肮脏和怯弱。哈姆莱特对人类再也没有兴趣,人就是肮脏的尘土。根本没有高贵可言,“不过是画上的图形,无知的禽兽”,连美德也不能熏陶人的邪恶本性,哈姆莱特甚至对自己作为一个人也感到厌恶:
我自己还不算是一个顶坏的人;可是我可以指出我的许多过失,一个人有了那些过失,他的母亲还是不要生下他来的好,我很骄傲,有仇必报,富于野心,我的罪恶是那么多,连我的思想也容纳不下,我的想象也不能给它们形象,甚至干我都没有充分的时间可以把它们实行出来。像我这样的家伙,匍匐于天地之间,有什么用处?我们都是些十足的坏人:一个也不要相信我们。(《哈姆莱特》,前揭,页70)
这种对人的厌恶的感觉,李尔也有:
葛罗斯特:啊!让我吻一吻那只手!
李尔:让我先把它揩干净;它上面有一股热烘烘的人气。(《李尔王》,前揭,页247)
无论哈姆莱特还是李尔,在指控这个残忍、荒唐的世界,揭露人虚假的高贵时,都没有假借传统神学的教义。在此之前,在中世纪,世界的冥暗和人的邪恶,都是从上帝与人的关系的意义上来讲的。人背叛上帝而沉沦于恶,世界的冥暗是由于人的罪的沦落所致。但在哈姆莱特和李尔眼里,人之恶纯粹由于人的天性之恶,而不是由于人背离上帝;换言之,人性之恶是自然的,而非背离上帝后的非自然的恶。
哈姆莱特和李尔都经历过人本主义精神的洗礼,都曾相信过人性的伟大和尊严、善良和理智。而且,就是现在,这两个人也没有接受上帝的神性秩序和人的坠落说。“事实上李尔嘲笑一切基督教神学;嘲笑宇宙起源说与历史的合理说;嘲笑诸神、善良的自然与按神的形象所创造的人”。①本来,当人的眼光摆脱了上帝的目光,就会看到人性的高贵、尊荣、伟大。经过人本主义精神的洗礼,应该赞颂人性才对,怎么会变得对人性如此厌恶?
①扬?柯特:《李尔王·最后一局》,见《莎士比亚评论汇编》,下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42页。
事情还得从但丁说起。但丁在神性的面纱下偷偷开启了人的双眼。在这双眼里,人的高贵超过了天使,虽然天使的高贵是神性的,但人应该赞美自己的人性而不是神性。①古人的使命乃是学会自己使自己不朽,而不是靠上帝使自己不朽。随之,世俗的荣誉和幸福成了人性的最高理想,尘世的享乐成了人追求的最高价值,人的自然需求取代了对上帝的祈求。彼特拉充宣称:“我不想变成上帝,或者居住在永恒中,或者把天地抱在怀里。属于人的那份光荣对我就够了。这是我所祈求的一切,我自己是凡人,我只要求凡人的幸福”。②
①参但丁:《飨宴篇》,第四篇,第十九章,引自《从文艺复兴到十九世纪资产阶级文学家、艺术家论人性沦、人道主义言论选》,北京大学西语系编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6年版(以下简称《人道主义言论选》)。
②参彼特拉克:《秘密》,转引自《人道主义言论选》,前揭。
尽管提出了”凡人”的诉求,这种人本主义的诉求却是在神本精神背景上产生出来的,所有人的愿望都显得是从前上帝的天使的愿望,在人本立场身后总有上帝国的影子。然而,在两种国度之间的紧张及其差异性中,现世的受苦可以得到说明。如今,人本主义摆脱上帝的国,在发现“凡人”的幸福时却找不到理由来说明人世的受苦,人于是成为世界的荒唐面目。
在文艺复兴时代的诗人看来,上帝的位置是多余的。达·芬奇声称,人而非上帝才是这个世界的原型。人所拥有的一切自然本性的权利都是正当的,尤其值得赞颂人的激情和快乐。即便人的疯狂也是人性的伟大天赋。在上帝国的背景下产生出来的人本主义似乎比没有这一背景的人本主义更极端地推衍人的自然本性。然而,文艺复兴的人本主义的寻欢作乐背后隐藏着人在得不到说明的世界荒谬性中的深切悲哀和无奈。爱拉斯谟以人的理由质问上帝:“神明在上,请他们告诉我,如果没有欢乐,也就是说没右疯狂来调剂,生活中哪时哪刻不是悲哀、烦闷、不愉快、无聊、不可忍受的?”①世界上所有的欢乐、幸福、安逸,都是人没有上帝之后直接面对自然性残酷的补偿,而这种补偿又恰恰是自然性残酷的要素。
这是人的觉悟吗?是的。但什么样的觉悟?仅仅将文艺复兴人本主义精神看成对上帝的反叛,从上帝的怀抱中挣脱出来,用人的双眼取代了上帝的双眼,恐怕过于近视了。这双人性的眼睛真正看到的,不是人没有上帝后的人间美景,而是人性的渺小、卑鄙、脆弱和兽性。与其说人本主义的觉悟是对人性的赞美,不如说是对人性的诅咒。蒙田这样挖苦人自以为宇宙主人的荒唐相:
①爱拉斯谟;《疯狂颂》,转引自《人道主义言论选》,前揭。
现在让我们单独来看看人本身吧,看着这个没有任何外来援助的人吧。……这个不仅不能掌握自己,而且遭受万物摆弄的可怜而渺小的生物自称是宇宙约主人和至尊,难道能想象出比这更可笑的事情?其实,人连宇宙的分毫也不能认识,遑论支配和控制宇亩,人自以为有权说自己是世界上唯一能认识宇宙大厦的美及其组成部分的生物,认为只有自己才有权对宇宙大厦的建筑者表示感谢,只有他才能计算世上事物的消长。这种特权到底是谁敕封给他的?叫他把敕封这个高位重责的委任状拿出来看看吧。
这样的委任状是否只良颁发给圣贤呢?这样的委任状很少烦发给一般人。疯子和恶人难道还配得上这种殊恩?他们是世界上最坏的人,难道比其余的生物更配得上这种殊恩?①
离开上帝之后,可怜的人没有什么品质值得夸耀自持,没有能力从上帝那里窃取自己欠缺的东西,人类应该承认自己长期以来探索的结果,无非是学会了认识自己的愚蠢,认识到人身上存在着与生俱来的恶。
莎士比亚的人本主义就是这样一种诅咒人性的人本主义:
衣不蔽体的不幸的人们,无论你们在什么地方,都得忍受着这样无情的暴风雨的袭击,你们的头上没有片瓦遮身,你们的腹中饥肠雷动,你们的衣服千疮百孔,怎么抵挡得了这样的气候呢?(《李尔王),页214)
如果人仅有泥土的本性还算不了什么,问题是人有比兽性更为可怖的恶性。在这个世界之中,任何可能有的生存目的都是琐碎而无意义的;世界仅是无聊的舞台还不至少太糟,但它还是死亡的供品,使人沉醉于欲焰中自己焚烧自己。人生只是围绕着自然性的激情转,而大自然造出激情纯粹为了作弄人。
①蒙田:《散文集》,转引自《人道主义言论选》,前揭。
这种人本主义精神引发出巨大的虚无感和荒唐感。人的伟大敌不过蛆虫,生存就像尘土一样随时可能被时间吹走,善在死亡面前显得支离破碎。即便如此,人还不能说自己是最不幸的,当人能够说“这是最不幸的”时,根本就还不是不幸,人们至多可以像葛罗斯特那样悲叹:“毁灭了的生命!这一个广大的世界有一天也会像这样零落得只剩一堆残迹”(《李尔王》,页47)。那些认识到这个世界的丑恶的人如果不被挖去眼睛,不幸的人类如何活下去呢?一旦听有人在恶的世界中都成了瞎子,就只能靠疯子把被挖去眼睛的人从绝望的境地解救出来,但疯子只能对他说:“祝福您的可爱的眼睛,它们在流血哩”(《李尔王》,页232}。
西方诗人这场“人的觉醒”的真正内涵,并非我们长期以为的那样,是什么离开上帝后的欢乐颂、人性战胜神性的凯歌,而是对人的本性及世界的恶的意识以及对恶无法作出说明,找不到力量来克制的无措感。形而上学的神性秩序被勾消后,人的本性及世界的恶才得不到说明,但勾消传统的神义论不正因为人不再相信形而上学的神性秩序?
人本主义的“人的觉醒”看来是一个悖谬的谜。一方面,人认识到人世的恶和生存世界的荒唐;另一方面,人又无从何解释人世的恶和生存的荒唐,,这种尴尬处境使得发疯和自杀都成为人的福份:“还是疯了的好;那样我可以不再想到我的不幸,让一切痛苦在昏乱的幻想之中忘记了自己的存在”(《李尔王》,前揭,页252)。于是,自杀成了脱离这个世界、摆脱人自身的恶的出路。
可是,既然人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