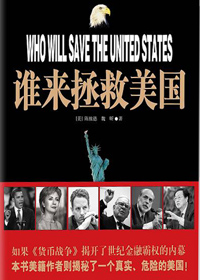拯救与逍遥(出书版)-第13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八
“人活着可以接受荒诞,但人不能生活在荒诞之中”。②同样,诗人活着可以接受绝望感,甚至可以说,绝望感是一种确证,排除盲目、偏狭、迷拜和无意义的牺牲,赖此确立真实的信仰。但诗人不能生活在绝望感中,更不能因为绝望为诗人提供了一种直观的地平线而抬高它的意义,正如不能因为痛苦或许使人接近上帝的真理,就把它说成是上帝的真理本身。如果不是在绝望的同时力图消除绝望感,在痛苦的同时祈求抹去痛苦的创痕,生命就没有出路。
①海德格尔:《诗人何为?》,见《林中路》, l957年版,第249页。
②马尔罗:《人的状况》,参柳鸣九,罗新章编,《马尔罗研究》,漓江出版杜l984年版,第287页。
“人总得有条出路呀!”(陀思妥耶夫斯基语)
自古以来,诗人有两类:要么在世界虚无的原初本相中坚守神圣的信念,要么在这种本相中狂饮生命的醇酒。只有前一类诗人才会有出路问题。一旦神圣的信念出了问题,坚守的诗人就会自杀或发疯,再不然就用伪造的神圣信念杀人。用精神的书写也可以杀人,种种骗人的诗语也是暴力,用诗歌或艺术赞美甚至炫耀放纵、担当荒诞,不就在歼灭人的情怀?要人们欢迎牺牲和不幸,抬高命运的暖昧意义,蔑视哭泣的眼泪,肯定世界的冥顽、轻蔑心灵的柔弱,不就在强化现世的荒唐?
既不发疯或自杀,也不标榜绝望是一种新美德,就只有沉溺:沉溺于自己的清醒、精明、看得透彻,沉溺于生欲的狂热——时间狂、享受狂、知识狂,过度的感性欲求,无止境的冒险……坚守神圣信念的诗人与沉溺于病态生命的诗人的冲突,就是拯救与逍遥的冲突。这一人类精神的基本冲突从古自今没有消弥。
问题是,如今上帝死了,基督不再值得信赖;孔孟庄周己是封建余毒,释迦牟尼成了历史文物,只有历史的必然规律对正在流血流泪的心提出的要求是绝对真实。人能靠沉溺于生命的病相过活?诗人自杀已经把这一问题提得太尖锐,而沉溺诗人从来就只为自己沉溺而活,见惯荒唐、鲜血和眼泪无所住心,对坚守的诗人以自己的生命提出的问题置之不理。
据说,诗的沉溺也是一种反抗,以碎片般的境界和怪异夸张的形式来攻击生活中的荒唐,把世界切碎以抗议荒诞,不再理睬神圣价值。波德莱尔的“恶之花”所表达的波希米亚式世界观鄙弃现存的道德原则,其理由是,接受任何非由自己创造的价值就是不诚实。自此以后,“恶之花”成为现代诗的原则,着总破坏有意义的内容,希求通过表达破碎世界的形式来取得某种意义,抵抗生活中意义的毁灭。19世纪以来,艺术形式的变换远远超过二千年来艺术形式变换的总和。只有形式才是唯一的意义所在,只有在形式的结构中,人的存在才不至于变为失去了回忆能力的零碎断片,也只有在形式的仪式中,人才感到居住在完整之中。
如果生活世界的本相就是破碎、荒诞、无聊,而今诗人把诗变成破碎、荒诞、无聊的形式本身,怎么会成了对破碎世界的诗化反抗?形式本身可以使生命有意义,可以使世界中无数个别事件有意义,仍然是审美主义的自我幻想。审美自救论的前提是:只要我的生命活过就有意义,而世界作为整体的意义则无关紧要,因为世界作为整体本来就没有意义。现代的沉溺诗人的审美幻想是:明明自己随同世界的沉沦一起坠落,却自己认为在反抗。在古代,艺术形式与某种确定的世界意义维系在一起。艺术形式使偶然的事件成为一个意义的整体,把人带入一个意义的世界。现代艺术的形式不再提供、确立某种意义的福祉,而是提供一个荒诞的世界。如果连诗的自为形式的意义都没有,诗的形式就是世界的零碎、荒唐、无聊本身,诗人还剩下些什么呢?
再说,没有形式能力的人怎么办?本来,他们可以指望在诗的形式所确立和固定下来的意义世界中找到安慰的场所,如今只能从现实的废墟进入诗的废墟,灵魂仍然得不到安宁。
凡没有担当起在世界的黑夜中追问终极价值的诗人,都称不上贫困时代中真正的诗人。
对终极价值的信念,基于对任何时候都与人类生活有关的两个基本问题的考虑;我们在其中生活的世界应该是什么,世界的命运亦即这个世界中我和我的同类的命运应该是怎样的。中西方历史上古典时代的哲人和宗教人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多少有效地支撑了诗人们对世界的信念,如今,古典的信念遭到致命的摧毁:“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不仅欧洲到了日薄西山之时,地球上所有文化均已处在暮霭沉沉之中。人类的末日,任何一个民放和任何一个个人均不能逃脱的一次重新铸造——不论毁灭还是新生——已经被人们顶感到了”(雅斯贝尔斯:《论历史的意义》,前揭,页41)。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时刻,沉醉诗人的歌声再次成为难以抗拒的诱惑。
如果拒绝沉溺,就面临着这样的抉择:要么摸索出与传统信念完全下同的新信念,要么反省历史中的传统信念、审察时代自身的境况,修复古典的精神信念的基础。
确信能提出新的信念,必须有一个不可或缺的前提:提供新信念的人确实具有创造新信念的能力。近代以来,无数哲人和宗教人会试过了,结果怎样?新信念如果不是终归回到古老的信念,末了都撞上荒诞的墙。
尼采否弃形而上学的上帝,终结了古典形而上学,但他所找到的新信念依然是古希腊狄奥尼索斯的信念。永恒回归的信念(所有事物无条件的、无限的重复循环)仍是形而上学式的观念。加缪跨入荒诞精神,终于呆不下去,只好返回所谓“南方思想”(la pensee de midi)的地中海精神,回复到以中庸、节制和生命的欢愉为原则的斯多亚信念去了。
萨特决意留在荒诞之中,拒绝返回古典信念,持守人的希望与世界的冷漠之间的鸿沟。于是,萨特不相信世界的虚无,就没有力量,不成为虚无,就无法生活。古老的神谕、上帝的恩典、现实的神意结构都在干着贬低人的勾当。据说,人的伟大就在于人的精神敢于拒绝神圣天父的救恩,敢于成为荒诞的人。萨特的虚无哲学既拒绝接受世界的理性结构,也拒绝为世界提供神意绪构的上帝信念,只要求人领受自己在失去什么和继续在失去什么,要求把人性的绝望当作自由来体验,把荒诞担当起来。正如萨特在剧本《无出路》中宣称的,他的出路就在于敢说“无出路”。
荒诞人成了诗人的英雄和楷模,尽管他在任何地方都找不到与自身和世界的生存联系,无论发生什么对他都无所谓,没有意义:实存的虚无才最真实,才是形而上学的基点。萨特这样的诗人只得把实存的虚无变成一曲自由颂歌:既然存在是绝对虚无,人也就拥有绝对自由;能自由行动就有意义,行动本身就是价值。诗人教导说,只要人们从虚无中成为自己,即使成为恶徒,或不断制造流血,吸毒、神经症,也有意义,因为人在自由中毕竟选择了自己。灵魂中一无所有的人可以投身到任何行为中去,没有什么需要牵挂。况且,他可以为自己的任何行为后果负责,因为实际上他无需负任何责。在实际生活中,诗人成了政治投机份子有什么好奇怪。
除了荒诞诗人,又有多少人能够担当荒唐、背负虚无前行?那需要一种什么样的邪恶心智?内心中没有丝毫生存意义的感觉,没有信仰、祈求和爱意,有意义的生活怎么可能?担当荒诞必不可少的冷漠除了会给本来就冷漠的世界增添冷漠,还能增添什么?
荒诞的信念证明,现代哲人和诗人都没有成熟到有能力为世界提供新信念。
思想必得通过对古典信仰的审察来重新确立寻求真实可靠的信仰的方向,不仅因为荒诞主义失败了,还因为思想在今天无法彻底抛弃传统。在今天,没有哪位诗人能不仰仗古典语言就想发挥出自己独特的天赋。即便沉溺于世界的病相的诗人也无法置身于古典的审美信念之外,无论是否了解这个传统,是否有意识地对待它,还是自以为正在重新开始,都无法切断与传统审美信念的历史血脉。在信仰问题上,现代人没有资格和能力自信高于古人。
九
既然我们是从现代困境意识来考察传统信念,就不可能是考据文物的“考古”;而是站在时代的深渊中与古典信念对话,使寻求真实信仰成为可能。即将进行的这场价值现象学的追问,是通过论析中西方诗人的古典信念传统及其现代演化来展开的。将进入精神冲突域的古典信念有:儒家的道德历史哲学、道家和禅宗的超脱主义、古希腊和近现代的理性哲学、基督教的救赎思想以及现代的虚无主义哲学。①
如果按在世态度来分类,可以把上述种种信念体系分为三种不同的类型:对世界的道德形而上学态度,对世界的宗教解救态度,对世界的审美超脱态度。
古典儒家的道德历史哲学与西方的古典形而上学信念很不相同,理论前提和借以推导的精神原则差异很大,但就以道德形而上学态度来看待世界而言,却大致同趣。鲜明而突出地与中西方的道德形而上学对立的在世态度是犹太-基督教的救赎信念和道家、禅宗的超脱信念。这是两条判然有别的解救之路:拯救与逍遥。这两条不同的在世态度远比道德形而上学的在世态度更多地体现在诗的意识之中,因此有理由把“拯救”与“逍遥”作为这场精神冲突的基本话题。我们将会看到,现代的虚无主义信念不过是超脱信念的延伸。
①我没有把印度佛学包括在内,因为与我的论题不相干,但我当然会涉及儒道化的禅宗思想。
道德形而上学、审美超脱和宗教解救这三种对世界的基本态度可以更为简洁地表述为对世界的接受和不接受态度。信念的基本问题涉及到个人与人类的关系,人面对自己的生存处境应该采取什么态度。这就是所谓的在世态度问题。宗教解救和审美超脱者都拒绝道德形而上学的接受世界的态度,但在如何拒世的问题上,两者之间则出现了拯救与逍遥的深刻分歧。
无论儒家还是希腊的道德形而上学,对世界都采取适度的接受态度。在道德形而上学看来,世界本质上是合理的,它体现了天道或自然秩序。世界之中有一个确实的可以信赖的道德秩序,人生只要从属于这个秩序就有意义。儒家倡导天人合一的基本信念,肯定人在现世道德的宗法秩序中成圣成乐的可能性;苏格拉底以理性的道德知识为真实的生活世界不可或缺的基础,生活的一切重要领域都依赖于人的道德理性。凭靠隐含着自我批判的道德理性认识,人就能够超越直接经验的偶然,寻求到世界的善的目的。善的宇宙理念使亚里士多德发现了用于处理人生历史中的偶然的道德理性,依靠这种理性知识,人就具有了克服生命欠缺的力量。
道德形而上学确立了道德理性这个不可穷尽的可能性的主体,以及赖以实现自身的中介(社会的道德实践或科学的知性认识)。从而,在道德形而上学眼中,人类处境并非是令人绝望的,人们无需祈求一个亲临存在深渊的上帝。人类凭靠自己的道德知识的力量,通过理性认识和社会伦理实践(修、齐、治、平)就会达到现实的完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