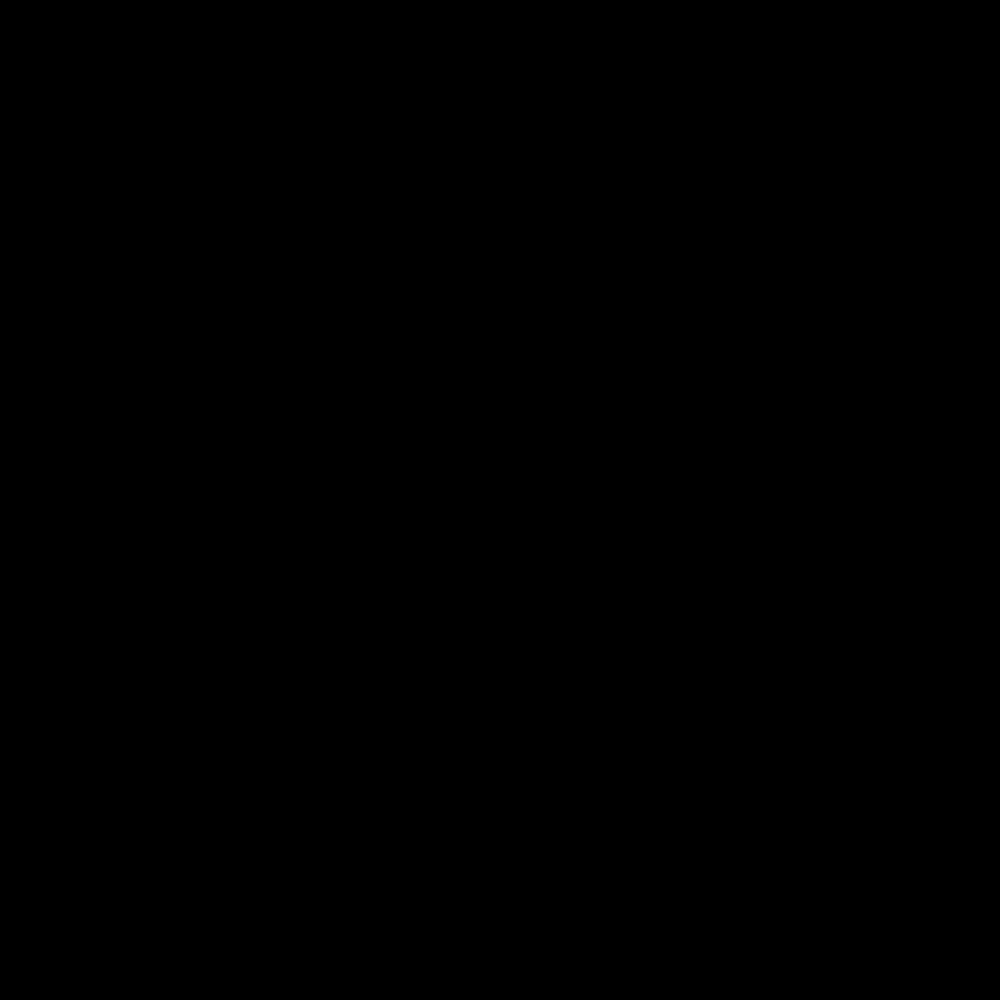风之冬樱-第35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后来,当我醒来的时候,才发现自己不知道什么时候被人给推到了住院部的一个双人病房。
旁边的床上躺着断了腿的海龟兄,他的腿打着石膏高高吊着,那模样要多拉风有多拉风。
由于他老人家挽救了我岌岌可危的经济状况,我对他当时心生好感,不由得多了几分亲近之意。
路晓枫没了惊慌失措的神情。
对着刚从地狱门口爬回来的病人,她拉着一张冰川脸装无情,看得我心头一阵赞叹——看看,啥叫艳若桃李,啥叫冷若冰霜?老板娘,你好样的!
海龟兄虚弱地躺在床上,轻声问:“晓枫,这些年,你过得好么?”
啧啧,这句开场白真是俗不可耐!海龟兄,你果然是出国出成奥特曼了,《追妞十八式》没读过?
看来,国内的这块市场尚属空白啊!如果我出一本这样的书,应该会受到广大青壮年男士朋友的欢迎吧?
如果弄成中英双语的话,那搞不好都可以卖到幼儿园去。现在有多少父母妄想自己 初级阶段的孩子可以讲一口流利的鸟语啊!《追妞十八式》本来就是小朋友们的兴趣,还满足了家长们虚荣心方面的要求,两个层次的消费群体情绪我都照顾到了,想不赚钱都难!
就在我的如意算盘打得梆梆响的时候,路晓枫同学开口了,眯缝着眼睛、竖着耳朵、装昏睡之衰相、行偷听之苟且的我立刻捕捉到更多的信息——
“别说得好像你和我很熟似的,万一被你太太知道了,那可不大好!”
哈!路晓枫,你这是典型的投石问路!嗯嗯,记下来,记下来!将来放在《追妞十八式》里做个典型案例,详细介绍下应对这种腹黑妞的武功心法。
“晓枫,我现在还是单身一个人!你是不是还在怪我当年突然出国留学?我那时也是被家里逼得,迫不得已!可我不是跟你说了,让你等我?后来我回国找你,却到处都没有你的消息,你——你是不是嫁人了?”
哇!海龟兄!人可以无耻,但是怎么可以无耻到这个地步?青春是女人最宝贵的资产之一,尤其是像路晓枫那样漂亮的女人!你给了多少青春补偿费?凭什么让人家苦苦守候一只远隔重洋的海龟啊?
“让我等你?我怎么等?”路晓枫的语气一下子激动无比,嗓音也哽咽起来:“就算我能等!我的肚子也等不了!”
天啊!这么猛的料!我安详的闭上眼睛,耳朵张的大大的,身体一动都不敢动,不管谁看到老身准保都得以为那是某位领袖被保存在xx格勒水晶棺内的遗体。
我没料到海龟兄的智商居然跟老身也有得一拼,只听他立刻抓住了路女侠话中的重点,穷追猛打:“晓枫,你是说——你怀孕了?”
我真恨不能替路女侠点头。你丫的!自己干的好事还要问别人啊?
“晓枫!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如果我知道是那样的情况,就算被人打死,我都不会离开你!”
切!我要是路晓枫的爸妈,你当年绝对会是一具面目全非的男碎尸然后被推进海里喂龟,你哪还有游过大洋彼岸装海龟的可能?
“现在说什么都没用了,孩子已经不见了!但是,费材,如果你还有人性的话,请你帮我找到我们的孩子!”路晓枫说话的语气里蕴含着一股难言的辛酸。
要不是娃他爹的名字叫“废材”那么搞笑,我都差点问声落泪、暴露行踪,再惨遭灭口。
废柴大人果然如我所料,拍胸脯打包票:“晓枫,你放心,我绝对会把孩子找回来!然后我们一家三口永远都不会再分开!”
床那边传来肉体撞击的声音。
嗯,我满意的在心里点点头——肯定是路晓枫再也无法继续COS冰山,直接扑进了废柴大人的怀抱。哇,有情人终成眷属耶!鼓掌!
过了好久,就在我浑身发痒挺得难受的时候,那边又传来低低的声音:“晓枫,我们的孩子——是男孩,还是女孩?”
嗯嗯,老身也想问这个问题很久了,铜球铜球!
一个带着哭腔的女声传来:“我不知道。当年刚生完孩子,我爸妈就把孩子给抱走了!那么多年来,他们始终不肯告诉我孩子到底被送到哪去了。孩子长得什么样子,身高多少,叫什么名字,男孩女孩,甚至是活着还是死了——我都不知道。”
苍天啊!那你还找个P啊?海里捞针都比你家孩子好捞!
废柴大人想必跟我是一样的感受,他的声音里也带上浓浓的泪意:“那你这些年就一直这么毫无线索地在找我们的孩子?晓枫!真是苦了你了!”
那边传来一阵**的声响,想必那个伤心的母亲在点头:“我爸妈恨死那个孩子了,他们一直到临终都不肯对我透露半句。后来终于被我查到我父母在那年曾来过苍霞,我就搬来这里开店,一边工作一边继续找人。跟我们孩子同一天生日的孩子情况,我都调查过了,他们都有生身父母的详细证明,呜呜呜,他们都不是我们的孩子——”
废柴大人灵机一动:“别急,晓枫!我们的孩子也有可能像我一样,血型是RH阴性AB型,如果从这点入手,一定会好找得多!”
路晓枫回过神来:“对啊!刚才那个大夫也说——医疗系统里有这种血型的人的登记情况,如果我们从这儿入手,一定找得到!不过。。。。。。费材,我以前居然都不知道你的血型这么怪!”
废柴海龟大人很会安抚女人:“晓枫,当年我们相处的时间实在是太少了!不过,这件事情就交给我吧,我在国内也认识不少很有能力的朋友,相信一定会有办法的。”
您就吹吧,废柴大人!男人在哄女人上床前都是这个样子!你们忘了?刚才那个。。。。。。3。。。。。。。3%还说过——很多小城市的人群信息都没在那个系统里,那得有多少漏网之鱼啊?譬如说我,嘿嘿,如果你们的孩子是我,你们不就找不到?
想到这里,我蓦地灵光一现!
“啊!”我猛地坐起身,彻底忘记了装昏。
床那边的两个人别我的叫声吓了一大跳,海龟兄的石膏腿都在空中甩了两甩。
我飞快的跳下床——
我怎么没想到这个?天啊,我还笑人家是废柴!我自己才是真的废柴!人家想得到用这个法子去找孩子,我怎么想不到用这个去找爸爸?
爸爸!我突然觉得你离我不再遥远了!现在的你可能不过是医疗数据库里的几个字符,可是,在不久的未来,你就会是个活生生站在我眼前的人了!
白芷他爸,等着我,阿芷我来啦!
看着惊恐地抱作一团的苦命鸳鸯,我堆出一脸笑容,谦卑又谄媚的问道:
“尊敬的老板以及美丽的老板娘,请问您们在数据库里搜索令公子的时候,能不能顺手也帮忙搜搜我老爸?”
风之冬樱 Autumn 42 开往布拉格的列车
清朗的声音穿越了千山万水从听筒中传来,我听得心中一热,眼里也有层薄雾渐渐浮起。
想想自己真是没有出息,孔达不过是离开我一个月而已,何至于如此?且不说他每个星期都会用手机给我打个国际长途,就是想想郑眉和安蓝那两盏不怎么省油的灯居然都老老实实地留在了英国,我也应该把悬着的心放下。
看看空荡荡的饭店大厅,用力咬咬下唇,竭力克制住越来越不听人控制的情绪,我攥着电话线将身体倚在吧台边上,故作镇定地开口询问:“那边的天气如何?”
听得出来,现在他的唇角也一定勾起了一个温暖的笑容:“维也纳的气候很好,自然环境也美,街上行人步履从容,整个城市都洋溢着一股优雅、恬淡的味道。多瑙河畔汇聚了很多独创一格的街头音乐家,听到他们的演奏,我深受启发,这个城市不愧于它”音乐之都“的称号,的确让人流连忘返。与伦敦、巴黎、以及罗马相比,我更喜欢维也纳。我有预感,这个星期会是我本次欧洲之行最值得珍惜的一段时光。一想到表演结束后就要离开这个城市,心里还真是有些舍不得。”
我的口气略显慌乱,手指也将打着卷的电话线给拽成了直线:“喂,你这家伙,可不要乐不思蜀啊!”
他噗嗤一乐,坦然道:“在金色大厅独奏是我一直以来的计划,但这并不是我的终极目标。。。。。。”
我叹了口气,插嘴道:“我知道,你的梦想是和维也纳爱乐乐团合作表演协奏曲!”
静默了一会儿,他柔声道:“阿芷,我以为自己已经表现的很明显了,但是按现在的情况来看,我以后要时时提醒自己——说话做事都要照顾到你的智商水准!”
我翻翻眼皮,大大咧咧的说:“这位天才少年,你直接笑我笨就得啦,不需要将一个字就可以讲明的意思表达的那么深奥婉转!”
他果然笑出声来。过了一会儿,他蓦地想起一事:“对了,还没问你,伯父的事情调查的怎么样了?陆老板和费先生有没有什么进展?”
我郁闷的点点头,用手撸一下被梳成马尾辫的光滑的长发:“嗯,老板娘的事情有些眉目了——费先生在数据库里搜索到一个与他们孩子年纪很相仿的男孩的资料。那孩子的养父养母过世以后,他被送到了省城的一家孤儿院,高中毕了业就到外地去工作,跟孤儿院基本处于失联状态。费先生带着老板娘今天一大早就飞去省城找孤儿院的负责人了,说不定现在已经一家团圆、抱头痛哭了。”
孔达体贴的安慰我:“你别着急,我看老板娘为人很有些侠气,即使她这次找到了自己的孩子,也不会对你撒手不管的。再说了,即使她不管,我也会帮你一起寻找的——对了,以前听你说伯父当年是去了布拉格的音乐学院进修钢琴演奏?他的名字叫徐谪?”
明知道远在地球彼端的他看不见,我还是点了点头:“是叫徐谪!他去了那里没几个月就跟我妈彻底失去了联络,我妈用过各种办法找他,可惜都是石沉大海。现在只能寄希望于他已经回国,否则世界那么大,我可不知道他到底会躲在地球的哪个角落。”
孔达沉吟了一会儿:“你妈在苍霞等了伯父那么多年没搬过家,如果他真的回了国,总会回家看一眼的吧?”
我的心脏开始砰砰乱跳,讲话的声音里也带上了一抹浓重的鼻音:“你是在暗示——他已经不在了?”
听出我的慌乱,孔达匆忙改口道:“不是,我只是按照常理推测,但是你也知道,这个世界上也有很多不合常理的事情。”
我用左手盖住话筒再使劲抽抽鼻子,仰起头后才将盖住话筒的手移开:“你不用安慰我,其实我也早想过这个可能性。我妈那么好,他没道理抛弃我妈那样的人——除非,他出了事情。不过,都过去那么多年了,我早就习惯了没有他的生活。生也好,死也好,或是变了心另外成了家也无所谓,我不过是想帮我妈弄个明白——这么多年了,他到底为什么不回来?”
孔达的口气里带了些许无奈的情绪:“阿芷,我理解你的心情,不过你还是别太执着了,人生里有很多事都是没办法强求的。更何况,你妈妈都已经——”
我一眼瞄到吧台墙上的挂钟,猛然插口道:“哎呀,国际长途漫游费那么贵,你快点挂电话吧,我也要工作了,白白,白白。”
没等那边接话,我直接挂断了电话,然后抬起满是疤痕的指背抹去眼角不小心溢出的一点泪滴。
不知道为什么,这通电话打得我很是伤感,也许是因为孔达远在异乡,也许是勾起了我多年来对父亲的执念,可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