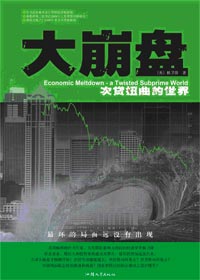平凡的世界(三)-第67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部下边的路边上。锣鼓唢呐立刻响成一片,秧歌队在田五的带领下手舞足蹈,应声而起。
我们看见,第一个从小车中走出的是年轻的县委书记武惠良——他去年就从黄原来这里
上任了。乡县有关部门的领导都纷纷走下车来。新成立的黄原电视台的几位记者一下车,就
扛着摄像机乱跑着忙开了。
在乡县领导中我们熟悉的人有:县乡镇企业局局长徐治功——该同志双水村的老百姓也
很熟悉;本乡乡长刘根民,副乡长杨高虎。其他还有县宣传部、教育局、人大政协文教组的
负责人。本来县长周文龙也想来——我们知道,他曾专门为少安的砖场点过火——但因有
会,没能起程。
金俊武、孙少安等人迎上去和上面的领导握手问候。紧接着,由秧歌队在前面引路,这
些领导被热情的双水村迎过了东拉河,迎过了庙坪和哭咽河。小学门口的孩子们立刻挥动花
束,一边跳跃,一边齐喊欢迎的口号,与秧歌队的锣鼓唢呐混合成一片巨大的喧响声。玉亭
几乎把这场面搞成了迎接外国国家元首……
经过一番必然的纷乱,领导们终于在贺凤英精心布置的主席台上就坐了。俊武是会议主
持人。不用说,男女主角孙少安和贺秀莲也在主席台上。
在庆祝会就要开始之前,主席台上的孙少安突然看见田福堂也来到了人群里。
田福堂是来了。他有勇气在最后一刻出现在这个场所,证明他不愧还是一条好汉!不
过,福堂看起来不象过去那般气势雄伟。他在很大程度上成了一位平凡的农村老人,脸上甚
至带着看开世事的超然和善的笑容。他不是一个人站在人群里。他手里拖着红梅前夫留下的
孩子,背上背着润生和红梅生的女儿。他还给两个小孙子一人做了一个高粱杆皮编的“风葫
芦”玩具。比起往常,福堂的身体看来倒好多了。
孙少安立刻离开座位,穿过人群,走到田福堂面前,拉他到主席台就坐。福堂谦虑而客
气地推让着。懂事的红梅走过来,把两个孩子从公公手里接过去。孙少安硬把前支书拉到主
席台上,并向县委书记作了介绍。受到启发的金俊武也在人群里把金俊山拉到了主席台上。
双水村新旧两任领导历史性地同坐在一起。
接着,庆祝仪式开始了。乡县领导分别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表彰孙少安夫妇劳动致
富后不忘为乡亲们谋福的光荣行为。县教育局还给少安夫妇颁发了一块大玻璃框奖状。
在乡县领导人讲话的时候,孙少安几乎连一个字也没听见。他的目光在人群中搜寻到父
亲。父亲头低倾着。少安猜测,老人家说不定在哭。他在学生娃中间也看见了儿子。红脸蛋
的儿子举一束红艳的鲜花,在笑。哭,笑,都是因为欢乐。哭的人知道而笑的人并不知道,
这欢乐是多少痛苦所换来的……透过这五彩缤纷的场面,他又回到了那似乎并不遥远的过
去;回到他辛酸的童年。他想起他穿着破烂衣裳,和扎着羊角辫的润叶在这同一地方念书的
情景……有人在肩膀上碰了碰他。他回过头,才发现庆祝仪式到了尾声,领导们都朝那块蒙
着红被面的碑石走去;县委书记正含着笑招呼他一同前往。
孙少安在喧腾涌动的人群中站起来,扭过头准备叫妻子,却猛地惊呆了!他看见,刚立
起来的秀莲嘴里鲜血喷涌,身子摇晃着向下倒去!
他大叫一声,发狂地张开双臂抱住了她……我们无比沉痛地获悉,原西县医院对秀莲的
论断结果是:肺癌。
第五十四章
暖洋洋的太阳照耀着都市的大街。公园里和道路旁已经处处绿意朦胧。风中飘着一团团
雪白的杨絮。街心花园的第一批鲜花,也在不知不觉中竞相开放了。古城的春天稍显即逝,
人们立刻就有一种身临初夏的感觉。
街头的行人稠密起来。人们纷纷走出户外,尽情享受阳光和暖风的抚爱。那些时髦的姑
娘已经过早地脱掉了外套,穿起单薄的、色彩鲜艳的毛衣线衣。到处传来春游的孩子们的歌
声。城市一改冬日的灰暗,重新显出了它那多彩的风貌。
孙少平的伤已经完全好了。雷汉义区长代表矿上来为他办出院手续。他准备过几天就返
回大牙湾。
这期间,妹妹兰香和她的男朋友仍然一直给他做工作,让他调到省城来。他到现在还没
有完全拒绝他们的好意。尽管他对自己未来的生活心中有数,但不好当面向他们进一步解释
他的想法。他们应该意识到,他和他们的处境不尽相同。不同生活处境的人应该寻找各自的
归宿。大城市对妹妹和仲平也许是合适的,但他在这里未必能寻找到自己的幸福。他想等以
后适当的时间用另一种方式向他们说明自己的观点和态度。
其实,这期间最使他伤神的倒不是兰香和仲平一再劝他来省城工作。他苦恼的是金秀对
他表示的热烈感情。自从她把那封恋爱信送到他手中,他就一直苦苦思索自己该怎么办?
秀可爱吗?非常可爱!她是那样的热情,漂亮;情感炽热而丰富,一个瞬间给予男人的
东西都要比冷血女人一生给予的还要多。她使他想起了死去的晓霞。她也是大学生,有文
化,有知识,有很好的专业。她无疑会是一个令男人骄傲的妻子。双方感情交流也没什么障
碍,他们从小一块长大,一直以兄妹相待;这种关系如果汇入夫妻生活,那将是十分美好
的。
秀要成为他的妻子?他要成为秀的丈夫?他一时又难以转过这个弯。他一直把秀当小妹
妹看待;在他眼里,她永远是个小孩子,怎么能和她一块过夫妻生活呢?想到这一点,他就
感到别扭。
当然,最重要的是,他和秀的差异太大了。他是一个在井下干活的煤矿工人,而金秀是
大学生,他怎么能和她结婚?秀在信上说她毕业后准备去他所在的矿医院当医生。他相信她
能真诚地做到这一点。但他能忍心让她这样做吗?据兰香一再给他说,按金秀的学习情况,
她完全可以考上研究生。他为什么要耽搁她的前程?如果因为他的关系,让秀来大牙湾煤
矿,实际上等于把她毁了。他现在才记起,他曾给金波也说过这个意思。
所有这一切考虑,不是说没勇气和一个女大学生一块生活。当年田晓霞也是大学生、记
者。但秀和晓霞又不一样。晓霞在总体素质上是另一种类型的女性。虽然他和秀一块长大,
但秀决不会象晓霞那样更深刻地理解他。他和秀之间总有一种隔代之感。
怎么办?这比兰香和仲平要他来大城市工作更难以回答。他知道秀在热切地等待他的回
话。给他交了那封信后,她尽管和往常一样细心而入微地照料他,但他们之间已明显地产生
了一种极不好意思的成份……生活是这样令人感慨不已!
孙少平不由想起十年前他的初恋。他想起了他爱上的第一个女人郝红梅。富有戏剧性的
是,十年前的那场感情纠葛发生在他和顾养民之间;没想到十年后,他又和顾养民纠缠在一
起。不同的是,十年前,郝红梅离他而去爱顾养民;而今天,金秀却要离开顾养民而爱他
了!
生活似乎走了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圆。
但生活又不会以圆的形式结束。生活会一直走向前去!瞧,十年过去了,所有人的生活
都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就拿他们几个说吧,养民已经到上海去读研究生;而前不久他震惊
地获悉,郝红梅带着前夫留下的孩子,竟然和他同村的另一个同学田润生结了婚,现在就生
活在双水村。而他,当了一名干粗活的煤矿工人,现在受了伤,住了院,却被养民爱着的金
秀爱上了……直到现在,他也不知如何与金秀谈这件事。他能感觉来,秀对他的爱是多么强
烈!他不能用简单的三言两语来拒绝她,这样会伤害孩子……是的,孩子。他现在还认为秀
是个孩子!但是,他又不能简单地响应她爱情的呼唤。如果是那样,那伤害的不仅是秀,还
有他自己的心灵。
孙少平左思右想,不知他该怎么办。
想不出个妥当的结果,他就不能轻易对她表示什么。好在他很快就要离开省城;等离开
时,说不定他能对这件事做出结论性的决定……
区长雷汉义帮他结完手续后,他就算和医院告别了。他让区长先回去,他自己还想在省
城逗留几天;他知道,他还有些“事”需要处理。
雷汉义临走时,才迟疑着从衣袋里摸出两份矿上的文件给了他。
孙少平一看,这两份文件都是有关他自己的。一份是通报表彰他舍己救人的献身精神;
另一份是批评他作为班长,元旦那天让喝醉酒的工人下井,违反了规章制度,决定给他记大
过一次。
孙少平把两份文件揉成一团,塞进了自己的衣袋里。雷汉义安慰他说:“不管是表彰,
还是处分,都是些球!回去只管掏咱的炭!”
但孙少平的心情却是沉重的。这是一种永远不能互相抵消的存在,就象他五官正常的脸
上那道丑陋的疤痕。他倒并不特别看重这两份让他哭笑不得的文件,而是由此伤感地想到,
这正好说明了他那负重前行的生存处境。
仲平竭力要求出院后的少平到他家去。但他谢绝了。兰香理解二哥的心情,也没有再坚
持。少平随即住进了一家个体户开办的小旅店。
他住进旅店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给惠英和明明写了一封信,告诉他什么时候回大牙湾煤
矿。
几天之后,在少平即将离开省城的时刻,金秀和兰香相跟着来旅店找他,想陪他出去到
街上转转。但少平推诿着不想去。最少在眼下,他不愿带着脸上的疤痕,和任何女性相跟着
逛大街,他无法忍受陌生人用异样的目光看他和身边两个漂亮的妹妹。说实话,对脸上的那
道疤痕,尽管他显得不在乎,但内心却为此而万般痛苦,爱美之心人人有,更何况,他正当
青春年华!至于他的脸倒究被毁到了何种程度,直到现在他都没有勇气去照镜子。
金秀见他执意不到街上去转,就提议他们三个人一块到她的宿舍去坐坐;她说她们宿舍
实习的同学都没回来,就她一个人。医学院离这儿很近,少平也就同意了。金秀本来不想让
兰香去,但她有口难言。
三个人到医学院金秀的宿舍后,秀特意让少平坐到她床上休息。她让少平先一个人待一
会,自己随即又拉了兰香,到外面去采买吃的——她想好好款待一下少平哥。
兰香和金秀走后,少平一个人没事,就在秀的枕头边拿了几本医学杂志看。他在无意间
发现秀床铺那头的墙上挂一面圆镜子。他犹豫了一下,过去摘下那面镜子。当镜子就要举到
面前的时候,他闭住了眼睛。
他闭着眼,举着镜子,脚步艰难地挪到了靠近房门的空地上。他久久地立着,拿镜子的
那条胳膊抖得象筛糠一般。在这一刻里,孙少平不再是血性男儿,完全成了一个胆怯的懦
夫!
我看到的将会是怎样的一个我?他在心里问自己。你啊!为什么不敢正视自己的不幸
呢?你不愿看见它,难道它就不存在吗?你连看见它的勇气都鼓不起来,你又怎样带着它回
到人们中间去生活?可笑。你这可笑的驼鸟政策!
他睁开了眼睛。呀!他看见,那道可怕的伤疤从额头的发楞起斜劈过右眼角,一直拉过
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