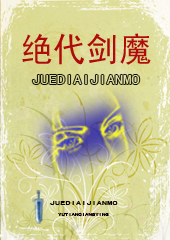施耐庵-绝代奇才-第108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约莫行得五七十步远近,一座刻柱雕檐的楼宇耸在眼前,楼檐下果然悬着块鎏金匾额,上书“齐鲁第一楼”,匾额下斜斜地伸出一竿布招,写着“纯阳酒家”四个大字。
施耐庵也顾不得品评匾额上那龙飞凤舞的字迹,低着头走到柜台前,左右望了望,没见可疑的人物,便将半吊钱一股脑儿搁到柜台上,说了声:“上等好酒,连壶买,不须找零。”
这酒店的掌柜近日来正愁着生意冷落,猛见这人出手如此阔绰,心中自然高兴,连忙拣上等的醇醪满满斟了一壶,连那瓷壶一起递给了施耐庵。
施耐庵接过那壶酒,忙忙地将酒壶揣入怀内,朝柜台上的老板拱一拱手,转身便要出门。
谁知他前脚恰才跨过门槛,猛然觉得两臂一紧,接着便是一阵酸麻,他心叫“不好”,待要挣扎,哪里挣扎得脱?
只听背后一个人“呵呵”大笑道:“俺是六耳猕猴,土行孙也休想从俺‘追风校尉’眼前溜过!你这区区一个穷酸,还想瞒天过海么?”
施耐庵扭头一看,只见面前站着一个军官打扮的汉子,一张国字黄脸,三绺稀疏长髯,细眉细眼,刁长的身形,显得十分麻利精悍。他朝施耐庵冷笑了笑,从他怀中搜出那壶美酒,拔开盖儿,嗅了一嗅,咂咂嘴唇,赞声“好酒”,“咕嘟嘟”灌了一大口,仰头叫道:“将这穷酸押回牢城营!”
施耐庵心中懊丧,自己糊里糊涂中了埋伏,进门之时也该仔细瞧瞧犄角旮旯,如今陷了缧绁,那去梁山泊取白绢的事儿成了泡影,下一步还不知甚么样的折辱在等着自己!唉唉,都是那该死的李黑牛,都是为了他这壶酒!
施耐庵一边叹恨,一边在众衙役的推搡下踉跄而行。
猛听得街口上暴雷般响起一阵怒喊:“直娘贼,还俺的酒来!”
众衙役尚未回过神来,街面上一团黑影夹着狂风着地卷了过来,一个黑大汉浑身脱膊,抡着两把板斧,没头没脑地剁了过来。说时迟,那时快,只见黄影一闪,那军官模样的瘦汉子凌空一跃,早迎着李黑牛的来势立了个门户,厉声斥道:“何方匹夫,休要在俺的辖区撒野!”
李黑牛一腔饥火正无处发泄,见这军官挡在面前,双臂登时抡圆,两柄板斧泼风般剁了过来。
那军官闪得几闪,不觉激得性起,叫一声:“抬过俺的瓜锤来!”立时便有两个衙役奉上一柄鎏铜的八瓣瓜锤,那军官接过来,掂得一掂,迎着李黑牛的板斧便砸!
斧锤相交,只听得“当啷”一声,那军官挡不住黑牛神力,虎口震麻,瓜锤险乎脱手。他叫声不好,疾退了两步,不觉脱口赞了声:“好气力!”
那李黑牛一招得手,呵呵大笑道:“乖儿子,尝到你黑爷爷的厉害了吧!识相的,放了俺相公,还了俺那壶老酒,磕一百个响头,俺放你们这伙鸟人回去!”
那军官笑道:“这秀才是朝廷的钦犯,这壶酒是俺抓人得的利市,有种的,与俺斗三百个回合,俺便一起还你。”李黑牛晃了晃手中的板斧,叫道:“说诳的,今生做乌龟,来世当王八!”
军官闻言大怒,一晃瓜锤扑了上去,与那李黑牛斗了个难解难分。
众衙役也不敢再逗留,押着施耐庵便离了那街口。李黑牛只去斗那军官,也顾不得施耐庵。一行人迤逦行来,也不知过了几道街巷,翻了几道岭坡,足足走了一个时辰,方才到了一个围着高墙深壕的所在。
这里,便是济州府辖下的牢城营。宋代以前,各州关押囚犯的牢城营,一向都设在治所的城廓附近。元人入主中原以后,民族压迫深重,造反的人也甚多,牢狱之中人满为患,朝廷为了防止关押在囹圄之中的囚犯们变成出柙之虎,骚扰通都大邑,便将这各州府的牢城营迁到偏远集镇,这济州牢城营便也设在马庄驿左近。
施耐庵被衙役们押进牢城营,暂寄在签押房内,暗暗为那李黑牛担心,心下想道:黑牛兄弟生性鲁莽,有勇无谋,孤身一人在马庄驿那龙潭虎穴里与人争斗,只怕是凶多吉少!三百个回合此时不知道是否斗完,谁胜谁负,是死是伤,委实叫人揪心!
大约过了两三个时辰,便有狱卒前来提审,跨进牢城营的大门,只见正厅上斧钺刑杖排列得十分整齐,再看正中坐位上端坐着的那个人,不觉惊得呆了。
这官儿不是别人,正是在马庄驿街上见过的那个黄脸黄须的军官!施耐庵暗暗纳罕:自己离开马庄驿时,此人正在与李黑牛赌斗,凭着李黑牛的手段,这军官三百回合之内收拾不下;再说,便是三百回合斗败了黑牛兄弟,马庄驿离牢城营少说也有二十里地,这真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大怪事。
施耐庵正自百思莫解,只听堂上响起一声呵斥:“这穷酸还不跟俺跪下!”
施耐庵冷冷兀立,说道:“晚生无罪,为何要胡乱跪下!”
座上那军官又喝道:“好个大胆的穷酸!俺问你,你可是姓张名学孟?”
施耐庵一听,不由得心中一动:好个糊涂官儿,抓来葫芦顶了瓢,却原来并不知道自己的底细。
那官儿也不等施耐庵回答,朝他丢个眼色,径直往下问道:“去年皇上来菏泽看牡丹,你竟敢偷吃大内的御酒,你可知罪?”
施耐庵越听越糊涂,站在厅上,只是冷笑。
那官儿道:“本该责打你四十杀威棒,只是你尚未经官判罪,暂且记下。”说着,吩咐道:“左右,将这穷酸押进单身号子,严加看管。”说毕,起身退堂。
这一夜,施耐庵久久不能入睡,他想起了那藏在梁山之阴的白绢,想起宋碧云、朱元璋等人的嘱托,心中十分烦闷,不觉披衣坐起。双脚刚要落地,猛见牢房门口人影一闪,接着锁孔里“咔咔”响了一阵,牢门房开了一条缝,轻手轻脚地走进一个人来。
施耐庵正欲发问,只见那人几步奔到床前,“噗”地纳头便拜,口中说道:“施相公,日间多有得罪,万望海涵!”施耐庵连忙双手扶起,睹面一看,不觉惊道:“你?”
站在面前的不是别人,正是在纯阳楼前捉了自己,在街上与李黑牛赌斗,后来又在牢城营里执掌公堂的黄脸军官!
施耐庵见状冷冷问道:“你,你究竟是何人?”
那黄脸军官道:“施相公,此处不是说话的地方,请借个方便的处所讲话。”
说着,他便引着施耐庵出了牢房,回身落了锁。然后领着他曲曲弯弯地走了许久,来到一座黑魆魆的土山前。那军官走近几步,轻轻地拍了拍掌,只听得“吱嘎”一声,那土山上竟然开了扇门,门内隐隐露出灯光。
黄脸军官朝门内一指,说了声:“施相公,请——”
施耐庵见他鬼鬼祟祟,心里头好似揣着个兔子,怦怦乱跳,此时身不由己,只好钻进了那扇门。门内紧接着便是一溜砖砌的石阶,施耐庵循阶而下,走完台阶,转过一根撑柱,抬眼一望,不觉又惊叫起来,窑洞深处站着两个人。左边那个英俊后生却是红巾军首领刘福通的掌坛总管潘一雄,亭亭玉立在右边的那个红巾红裙的女子,分明是白莲教飞凤旗旗首宋碧云!
这一场面实在出乎意外,施耐庵一时竟恍惚若梦,他望望面前这两个人,又望望立在身后的那个黄脸军官,半晌说不出一个字来。
倒是宋碧云先发了话。她趋前一步,朝施耐庵施了一礼,笑道:“施相公,别来无恙。”
这一声把施耐庵唤醒过来,他仔细打量面前的宋碧云等,不觉狂喜地叫道:“潘总管,宋旗首,你们怎么来了?”
宋碧云笑道:“朱家庄一别,小女子刚刚走到济州,便遇到乌桥镇刘大龙头的信使,命俺滞留山东,协助施相公去梁山故垒取那白绢,昨夜已先到了戴大哥这里,不期此刻相会!”
潘一雄也奔过来,抓着施耐庵的手嚷道:“施相公,近日可好?”
一句话勾起施耐庵的心事,想起离开朱家庄后的种种经历,不由得热泪满腮,呐呐地说道:“惭愧!费了许多周折,尚未走到梁山,晚生有负众望!”
那黄脸军官插上来说道:“众位有话慢慢叙谈,请到这边来。”
说着,领着众人转过两个巷道,只见一个深深的穹庐下早已摆好了酒菜,黄脸军官招呼众人坐下后,从怀中掏出那壶从纯阳楼斟来的佳酿,说道:“施相公,休怪俺鲁莽,纯阳楼前抢来的这壶酒,正好为众位接风,只可惜那黑兄弟没有口福!”
说毕,与众人斟满杯,朗声说道:“为重振梁山雄风,为抗元大业,干了这一杯!”
众人一饮而尽,施耐庵望着那黄脸军官说道:“足下行迹奇异,不知如何称呼?”
宋碧云听了,不觉莞尔一笑,说道:“这便是名震山东的‘追风校尉’戴逵戴大哥,当年梁山泊大寨‘神行太保’戴宗老英雄的后人!”
施耐庵一听,不觉肃然起敬,忙忙地斟了一杯酒,递到戴逵手中,说道:“晚生有眼不识泰山,敬此一杯,以表微衷。”他看着戴逵喝完酒,续道:“戴大哥,今日幸会,倒有许多哑谜难解,可否请指点迷津?”
戴逵笑道:“不知施相公有哪几桩不解之事?”
施耐庵道:“戴大哥身为英雄后裔,不知缘何却成了朝廷的典狱军官?这是一;晚生与你素昧平生,你却如何对俺来历行踪了如指掌?这是二;晚生好好儿地赶往梁山,你却为何要在纯阳楼前设下埋伏,将晚生拿到此处?这是三;在马庄驿街头你言明与黑牛兄弟赌斗三百回合,如何却先期回了牢城营?这是四;宋旗首远在济南,潘总管远在乌桥,如何倏忽间来到了济州?这是五。这五点疑窦,实在叫人费尽猜详,请戴大哥一一剖析明白。”
戴逵听毕,又干了一杯酒,揩了嘴唇,掐着两根指头,不慌不忙地说出一番话来:
“说起俺的身世,那也是一言难尽!自从俺那远祖戴宗跟随梁山泊宋江举义失败之后,儿孙们恨朝廷背信弃义,发誓要与那些昏君奸臣们做对到底。可是,当时宋室江山风雨飘摇、绿林义师偃旗息鼓,想找个报仇雪恨的时机,可哪里寻得到?”
说到此处,他顿得一顿,干了一杯酒,又说道:“忽然有一天,俺那常年在外经商的曾祖父的祖父,也就是俺的五世祖戴戡从燕山以北回到家里,十分神秘地告诉家人一个消息,说是大漠上兴起一支民族,励兵精武,行仁布义,要作赵宋朝廷的对头,俺这戴氏门人要想报仇,应该投奔这股人马,借他们之手,斩尽奸佞。当时大家报仇之心太切,也不问青红皂白,便有两三人投奔到了元兵的帐下。那戴戡先辈凭着一身武艺,竟然博得个七品校尉的头衔。”
说到此处,只见那潘一雄怒冲冲拍案而起,叫道:“你的这些祖辈真真糊涂,竟然弃了衣冠风俗,去认贼作父?!”
戴逵长叹一声,说道:“的确是如此。不过,当时在元人军中,俺的那些祖辈没有残杀一个无辜百姓,只是杀了几个平素劣迹昭彰的贪官污吏,猾胥劣绅。待到元人一统天下,坐了龙庭,他们目睹蒙古贵戚们飞扬跋扈、搜刮聚敛、欺压汉人的情景,方才大悟,知道走错了路子,当了为虎作伥的卑劣小人。
“又过了许多年,有一日,那是一个风雨如磐的暗夜,俺父亲突然从任所赶回家乡,召齐了戴家一门四十余口,齐齐跪在祖庙前,披发袒肉,对着祖宗神位惨声叫道:‘列祖列宗神灵在上,不肖子孙鬼迷心窍,为元人暴政效力了六十余年,九死难赎其罪。今日齐集满门,沥血谢罪!’说着,他便剁下十个指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