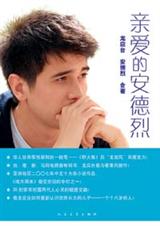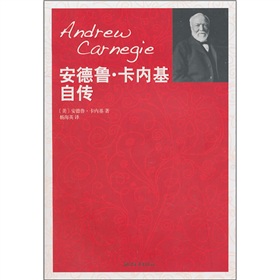����³�����ڻ��Դ�-��2����
�������Ϸ���� �� �� �� �ɿ������·�ҳ���������ϵ� Enter ���ɻص�����Ŀ¼ҳ���������Ϸ���� �� �ɻص���ҳ������
��������δ�Ķ��ꣿ������ǩ�ѱ��´μ����Ķ���
���е����м�ֵ��ͨ��֮һ�������������ǿɾ������Ѻ�ͨ���ߣ��ո���������˹��Ī��ɭ�����ͨ�žͳ�������һ���С������Կ��������ҡ��ű�Ϳѻ����ϰ������˫������Ŵ�����Ϊ���ڻ�����ͬ��Ҳ�����鲢������˼�����ҵ����游Ī��ɭ��һ����������˵�ң�һ�����������ͣ�ͬʱҲ�ǵ������������������������䡪����һְ����������Ķ��ӣ��ҵľ˾����̳С���ֹһ�������������������ո����˰ݷù��ң����롰����˹��Ī��ɭ��������֡�����������ƥ�ȱ���·��˾�ĸ����˷�Ĭ������һ�ζ���˵���������е�һ��ѧʶ���Ļ����������������游��Ӱ�졣������ķ���ش��¼�ʷ�����߰��������ɭҲ˵���������еĽ����ںܴ�̶�������Ϊһ���dz����˵��¼�����������һ��С����ʱ������ܵ������游��Ӱ�졣���ҵ������У��������ܹ��õ�һЩ��ά�����ǵ���һ��ά������һ������������������ʥ������³���������Ĺ��ڵط����ε��ݽ��ĸ���˹�籨�ļ��ߣ���û���κ������Ŀ佱��ʹ�Ҹ��ӿ����ˡ��Ǹ�ͨѶ�������д������ʱ�ո����ֵ����۶������Լ����ҵļ�ͥ�������ҵ����游����˹��Ī��ɭ��ء�������д��������һ�����ڽ�̨�Ϸ��������ʱ���ж�ô�ľ��Ȱɣ�������̬�����ƺ���ò�϶��Ƕ���Ī��ɭ��һ��������ġд���ҼDz������ҵ����游��ʲô���ˣ������Һ���֮�侪�˵�����ȴ�Dz������ɵġ���Ϊ������ؼǵã��ڶ�ʮ�������꣬�ҵ�һ�λص�����ķ�֣�������ɳ���Ϻ��ҵľ˾˱�����Ī��ɭ����һ��ʱ��������ؼǵ������۾��ﺬ������ˮ������֪��˵ʲôȻ�����˷��䣬������һ�����ʱ��������˵�����ϵ�ijЩ�����������ĸ��ײ�ʱ��������ǰ���֡����Ӱ���������ʧ���������˶�ñ������³����ˡ��ҵ�һЩ���ƣ�����Ҳ��ʹ�����ܺܺõĽ��Һ����ĸ������ֿ�����ԭ���ҵ�ĸ�ײ�ͣ�����������ҵ������游�����е�һЩ��������Ŵ�ѧ˵ʱ�̶����õ�֤������һ����������飬����һ������Ҳ�����ڴ���֮�䴫�ݣ�����ijЩ��Խ������Ķ�������Ϊ֮��������ˡ�
�ҵĸ�ĸ��ͯ�꣨ͼ����2��
�ҵ����游Ī��ɭȢ���ǰ������Ļ���Ůʿ������һλ���ݸ߹�ֹ���ţ�����ѧʶ�����ĸ��ˣ��ܿ�ϧ���ǣ��������ͥ���dz������ᣬ��������ȥ���ˡ���ʱ��������һ�ݰ��ȵ�С�������Ϊһ��Ƥ�������ڵ���ķ�ֹ������Լ��������һС�ݲ�ҵ��������ͬ������ǧ�������һ�������ڻ���¬ս��ĺ�ƽ���Ʋ��ˡ����Ĵ���ӣ��ҵľ˾˱������������ͥ���ݻ�ʱ�ڳɳ������ģ���Ϊ�ڶ�ʱ����һƥС�����ɹ���ˣ�������֮���������Щ��ͥ��Ա���������˼���������ĵڶ���Ů����������أ�Ҳ�����ҵ����衣��17������³�����ڻ���ĸ��������أ�Ī��ɭ��һλ������ո�����Ů����������û������̸��̫�ࡣ��������ĸ������̳е��˸߹��º��к����ķ�����ʡ�Ҳ��ijһ���ҿ�����ȫ���署�����Ů���˹���һЩ���������Դ�����Ȼ�Ĵ����ǡ�������˵������Ů��һ��ʥ�࣬���������������ġ�������֮�⣬û���˿���˵�����˽��������Ҹ���ȥ�����������ҵ�ȫ���ˡ����ҡ���һ������״����ҽ�����һ��ʵ�����������Ӣ�ۣ����ҵ�ĸ�ס����������˵ģ���Ϊ�������ǣ��ҵij����ض�����˵�������ϵ����塣��һ������˵�����������ʱ�dz���Ҫ�ġ���Ϊ��ͬ�Ļ����ʹ�ͳ��̼����γ�С����ͬ��DZ�ڵ�������˹����ʵ����˵���ڰ�������ÿһ�������ĺ��Ӷ��ܵ������ӽ��еijDZ�Ӱ�죬����ķ�ֵĶ�ͯҲ����ˣ����ǿ϶��ܵ����ո�����˹��˹�ص�ׯ�ϵ���Ժ��Ӱ�죬������ʮһ���ͣ�1070���ɱ���ʥͽ������ķ�����Ļʺ�����������ġ�����ΰ�����Ժ���ż��Լ������������Ĺ���������Ȼ�������ţ������Ƥ�ؿ�����Ͽ�ȡ�����ʺ�������ص�������������ķ�ijDZ����ż�����������ҥ��������ˣ�˹��˹�������Ŀ�ͷһ�������������ڵ���ķ�ֳDZ�֮�У�����Ѫ������Ѿơ�����³˹�ķ�Ĺ������Ժ�����ģ���������صķ�Ĺ���Աߣ����ڲ�Զ����Χ�ģ������������������������С������һ�ο������������������ٿ�����ij���ʱ���ǵ�ȷ��һ�����¡����������̾��ڸ���������Ӣ�ﴦ�ĸߵ��ϣ���ǰ���Ը����������ӽ�ת�����棬���������������Ұ�У�����Զ����ʱ���ֿ������ؿ���������ɽ�ķ嶥����һ�ж��������뵽�ڵ���ķ�ֺ�ͬΪ�ո������ڽ̺�����ʱ������Щ��ȥ��Ȩ���ǡ��������Ļ����������ͯ���ܵõ����ȵķ�չ�������������Ŀ���������ս���ʫ���������Ϣ��������Ŀ������ʱ������������ʷ�ʹ�ͳ��������Щ�ͱ���˶�ͯ�ǵ���ʵ���硪�������������ǵġ����������Ժ���ٵĽΣ��������������������Ͽ����ʵ��ʱ����ʵ�ſ�ʼ������������������ʱ���������������е����һ�죬�����ڵ���Щӡ����Ȼ�����ţ��������ǻ�ż�����ݵ���ʧ����ֻ�����DZ����ϱ��������ܵ���ѹ�ơ����ǻ�����������һ����һ�ε������Ҹ�������Ӱ�죬�������ǵ�˼���ױ�����ǵ�����ڵ���ķ�֣�û���ĸ��ϻ۵ĺ�ͯ�ܹ����ѳ���Ժ�������Ͽ����������Ӱ�졣��Щ�����ᴥ�����Dz��ҵ�ȼ�������DZ�ڵĻ��磬ʹ�����dz�Խ����Ҫ��Ϊ�����Ӳ��������Щ��һ�����ҵĸ�ĸҲ����������������ܹ���Ļ����£���ˣ��Һ������ɣ�������ʫ��������Ӱ��һ��Ҳ�鼰�����������������ҵĸ����ڷ�֯ҵ�л�óɹ������DZ��Ħ�Ͻְᵽ��¹���һ�������ö�ķ���������Ļ���̨��ɴ��ռ����¥�µ�һ�㣬������ס��¥�ϣ�������е�����¥��ֱ����֮��ͨ����ǿ����˵��������ʽ�ո�����ӵĹ�ͬ���a12������Ŀ��ڻ��ڸ��ķ�ɴ��ǰ�����������ҵ����ڼ��俪ʼ�ĵط���Ȼ����ֵ��ǣ��Ҷ���Щ����ĵ�һ�λ��ݾ������������ҵ�һ�μ���һ��С��������ͼ��ʱ���������ڹ����ϣ��������Ӣ����ô�����ҵĸ��ס�ĸ�ס������̸��Ͱ��ؿ����������������ƥ�ȱ�������ָ���������������Ǽ����ӡ�����֮���̸��Ͱ��ؿ������ȥ���ǿ����ǵõ�����ŵ�����ء���ʱ���Ҽǵ��������Σ���£�Dod�������Լ�����������ͷ���ľ�Σ����������һ�������ڶ�¥�ϵķǷ������ġ��Ҽǵ����Ǵη�������������֮�У������������ҵĸ��ס����塢���Ҽ����������������ļ������ӡ�������һ��С���б���Χ��������ͬҵ�������к�������ӷ����˼��ҵ��������ҵ���;˾��ǣ��Լ��ҵĸ������ڻ����з��Ե���Ҫ����ҵ�������ͥȦ�Ӷ�������ɧ�������ˡ�����������һ������ؼǵ��Ǹ����ϣ��ұ����ϵ�һ��������ô��������ѡ���������֪ͨ�ҵĸ�ĸ˵�����˾���Ϊ�ټ��Ѿ�����ֹ�ٿ��Ļ�������ؽ��˼�����ͨ����ʿ�İ������ΰ��������ٿ��������ļ�Ӣ��Զ��ץס����������ҹ�������������ӣ������������һ��Ⱥ�ˡ����ǵ��Ļᷢ���������ص��鷳����Ϊ�����ǹĶ���Ҫȥ�������������������ֵ�֪����������Ȱ���ߵ���ǰ�������µĴ�֣����������dz��롣���������ˣ���˵���������λ��������Ϊ�����������ڽ������������ô���������ǵ��������������������ˣ��ڶ��ݵ�ͣ��֮������˵�������ڣ�����ƽ�����뿪������������еļ�ͥ��Աһ�����Ҿ˾˵�������һ�ֵ��º;������������Է�����һ��ǿ�ҵ�˳�ӣ�Ȼ����������ȴ��һ���������ӣ���������һ��ǿ�ҵ����������ǿ����������е���һ�ж������ؽ��У���Щ����˽�µ������Ļ��ォ���ж�ô���ơ���һ�о�����������������Ȩ��Ǵ��ΰ��Ĺ������壬��������Խ��һ����ס��������ͬ��һ��������˵����ء������˵ļ��磬������û����Ȩ������ƽ�ȵ�����Ȩ�����������������ܵ��ļ������ĵ����ɣ��ұ���������ķ�Χ�гɳ�����Ϊһ����ͯ�����Ѿ�ɱ���˹����������ͷ⽨������������Ϊ���ǵ�������Ϊ�˹��ҷ���ģ���˱�Ҳ��һ��Ӣ����Ϊ����������ں�ͯʱ����������������������Ӱ�죬��ʱ��Զ���ܹ�ǫ����ȥ̸����Щ��Ȩ������������Ȩ�ߣ���Ϊ���Dz���ͨ��ij�ָ��еķ�ʽʹ�Լ��������Ӯ�ñ����������ص�Ȩ������ֻ����Ϊ���ǵ�Ѫͳ�������ǵ�������Ȼ��������Ц������ʲôҲ���ǣ�ʲôҲû����ֻ��������Ϊһ��żȻ�ij����㴩�Ž�������ë������������ʼ��ҡײƭ�����ļ�������߳ɹ��IJ����Ѿ�������һ��������صס����е��������;�����Ȩ�����������Ǿ��������Ĵ������ǣ������һ���в��ܵ����ܵ�������������Ϊ֮�е����ȡ������Dz����䷳�����ý��е��Ǽ����ܹ�ȷ�ر�����ҵ���ߵ���䣺�������и���³ͼ˹������Ҳ���ܹ����̣�ħ��Ҫ�������ľ�����ǧ������ذ��й��ҡ������ǣ�������Ȼ�ǹ���������ֻ��һ��Ӱ��Ȼ����һ�ж��Ǽ̳е�������ֻ�Ƕ����ڼ����������Ķ���������Ӧ������ķ����ΪҲ������������Ϊ������һ��������������ʢ����������˹��������ơ����Ӳ�����������ĸ�Դ��˵�����Ǹ�Ϊ���ŵġ�������̸�۵��Ǹ�ʱ�ڣ�����ķ�ִֵ��˿ڶ���С�ֹ�ҵ�ߣ����Ƕ����Լ��ķ�ɴ����һ̨���ߺü�̨������û�й̶��Ĺ���ʱ�䣬�������ɵĶ��ǼƼ��������Ӹ���������������ȡ���ϣ�Ȼ���ڼ�����мӹ���
�ҵĸ�ĸ��ͯ�꣨ͼ����3��
����һ��������ǿ�ҵ�����ɧ����ʱ����������С��ķ�Χ�У�����Ҳ����Ƶ���ظ��ܵõ��������緹�����һС��ʱ���Χ��Χȹ�����DZ����£������ʼ�����������ص����顣���ӡ����Ʋ��ǡ��Ͳ����ء�������Ϊ��������֪������̸���в�ʱ�رų��������һ���С��ʱ���Ҿͳ�����һȦȦ������������������̸������ʵ���ڣ���Ҳֻ�Ǵ���ĵ�����������ѡ����㷺���ܵĽ����ǣ�����Ʋ����⡣���ֲ�����������֯�������ص����ű�ֽҲ�����������ġ��dz���ֵ��ǣ�ÿ�����ϣ����ϵ�һ������̳���������Ҫ�����۶������������Ҿ˾˱�����Ī��ɭ���������Ǹ��ʶ��ߣ��ڶ�������������˶�Ҫ�������������ۣ����鳡��ʮ�ֵ����˼��������������λ���Ƶ���ľ��У�Ҳ����Ҳ�����������ǵ��������ҶԴ˻���������Ȥ���μ��˲��١��ҵĸ�����ij���˾�����ӵ�кܶ�����ڡ��ǵ���һ�����ϣ��ҵĸ�����һ�����͵Ļ�������Ϸ����ݽ��������ڶ࣬��ֻ�ܴ����ǵ��������ȥ����ʱ������Ҳ����ѹ���ҵ��˷ܺ����飬�����������˶������ػ�����������ſ��һ���˵����£�̧��ͷ���������Ҹе���ij�ְ�ȫ���Ҹ�����˵�ݽ������ҵ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