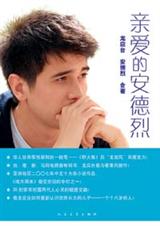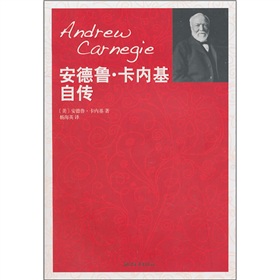安德鲁·卡内基自传-第19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夕法尼亚铁路公司的贡献,你们将分享他的成功和繁荣。最诚挚地感谢你们对我的关心,感谢你们用积极的工作来支持我,也请你们对我的继任者给与同样的支持。再见此致敬礼 (签名) 安德鲁?卡内基1965年3月28日从那以后,我不再没有为了工资而工作。一个人要听命于人,那他必然地只能在小范围内有自主权。即便当他成为了一家大公司的总裁,他也很难是自己的主人,除非他掌控自己的股票。一个在能干的总裁也要受到董事会和股东的制约,他们有可能对商业一窍不通。但是我还是要很高兴地说,我今天最好的那些朋友,是和我一起在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工作的那些朋友。1867年,菲浦斯先生、J。W。范德沃特和我一起重游欧洲。包括英格兰、苏格兰及欧洲大陆。这这之前,“范迪”就成为了我亲密的朋友。我俩读了拜尔德?泰勒的《旅行手册》,大受鼓舞。当时正处于是油性分歧,股价以火箭般的速度攀升。一个星期天,我躺在草坪上,对“范迪”说:“如果你能赚到三千美元,你会和我一起去欧洲旅游吗?”“鸭子会游泳,或者,爱尔兰人吃土豆吗?”这是他的答复。“范迪”用他积攒下来的几百美元投资石油股票,很快就赚到了这一笔钱,这就是我们旅行的开始。我们邀请我的合伙人亨利?菲浦斯一起参加,他当时已是个不小的资本家了。我们游览了大部分欧洲国家的首都,以年轻人特有的激情,背着背包爬上每一座山,在山顶上睡觉。我们旅行的最后一站是维苏威火山。在那里,我们立下誓言,有朝一日我们一定要环游世界。这次欧洲之行受益颇多。在此之前,我对绘画和雕刻一无所知,但很快我就学会了鉴别一些大画家的作品。也许有人不会感觉到他在欣赏大师们的伟大作品时所获得的那种能力,但是当他回到美国,他会发现他开始无意识地抵制那些在他以前看来漂亮的东西,开始用一种新的标准来审视作品。那些真正的杰作给他的印象是如此之深,一切自命不凡的作品便再也没有了吸引力。我这次欧洲之行也第一次让我感悟到了音乐盛宴的无穷魅力。当时伦敦的水晶宫正在庆祝韩德尔的诞辰,在此之前我从来没有这样深刻地体会过音乐的魅力和壮美,而在此之后我也很少有这样的感觉。我在水晶宫所听到的、我后来在欧洲大陆的天主教堂中所听到的、还有唱诗班的合唱,都毫无疑问地使我对音乐的鉴赏能力有了大幅度地提高。在罗马,教皇的唱诗班和教堂在圣诞节和复活节举办的庆祝活动更使我站到了音乐壮美之巅。这次欧洲之行对我的商业意识也极具意义。一个人只有跳出共和国的漩涡,才能够有一个对其旋转速率的正确估计。我觉得我们这样一个制造企业,其发展速度无法快的满足美国人民的需求,然而在国外,好像没有什么发展进步的东西。如果排除这个大陆上的几个首都城市,那么这里的每一件事情看起来都是静止的。而美国到处都呈现出这样一番景象,就像书中描述的建造巴别塔的景象:成千上万的人来回奔忙,比他的任何一个邻居都要有活力,而且所有人都参与到这座通天塔的建设中来。我们工厂——美国首家此类企业——的运营能取得新的发展,我必须感谢我的表兄弟“多德”。是他带克鲁曼先生去英格兰的威根区,并且给他讲解如何从煤矿中清洗煤渣和炼焦的工艺。克罗门大为振奋,不断地跟我们说,如果可以把我们这儿的煤矿所产生的矿渣利用起来,那该是多么伟大。而将它们扔掉又是多么的浪费。多德表格是个机械工程师,毕业于格拉斯哥大学,师从凯尔文爵士。他证实了克罗门先生的说法是正确的。于是,1871年12月,我开始筹集资金,在宾夕法尼亚铁路沿线建了几个厂子。我与几家主要的煤炭公司签订了长达十年的合同,它们为我们提供煤渣。另外我们还需要铁路公司的运输,也与它们签订了合同。劳德先生来到了匹兹堡,并且好几年主管这个项目整个的运行,还开始建造美国第一台洗煤机。他获得了成功,在采矿和机械设备领域他向来都能出色的完成任务,很快他就将建厂的投资收回了。难怪后来我的合伙人要把焦炭厂纳入我们的集团公司,它不仅仅想拥有厂子,也想得到“多德”,他已经声名卓著。
钢铁厂的回忆(图)(5)
我们的炼焦炉数量不断增加,直到后来我们已经拥有了500座,每天能够洗煤1500吨。我承认,每次我说起这些炼焦炉,都会有这样一种感觉:如果一个人使先前只长出一棵草的地方长出了两棵,就算得上有功于人类,那么,那些从扔掉的废料中生产出来优质焦炭的人完全有理由为自己庆祝。变废为宝,点石成金,这是一件美妙的事情。而能在我们这块大陆上成为这样一个先驱者,也是很了不起的。我在丹佛姆林的表兄莫里森的儿子后来也成为了我的合伙人,对我来说,他同样是可贵的。有一天,我在工厂车间里巡视,经理问我是否知道我的一个亲戚是位杰出的技工。我告诉他我并不知道,我问他能否和他聊上几句并且四处走走。然后,我们见面了,我问了他的名字。“莫里森,”这是他的回答,“罗伯特的儿子”,罗伯特是我的表兄弟。“哦,你是怎么来这儿的?”“我想我们能过得好一点,”他说。“那,是谁和你一起来的呢?”“我妻子。”他回答。“你为什么不先来见你的这位亲戚,我可以介绍你到这儿来。”“呵呵,如果有机会,我想我并不需要帮助。”这就是真实的莫里森,从小便被教育要依靠自己,像金星(Lucifer,另一含义是魔鬼)一样独立。之后不久,我就听说他被提拔为我们在迪凯纳的一家新厂的主管。从这起步,他的职位不断稳步上升。如今,他已经是不择不扣地百万富了,但依然保持着他特有的明智的判断。我们都为汤姆?莫里森感到骄傲。(我昨天收到他的一封短信,在信中他邀请我和夫人在参加卡内基学院的周年庆典时一起到他家做客)。我以前一直认为我们应该扩大钢铁厂的规模,而许多与钢铁制造业息息相关的新兴行业也应该得到发展,而当时这些还正处于发展初期。所有对钢铁行业未来的担心都随着美国在进口关税上的举措而烟消云散。我清楚地认识到,内战已经使美国人民下定决心,建立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任何与国家安全有实质联系的产业都不能依赖欧洲。美国所有形式的钢材和所需要的大部分的铁一度依赖进口,英国是最大的供应国。美国人民强烈要求自足,国会决定向进口钢轨按价征收28%的关税——相当于每吨28美元,当时钢轨每吨可卖到100美元。其他物品也按相应比例征收。在美国制造业的发展中,保护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在内战以前,这还只是一个政党问题。南方主张自由贸易,而北方则认为征收进口税是必要的。英国政府对邦联体制的支持,在它从阿拉巴马和其他一些攻击英美商业的武装民船中逃离出来之后达到了顶点。由此美国人民对英国政府产生了敌意,尽管大部分的英国人民支持并喜爱美国。如今征收关税已经不再是一个政党问题了,而是一项国家的政策,为两个政党的一致支持。关税变成了爱国税,有利于经济发展。国会中的90多个北方民主党议员,包括议长(speaker of the house)都赞成这一点。资本毫不迟疑地登上制造业这艘大船,自信得就像国家会尽一切可能保护它一样。内战后的几年中,降低税率的呼声开始高涨,我也不可避免地卷入了这场争论。经常有人指责道,制造业主贿赂议员的现象很普遍。但据我所知,这种说法没有任何根据。除了维持钢铁协会每年所需的几千美元之外,他们从来没有为任何目的集过资。他们只不过为一次保护贸易对抗自由贸易的活动捐了款。在我的大力支持下,刚才的进口税持续下降,到后来降到了每吨先前的四分之一,每顿起美元。(今天(1911年),进口税又降了一半,即便如此,在接下来的方案中还要得到继续修改。)克利夫兰总统为通过一项新的激烈的税则所做出的努力很有趣。它在很多地方降税太多,如果它获得通过的话,那么将会有多家而不是一家制造商受到损害。我被召往华盛顿,准备对威尔逊法进行修改,提高税率。参议员高曼(参议院中的民主党领袖)、纽约州州长弗劳和许多出色的民主党人都和我一样是坚定的适度贸易保护论者。他们倾向于反对威尔逊法,因为它过于严厉,降税太过厉害,肯定会阻碍我们国内的一些工业。高曼议院对我说,他希望我尽量减少对本国生产商的损害,他还说他的同事们对我有信心,如果税率大幅度降低,参议员们又一致支持这一法案,那么在钢铁的税率上,他们将接受我的引导。我依然还记得他说的话,“我可以反对总统,但必须打败她;但我承受不起去反对他,但却被他打败的结果。”弗劳尔州长也持同样的看法,让我们党同意我所提议的大幅度降税,这没有丝毫困难。威尔逊——高曼关税案获得了通过。后来我会面了高曼参议员,他解释说,他必须给棉花包让路,以确保一些南方参议员的利益。棉花包须免关税,所以,关税立法获得通过。在内战刚结束的时候,我在制造业中的影响力还不够参加关税法的制定,所以我总是在扮演一个赞成者的角色。我反对极端主义——既反对那些认为关税越高越好,对所有的减税措施一概抨击的非理性的贸易保护主义者,也反对那些抵制一切关税,倡导无限自由贸易的极端分子。1907年,我们有能力废除在钢铁上的一切进口税,而不会有任何损害。高额关税在早期是必要的。欧洲没有多少剩余的产品,所以,即便这里钢铁价格的大幅度上涨,人们也只能从欧洲进口少数的钢铁产品,甚至这还可能导致欧洲钢铁产品价格上涨,国内的制造工业不会受到影响。自由贸易只有在需求过量的时候才会妨碍国内钢铁价格的上涨。对于自由贸易,国内的制造商们无须害怕。
总部在纽约(图)(1)
我们的商业继续膨胀,我需要频繁地去东边,尤其是纽约,它在美国就像伦敦在英国一样重要——美国真正重要的大公司的总部都在这里。似乎不在纽约设立代表处,大公司就不能良好发展。我弟弟和菲普斯已经完全掌管了匹兹堡的业务。对我来说,似乎只要指挥下公司整体政策,以及参与重要的合同谈判。 我弟弟很幸运地和露西?克鲁曼小姐结婚了,克鲁曼小姐的父亲是我们最可贵的一个合伙人和朋友。我们在荷姆伍德的家交给了弟弟,这样我有一次被迫放弃现有的生活圈子,1867年离开匹兹堡,到纽约安家。对我来说,这个变化是痛苦的,而对我母亲则更加难以接受。但是她依然还年富力强,只要我们不管到哪里都在一起,我们就会很高兴。她依然满怀离愁别绪,在纽约我们完全就是陌生人,一开始,我们把住处安在圣尼古拉斯旅馆,它在当时当地十分有名。我在百老汇街开了一个办公室。匹兹堡的朋友们有时来纽约,我们都会感到非常高兴,这上也是到纽约之后能让我感到快乐的主要事情了,匹兹堡的报纸也是不可少的。我频繁的奔赴匹兹堡,母亲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