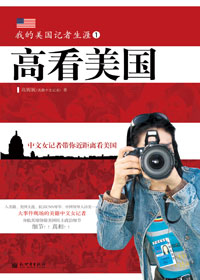美国人:殖民地历程-第38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础,你们便可正规地学习法律,兼学一些有助于精通法律的相关的科学。这
类科学主要包括物理学、伦理学、宗教、自然法、纯文学、考证学、修辞学
以及演讲学。兼习几种学科自有益处,因为多样化会开拓思想与视野。”
学院介绍法律问题,不是出于专业上的原因,而是因为它密切关联着神
学与“哲学”研究。国王学院第一张课程表列举四年级课程为“法律与政府
的主要原理,以及宗教史和世俗史”,不久又设立了自然法教授讲席。杰斐
逊自己的计划(先为威廉与玛丽学院,后为弗吉尼亚大学制订),包括了与
人文主义主题密切有关的广泛的法律研究。北美法律研究的更为广泛的内
容,表明美利坚人对这一职业的观念距离其英国行会背景甚远。埃兹拉·斯
蒂尔校长关于在耶鲁大学设置法律教授讲席的计划(1777 年)对此作了最
好的表述:
法律教授讲席与医学教授讲席同等重要。它确非旨在培养出律师或高等律师,而只是为了造就
平民(公民)。在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绅士中,能够从事神学、法律或医学等有学问的职业的
也许不到四分之一,大多数人在完成大学课程以后就回到家乡,与公众打成一片,经营商业或
垦殖自己的种植园。也许其中绝大部分人在其生活中,响应本地区的召唤,参加本州这样或那
棵的民政改革与公共事务。可以断言,值得认真注意的是,在这个知识领域的培养和教育,将
使他们能够成为社会有用的成员,市镇行政管理委员会成员、治安官、议会议员、法官和国会
议员。一个社会拥有许多受到有关权利和自由权知识的良好教育的人,该是多么今人欣慰。这
些知识正在吸引和影响那些没有受过自由教育的人,使他们适于从事公共事业。主要应归功于
我们中间的各个学府,美国才拥有许许多多这样一些人来从事现时的艰苦斗争,这些人具有已
经震惊欧洲并将使我们流芳后世的智慧与宽宏,他们能胜任制定新的政策、建立新的政府形式,
从事美利坚合众国的陆军、海军、政治等部门的公共事务和全部公共管理这一伟大而重要的工
作。……一个由在法律、权利与自由方面训练有素的公民组成的共和国,是不可能被奴役的。
在尔后的年代里,当美国的法律界更为自觉时,它将夸耀“律师”在建
立这个国家及其制度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独立宣言》的五十六位签署者
中有二十五位是“律师”;费城制宪会议的五十五位成员中有三十一位是“律
师”;在首届国会中,二十九名参议员中有十人以及六十五名众议员中有十
七人是“律师”。但是,与普遍的信念相反,这一情形并不表示一个专门化
的需要学问的职业在塑造我们国家中的重要性。美国人的经历尚未培养起对
法律或其他方面的有造诣的专家的敬畏之感。所有美国职业特权的界限都是
模糊不清的。上述情形所确实表明的是美国事务家普遍具有法律才干,还表
明在一个变动不定的美国社会法律与所有其他知识之间的界限是模糊不清
的。说杰斐逊是一个职业“律师”,那就简直根本没告诉我们这样一个曾在
乔治·威思门下短期见习而自学成才的律师——杰斐逊的经历!
安德鲁·杰克逊的生涯经典地表达了在美国当律师意味着什么。他在充
当了一个巡回法庭的嘻闹旅行的学徒以及接受爱好交际的约翰·斯托克斯上
校的督导之后,于 1787 年二十岁时,被该庭宣布为“一个道德品质纯洁,
法律知识丰富的人”。
对专门法律知识围墙的这种早期突破,为研究以后几十年间美国政治生
活提供了线索。从对律师的不信任中滋长起一种对法律日益广泛的关注。美
国革命能用法律语言来阐述,是因为这种语言是为文明社会服务的。贯穿于
十九世纪内战和二十世纪新政的美国重大政治争端,是用法律语言来表达的
(是一种是否“合宪法性”的神圣检验),正是因为美国人将可敬的法律框
架视为社会赖以成长的骨骼。将法律的检验如此用于政治,有着一种在非原
始民族中不常见的正在蓄积的自我陶醉。在一个梦想已成为现实的世界上,
社会已然开始使自己的实际形象成为自己所向往的模式。
第八编新大陆的医学
“他们之幸运在于这里很少有医生,仅有
的医生也只运用朴实无华的治疗方法,所
需的药物在本地的树林中多得很。确实,
他们也并无很多病痛,治疗方法人所共知
,并非神秘得要像其他国家的博学者们那
样,今人生厌地将医生作为一项职业。”
罗伯特·贝弗利
34.自然康复和简补的治疗方法
美洲的经历很难激发自然科学方面的伟大业绩。即便在生物科学方面,
殖民地时期也极少理论上的建树。然而在某些科学领域里,美洲生活的天真
简朴,却有着独特的好处;因为这里没有欧洲科学领域里盛行蔓生的生硬教
条。医学——包括药物,即后来所谓的药学或药物学——就是这样一个领域。
在十八世纪,博物学(特别是植物学)和医学是紧密相连的。那时候,
最常用的药物都是植物性的,最重要的植物学论著是“药草纲目”,即对通
常用于治病的植物进行分类,并介绍各种药草的分布、生长情况及其用途。
在欧洲受过训练的医生来到这块长满陌生植物的新大陆时,想要抓住机会作
出些植物学方面的发现,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就是不从事医学的门外汉也
注意考察美洲的植物,希望为医学知识增添一些新东西。
1610 年,即詹姆斯敦殖民地艰难的早期年代里,总督和参事会致函伦
敦公司,谈及疾病广泛传布(“奇特的腹泻和疟疾勺以及药物供应日趋减少
的情况。公司医生劳伦斯·博亨设法寻找可供药用的当地植物。除了其他一
些发现外,他在白杨树的树胶中找到了一种能“愈合任何未愈伤口”的香脂,
他还用詹姆斯顿周围很普遍的黄樟材做试验。烟草从一开始被发现起,就因
其可能有的药用功能而使欧洲人大感兴趣。哈里奥特在他的《新发现地弗吉
尼亚实况概要》(1588 年)中,大肆吹嘘烟草可作药物,有“扑热息火、
消除滞稠体液、疏通毛孔和人体各种通道的功效。它不仅可用来防止人体内
的滞阻,而且即使有滞阻,使用不久能迅即开通:由此,体格能明显保持强
健,不大有我们英国人时常罹致的众多的重病。”有人声称,吸用烟草能治
疗痛风和疟疾,并有醒酒、消乏和解饥的作用。有一种植物叫“詹姆斯敦草”
(曼陀罗),现代医学业已证明少量服用有镇静和解痉作用,而大剂量使用
则有麻醉作用和毒性。这种植物被誉为有“凉血平抑”的作用。
罗伯特。贝弗利在 1705 年提到,“种植园主们讨厌所有的医生,除非
处于万不得已的地步”。他说:
种植园主们……有几种本地的块根植物,他们宣称,患病者用之,必然药到病除。他们之幸运
在于这里很少有医生,仅有的医生也只运用朴实无华的治疗方法,所需的药物在本地的树林中
多得根。确实,他们也并无很多病痛,治疗方法人所共知,并非神秘得要像其他国家的博学者
们那样,令人生厌地将医生作为一项职业。
在两位很有名望的英国医生劝说下,马克·凯茨比于 1710 年到 1719 年问进
行了广泛的旅行。此行使他写出了《卡罗来纳、佛罗里达和巴哈马群岛的博
物学》一书。他发现了许多有治疗作用的植物,包括盾叶鬼白、蛇根、人参
和巫棒。在最有用的植物之中,有一种叫“牙痛树”,其叶“气味有如桔叶,
种子和树皮芳香辛辣,有止血收敛的功效。弗吉尼亚和卡罗来纳的沿海居民
用它治牙痛,故得此名。”甚至醉心于欧洲医学、希望把欧洲医学的清规戒
律全盘照搬到美洲来的约翰·摩根医生,也不能忽视美洲所特有的机会:
我们生活在一片辽阔的大陆,业经考察过的地方只是极小的一部分,甚至有人居住的地方亦是
如此。森林、山脉。河流和地下矿藏为那些富有创造才能的人们提供了探索研究的广阔天地。
在这一方百也就是说,一个美洲学者的条件比欧洲学者优越得多。最广阔的探索领域展现在我
们西前,让我们去丰富博物学方面的知识。欧洲各国己由许多极具天赋和学识渊博的人反复作
了全面深入的考察,他们力求对这些国家提供的一切事物进行最为细致入微的研究,因此后继
的学者很少有希望和机会作出新的发现。但这里的世界可说是提供了尚未揭开的最丰富的自然
知识的宝藏,它足以满足青年自然探索者们如饥似渴的求知欲望。他们的发现必定会大大地丰
富医学科学……在这块土地所特有的林木杂草中,谁知道会有多少种植物具有特殊的功效呢?
美洲医生对博物学的重视,不仅受着新大陆无限机会的鼓舞,甚至也受
到欧洲古老的医学教条“植物外形特征论”的影响。这一教条可以用“以毒
攻毒”的格言来表述(奇怪的是,这一信条后来竟为接种疫苗法的运用所证
实),意思是发生某种疾病的地方和可望找到治疗办法的地方这两者之间,
必定存在着天意安排的巧合。到了十八世纪末期,有些科学家开始怀疑这种
笼统的说法,但它如此广泛地被人们相信,以致本杰明·史密斯·巴顿在《药
物标本的采集》(1801—1804 年)一书中,把下面的理论称为“老生常谈”,
“各个地区都有适于治愈当地特有疾病的药物……土法治疗所需的大部分药
物都可以在疾病流行地区的植物中找到。”人们因此普遍认为,治响尾蛇咬
伤的药物大概可以在响尾蛇出没的美洲原野发现。果然,美远志(俗称“响
尾蛇根”)证明正是这样的植物!宾夕法尼亚瑞典教会的教区长尼古拉斯·科
林牧师,一个小有成就的发明家和博物学家,因此不无根据地宣称:“慷慨
的造物主显奇迹,造就了与人的需要相应的万物……每个地区都有对付其自
然缺陷的土生药物。”即使在这一古老的教条淡化到只是一种假设或怀疑时,
它仍然鼓励着美洲疾病的研究者特别注意造物主安排于此地区的植物。
在美洲,受过训练的医生们对美洲地貌、气候和特有的动植物表现了一
种给人深刻印象并且富有成果的关注。所以如此,部分的原因当然是植物学
和医学作为欧洲学术的两个门类,历来有着密切的联系(这对两者都不是特
别幸运)。那时候,除了数学家和天文学家,科学家们一般都是从接受医学
教育入手的。伟大的瑞典植物学家卡尔·林奈就受过医学教育;植物园主管
赫尔曼·波尔哈夫作为莱顿大学的植物学和医学教授,支配了十八世纪初期
的欧洲医学学科。对于他的门徒来说,植物园是医学机构的基本设施。甚至
在十九世纪 初,纽约市培养内外科医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