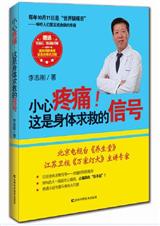这是一篇纯情的正直的包养文-第22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辛加无法眼看着小松出丑,便要站起来替小松解围,莉莉制止他,此刻她美目泛泪,哽咽道:“老公,老公,你告诉我,你是不是跟她在一起了?”
“是,但我已经跟她分手了,我跟她没有……”
小松不敢直视妻子的眼泪,扭过头开口承认自己出轨的事实,他话未完,便叫丈人一拳击倒,重重倒地,带落手边的杯盏碗碟,汤水菜肴顿时哗啦啦洒落一地,众人躲避不及,莉莉难以抑制心中悲愤,尖叫着掀翻桌上一切物事,场面彻底失控。
“老子打死你个王八蛋!”
女方亲友愤怒地厮打小松,其中属他老丈人和大舅哥战斗力最强,男方一众亲朋赶紧上前拉架,拼了死劲才隔开他们,饶是如此小松仍挂了彩,被打掉一颗牙齿,可见其狂怒中的丈人大舅之可怕,只怕小松一条小命是要交代在这儿了。
大厅里乱哄哄闹成一片,本抱着看戏心态的宾客瞧见势头不对,风流戏文演变成包公怒铡陈世美,立刻争着抢着撤退,方才还热热闹闹地一顿满月酒转眼间闹得风卷残叶般凄凉,那狐狸精一瞧见势头不对便脚底抹油溜了,不多时偌大的宴会厅只剩主人亲朋并一双哭得心碎的母子,场面实在难堪。
“小松你疯了!怎么会弄成这样!你说话呀!”乐队三人与小松关系最是亲密,都道这小夫妻俩情比金坚羡煞旁人,真是抓破脑袋也弄不明白,并且这事还瞒得滴水不漏,此刻才捅破,三人都震惊不已。
“他有脸说嘛他!”丈人讥讽道,“他不要脸我们还要脸呢!传出去叫我们还怎么做人!”
小松古怪地冷笑一声,“脸?我丢你家的脸?!”
他忽然不顾一切歇斯底里大叫道:“我丢你家的脸,你家什么时候给过我脸?啊?!”
从未有人见过如此这般的小松,莫说至交好友,就连亲生父母亦未曾见过,老两口望着面目扭曲的儿子,都吓呆了。
“我是疯了!都是你逼的!”狂犬似的小松朝着自己的妻子大吼,愤怒中仿佛带着残酷的快意。
“别说了小松!你冷静点!吓着你儿子了!”
闺蜜怀中的小婴儿被奇怪的大人们吓得哭闹不止,听着格外凄厉,莉莉悲哀地望着向自己大吼大叫的丈夫,苦笑道,“让他疯,我知道迟早会有那么一天,哎,我问你个事,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我怀孕的时候?”
“你知道还何必问。”
孕内出轨,辛加难以置信地望着小松,仿佛他是什么戴着面具的陌生人。
这段女强男弱的长短脚之恋终于走到尽头了。
“我知道了,我知道了。”莉莉喃喃自语,又问,“老公,你喜欢她吗?”
“我跟她已经分手了。”
众人注视着他们的一举一动,看到莉莉面上浮现出如释重负的轻快笑容,突然生出不安的预感。
“儿媳妇,看在宝宝的份上,你千万别冲动,我们替这畜生给你道歉……”
“小松!你快向莉莉认错啊!莉莉,嫂子,你看我们都认识十多年了,小松他就一时鬼迷心窍……”
然而莉莉铁了心不回头了。
几人聚集在小松家中,坐立难安,父母亲老两口疲惫而抑郁,不断叹气,客厅里弥漫着酸涩苦辣的烟雾,缓慢沉滞地在上方盘桓。
“明天一早去民政局签字离婚呗,没什么好说的了。”小松嘴里叼着烟,含混不清道。
“孩子怎么办?!”小松母亲声嘶力竭道,“你怎么能说出这么不负责任的话!”
“你赶紧把事情交代清楚!你脑子有毛病吧!好端端一个家……”
小松揪起辛加的衣领,因他比辛加矮小而显得此举尤其吃力,脖颈青筋鼓胀,“你少这样端着自己指责我!你以为你是个什么好东西!”
“放手!”童以恒将小松掼到一旁,余力未消,他便狠狠撞到身后的置物架,杂物哗啦啦落了一地。
他颓然坐在地上,形容萎顿不堪,他抬不起头来,两手捂着一张红肿的脸,哀哀啜泣。
“她说她是我粉丝,很崇拜我,我们在一起,没人看见,也没人说我们不般配……他们都说我吃软饭,靠女人……我是个男人……”
窗外下着连绵秋雨,铅灰色的天沉沉向地面压迫,走廊里充斥着白茫茫的人造光源,如同一段漫长冰冷的静噪音。阿绿凝望萧索秋景,不厌烦地咀嚼着口中的薄荷糖,身周隐隐透出一股轻飘飘冷冰冰的香气。
“这种事没什么好说的。”他耸耸肩,“你情我愿。”
最近乐队五人陷入了一种尴尬的相处氛围,自从阿绿的莫名疏远与小松的私事捅破后,一直维系五人友谊的绳索越绷越紧,但大家都装作若无其事,自欺欺人,集体无视绳索终有一天会断裂这一事实,苦苦维持表面上的亲密。
“你在戒烟?”沉默半晌后辛加问道。
未及阿绿回应,助理便在拐弯处探出头来询问,“ok了吗,导演喊你们回去重新就位。”
受近日不愉快的情绪影响,这支饮料广告拍得异常艰辛,实在是放不开手脚在摄像机前打闹追逐,一张脸因着假笑都快要僵硬了。
导演不生气才有鬼,急得几欲爆炸,后来发现只有阿绿的情绪比较到位,唯有令镜头多集中于贝斯手,这才能完成拍摄任务。
辛加枕在童以恒的胸膛上,两人之间紧贴着一层逐渐褪去热气的湿滑汗水,辛加面颊挨着的肌肉仿佛是某种珍贵织物的面料,带着妙不可言又令人着迷的触感。他听着胸腔传来的心跳声,昏昏欲睡。
“导演还不错,还给你说公私分明的道理,你记着别忘了。”童以恒有一下没一下地抚摸辛加光滑的背脊,嘴里却说着这样认真的话。
辛加仔细聆听他说话时肉体传来的震动,如同风拂起绿野的波浪,心里忽然生出不再无枝可依的奇妙感觉,于是便微微抬头,亲吻童先生带着胡茬的下巴。
作为摇滚乐团的主唱,该是专心创作好好唱歌才对,只是国内唱片业十年前便日渐式微,到了今时今日已仿佛是夕阳产业,破产者转行买烧鸭者比比皆是。近段时间万人空巷的歌唱真人秀仿佛带来了些许希望,如枯枝上的一点新芽,然而日子久了,那点势头亦不过是刺激将死之人的那两道电流,架势挺大,但要死的终归是救不回来。圈里的人自然明白这个道理,借一股势不可挡的真人秀东风,还能唱的,就到歌唱真人秀上玩命唱去;水准不高的,就削尖了脑袋挤到各种虐星真人秀上去露脸,以求在这一片后浪打前浪的海上求得一线生机。
Betty向来对手下的艺人十分严厉,虽是后娘的身却操着亲娘的心,过五关斩六将为辛加争取到一个旅游真人秀的mc位置,将他视作公司力捧新人,摆到最显眼的地方去。
戏也拍了广告也拍了,真人秀也接二连三地参加了,然而作为一支乐队来说,似乎是有些不务正业,连构思新曲的时间都被挤占了,辛加觉得这不是自己想要的结果,偏离了众人的初衷,因此委婉地向经纪人提出了自己的想法。
Betty忙得分身乏术,此刻也不得不坐下来与他扯皮,“你是真傻还是假傻,现在唱歌有多难活你知道吗?要不是看你长得还行才给你机会,不然一百个童董给你撑腰也救不了你!傻小子!”
一番话噎得辛加无言以对,也是,要么听话要么死,当初为了不再做个永无出头日的死外卖仔,甘愿自己当外卖送到人手里,现在还扭扭捏捏个什么劲儿呢!
白痴!傻逼!精神点!辛加对着镜中的自己自掌了几个嘴巴,在门铃的催促下,匆匆赶出去迎接入屋拍摄的pd与vj。
“童童,我走了啊。”辛加亲一亲男友的脸颊,准备出门赶飞机去了。
年近晚,天亦亮得晚,辛加当真是算得上披星戴月地去赶那趟真人秀的越洋航班,他这一去,必定是有十天半个月与童先生分离,心中十分依依不舍,万般留恋,之不能与心上人一说,因他的心上人是个做牛马的命,不知是前世欠了童老总多大的恩情,今世得结草衔环来还。到了年末,更恨不能把人活活累死,年度总结新建项目林林总总,每夜里忙活到凌晨才睡下,在耳边放鞭炮都炸不醒。
童以恒兀自沉沉睡着,却不知辛加快心疼坏了,他忽而一扫不舍与疲态,拎起行李箱昂首挺胸大步向前,看得一旁的犬次郎一愣一愣的。
“哎,刚才还跟块牛皮糖似的,怎么变那么快呀。”犬次郎奇道。
“他爹不心疼儿子,我还心疼我……呢。”
“你什么?”
“我赚钱养他!”
犬次郎受托,一直看着辛加与节目组会合直至登机,想起辛加跟唐僧似的叨叨个不停,三句不离他童先生,只说自己但求变成个挂件,随童先生去哪他便去哪。
哎呦喂。犬次郎揉一揉自己酸倒的腮帮子,而后又掩嘴嗤嗤笑起来。芸芸旅客,他形单影只的背影仿佛发散出超然物外不屑凡尘的道道单身狗佛光。
拍摄地点选在西欧某国,也是近年来国内旅客青睐的热门旅游景点,选择这么一个毫无新意的地方,只因该国与本国签订了旅游发展协议,没办法,政府部门也看业绩的嘛。
说是真人秀,确实是秀,一切按剧本人设发展,譬如辛加,一个以前玩视觉系摇滚的,就在旅行团里担任迷糊卖蠢的吉祥物,贯彻傻弟弟路线。此刻他正与其余五位各有各担当的女艺人,上演一场手忙脚乱无助彷徨的机场打车记。
六个人在奔走着不期然的对视中,都读懂了大家心中对节目组以及那位负责住行的mc男星暴风雨般猛烈的吐槽。
此名男星,用豪门二字都不足以形容他显赫的家世,别人家的少爷能够含着金汤匙出生已是前世修来,这位仁兄却含的是钻石汤匙出的娘胎,家中长辈个顶个金贵,首富爷爷影后姑姑名模姐姐,怕是荣国府宝二爷见了他也得自叹弗如。据说此现代贾宝玉入行纯属玩票性质,拍戏唱歌过足了瘾,便皇上翻牌似的点了个真人秀,吃着火锅唱着歌就来了。
辛加蹲在路旁手托腮,望着这位与司机叽里呱啦砍价的王子,鸟语说得比中文还溜,如鱼得水,连fuck都fuck得那么洋气骄傲,心里不由得生起了一种酸不拉几的憋屈感。
那大约便是仇富。
然而出人意料的是,除了应节目要求表现出独断专行飞扬跋扈的性格外,王子殿下意外地谦恭有礼,丝毫不似外界所传言一般,天下无敌手,嫖赌饮荡吹。
因而辛加便放下心来,在日间拍摄任务结束之时,隔着大半个地球与颠倒的昼夜悄悄地与童先生通电话。此刻正是凌晨,他估摸着童先生起床上班的钟点,捉紧时间,只想听一听心上人的声音。
童以恒自恃比小男友虚长些年岁,又比他多吃了几年盐多行了几年桥,自然是不完小年轻那一套,抱着电话honey baby地叫,平白浪费时间,于是便十分务实,上司查岗一样盘问辛加。
“吃饭了没?洗澡了没?天气冷多加衣服没?睡觉蹬被子没?听监制的话不?听导演的话不?听助理的话不?”
所谓什么样的锅配什么样的盖,辛加对于这样的盘问受用得很,简直是心花怒放,像泡进了蜜罐子里,十分乖巧地一一答了。
“吃了,洗了,加了,蹬了,听话。还有吗?”
“还有。”
“还有什么,我听着呢。”
“我想你,你想我没?”
辛加躲在窗帘后,他面前是异国陌生的夜景,深浓的黑夜如同一片无垠的大海,绵延的街灯是起伏的浪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