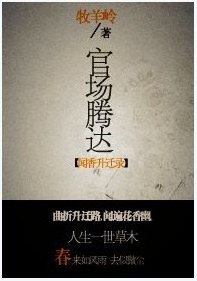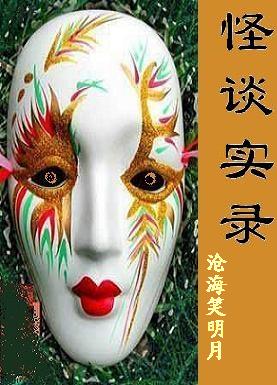风颜录(女强)-第40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帝少姜只是看了一眼他呈上的还未开封的信,起身,“不必看了。无非是求一人活命。”
“一介痴傻妇人而已,准。”
檀渊应了声是,陆敏青已经明白过来。那个只身亲赴北境的兵部侍郎已经回不来了。
陆敏青眼波一转,余光里是帝少姜冷然不动的侧脸,表情依旧如皑皑冰雪不识烟火般漠然,他心里突然涌起一种痛恨来。这样的人,实在已不能用恶毒来形容了。
可那素日妖娆放荡的青年想到此处,却仍旧笑如芳蕊绽香,隐隐有种讥讽,“你肯成全,别人却未必认为那就是恩赐。”陆敏青冷冷说了一句,眼里那女子无动于衷的表情愈发刺目,“那个女人并非癫狂,却装疯卖傻数年骨肉亲情也不顾念,居然只为成就和顾清远的一段孽缘。”
“情之一字,即便你贵为天子,也无法伸手操控。”
他见不得这女子视情爱如无物的冷漠,见不得她自以为一切皆已洞穿堪透的难以触动,心底的恨不全然是恨,不过是因为识得情味后略有同情却愈发焦灼绝望起来。人之一心本来难求,何况追寻魔物的钟情?那一副从来只会践踏他人情意的表情,如何不让他心生恐惧和忧郁?
可即便他这情绪外露的如此明显,那人也不过淡淡转目,毫无意义的一句“或许”既不赞同也不反驳。那些话没有引起她注意的价值。
帝少姜似有所思的与陆敏青擦肩而去。
离房门不过几步的距离,外间却有人来报。
明氏最小的女儿,兵部侍郎的夫人,那个疯癫的妇人,在听闻自己丈夫于明相身死第二日自刺身亡的消息后,沉默而安静的自缢于牢底。
她不屑独活。她心知他必死。
情之一字,无非如此。
帝少姜闻讯顿足。陆敏青挑唇轻笑,“你看。”欣喜恍若见到了一朵花开。似乎在向她证明着什么。
帝少姜略有讶异的侧目看了青年一眼,檀渊沉默屏息站在她身旁。
“确实如此。”帝少姜不痛不痒的说了一句。“迷乱背离理智,沉醉如同引颈就刀。”她如霜冷长河的目光轻轻落到青年身上,檀渊上前打开门,陆敏青听见她依旧冷淡的声音充斥冷眼旁观的冰寒,“赞誉或者指谪,不过多余。陆敏青,你的变化很有趣,可惜,不足以改变我的初衷。”
一个在风月场逍遥混迹多年的浪子,一个心含毒液如蛇蝎的妖孽,一个游戏情爱负心薄幸之人,却开口指责起别人的无情,居然变成了如今这样的模样,如何能不有趣?
但也不过有趣二字而已。
陆敏青看她冷漠背影,心下那股四处冲撞的灼毒,似被寸寸冻结,终究化成了阴寒无比的恨意。
赞誉必出自真心,指谪却源于期盼。如果不是保有希冀,难道陌生人会来横加干预,妄图你成为某个模样么?
“帝少姜,你不懂情。”尽管你自诩无所不知。
☆、互为鸳盟
新皇登基,太渊城主朝贺。
奉净暂代城中职务,城主独身赴京,天黑歇在璇玑阁。
第二日迦纳一身白衣,怀揣城主印信入宫朝见女帝。期间与那龙椅上的女皇目光一触即离再无神交。傍晚迦纳再入禁宫,帝少姜正登临重华台。
迦纳望了一眼台上迎风而立的女帝,大理石筑就的高台上白玉雕柱,栏杆较低矮,那黑衣的女帝正从台上俯视两袖飘飘行来的太渊城主,目光中说不出的冷意。她四周遍布御林及侍卫,个个身躯笔直如杨,气息稳健。
迦纳青墨色的眼目微微一转,目不斜视拾级而上。
台上的帝少姜倏忽开口,声如冰封,“朕号令之下莫敢不从,你自认本事举世无双可抵得过万箭攒发?”
像是印证此话,台上玄衣玉冠的女子扬袖,四周待命的御林、弓箭手齐齐出动,撘弓拉弦气势紧凝。
迦纳微微一笑,将那冷喝听得分明,脚下却不紧不慢继续走着,似是浑不在意。
“殿下当初贵为亲王便身负盛名,如今继业登基是为明君,怎会无故对子民痛下杀手?何况……您不是一直厌恶胜之不武么?”太渊城主微笑回应,微曲的长发晃动,白羽泓影般的身姿清雅高洁,尽管那话并不高声,却明晰而不容错听的落入台上之人的耳里。
“束缚的手段么?果然活得愈久胆子就越小,白肉枯骨也配叫嚣作乱?!”帝少姜神色阴恻,冷笑一声,“我倒要看看,谁更副那怪物的盛名!”挥袖间御林弓箭手齐齐退去。
迦纳目中几不可见的滑过冷光,但那阴冷瞬息散去,他登上重华台,女帝的表情像是从未有过刚才那样的诡谲莫测,依旧如平日的雪冷高漠。
帝少姜像是未显出过杀意般,脸色冷淡的斜睇了一眼前来的宗师,“何事?”
“请陛下践约。”也似无事发生般,迦纳拂指掠过衣袖,青墨色的双眼温凉,目中浸着世人熟稔的悲天悯人。“陛下曾应允过的比肩之人,老夫为门下弟子索约,请陛下实现昔日的诺言。”
“呵。”那女子低笑一声,连声音也似覆了层霜雪,寒意欺面而来。“奉净的弟子幽篁?”
“不。”出乎意料的,迦纳否认了人选,“右相公子才是最佳人选。”
帝少姜侧目,瞳中深处的冷意更甚,太渊城主叠手笑如拈花,“幽篁儒弱且心不甘情不愿,而颜烬阳已入我门下。”
女帝不动,漆黑双眸宛若冰凝。
“好得很。”良久她才说了句,面上斗得绽了一笑,锋利似刀口嗜血。
☆☆☆☆☆☆
“颜烬阳。”冷冷的三个字似乎隐藏了其他东西。
“少姜。”长身立在风里的男子白衣如羽,沐浴着月光飘飘而来,闲庭信步,恍若是来赴一场风花雪月。
他提着好酒,几步踩过信道石阶踏进长廊。走到她凭栏而坐的位置便一撩衣袍也盘腿坐了下来。
“你真正喜欢过一个人么?”他的容颜浸在朦胧月色里,几分晦暗沉寂。让出怀中的一坛酒待她接过后,便将手中那坛起封仰头灌了一口,溢出的酒水淌湿了下颚,右相公子伸出雅致如竹的手抹了抹,表情浑不在意地轻问,“真正地,纯粹地,什么也无法计较的喜欢……有这样的时候吗?”
她恍似不曾听见这样的低语,神情冷漠而不应。他便兀自提了酒坛仰头再灌了两口,待低下来,脸颊连同几缕长发都已浸湿,眼目也似沾了水光,静默而缱绻地凝望夜空某处。帝少姜静静看他反常的行径,黑色的瞳孔里倒映不出任何色彩,院中的月光只衬出她霜雪一般的冷然。
“不愿意回答么?”他侧过脸来微笑,漂亮的眼光彩迷叠,幻出无数种缥离,“还是说不敢回答这样的问题?”
帝少姜微微皱眉,子夜一般的眼睛仔细打量了面前这个人,良久像是看穿什么,冷淡的转开目光不予理会,起手开了那坛酒饮了一口便丢在身旁,靠在栏杆上闭目似是休憩。雅致讲究的如同身边空无一物。似乎任何事都无法影响她一贯绝无差错的自制。
你分明什么都知道。颜烬阳暗自叹息。五指紧紧抓住酒坛边口,突然间失去了言语的兴趣。可他还是笑,笑的仿佛自己刀枪不入,视线一直流连在那张脸上试图寻找自己熟悉的点滴。
“不屑回答?”颜氏公子垂眉,手指轻缓摩挲着酒坛,“也对……你从来半分不愿理睬这些。儿女情长,只增累赘。”
那人浴着投进廊下的月光,闭目冷淡的模样让人以为她天生没有痛觉怜悯。颜烬阳叹息,“我有过的……”
“不止一次的,真正的,纯粹的,什么都无法思考的喜欢。”淡色的唇小小的掀了弧度,“你不懂,帝少姜。有时候,情到深处的绝望令人无法回避和遗忘,便只能选择成恨。”
“还不愿承认么?”眉目如画的公子朝她靠近,一字一字平静地吐出,“你欠我。”
这样的话一落,那女子猛然睁眼。
属于她的视线慢慢地调转投注于他的双目,颜烬阳清晰的看到她细长的眼突然眯起,那一瞬间如一线夜空混沌里突然劈出一道雪亮的冷电,照见的分明是浓郁的杀意和仇恨。
是令人不寒而栗的怒气。仿佛暗夜里雪亮的野兽的眼睛。
“即便你如今手握天下,”公子烬阳对她的杀意视而不见,“你还是欠我。”
“帝少姜,你欠我,一世孤独。”
“那么,你是准备好了要揭下脸上的面具了么?”她这样问。
唉……他仿佛听见心中有这样一声叹息,绵缓似钝刀慢慢在灵魂里拉出长长的伤痕,却仍旧笑着摇头回答,“我不敢。”
不敢就如此的与你直面,因为在此刻我不是别人,只是颜烬阳而已。
若就此直面,我还能是这世上的谁呢?
抛开怀里的酒,他反问,“你又敢揭下你的与我直面么?”
“又有何不敢?”她冷笑,“这些还能动摇到我?”帝少姜的表情冷峭而冰凉。
果真是什么时候都能冷血的下来的人。那公子摇了摇头,“不用了。我不想连今夜都失去。”指尖扣紧,他笑的嘲讽,“如果活不过明天,至少要保证今夜还能尽兴吧。”
这话何尝不是一种试探。
他们到如今,已是真的知根究底,只是维持着薄弱的不拆穿罢了。
他准备未讫,一切尚未完满,本来就是铤而走险出不得一点纰漏,如今他一切又已被她知悉,无异于将软弱而尚无反搏之力的自己送到了对方手上。本来就是一场玩命的赌博,赢了一本万利,输了永不翻身。
如果那一天到来,还能保全情意的话……这不过是对某人尚有情念的希冀罢了。
已经没有挽回的余地了。
“终有一日你会明白,不过是情之一字罢了。”他笑,觑见远远的一边,沉绛色衣衫的青年男子转头走得决绝冷寂,恍若正独自踏进冰雪万丈的荒芜世界。
右相公子虚无的笑意淡去,垂目看自己光洁毫无痕迹的掌心,空泛中某种怅惘浮上心头。
遇上你,生生是场劫。溃败如山倒,命运照见我阴暗绝望的心。怎能不嫉妒到发狂,怎能不记恨他人的幸运?
“我恨只恨,你从来都看不见我。”
☆、情之见相
“我信你,帝少姜。一直信任着你。那么你呢,你信任我么?”
颜烬阳低声寻问,面上带着她看不懂的表情。也许不是她看不懂,而是他将所有的情绪都已隐藏,即便能耐再大的帝少姜也无法捕捉到一丝一毫。
怎么可能信任?这种看上去莫名其妙必定要投注真实感情的问题又怎么能得到回答?难道忘了,这女子从不会对需要引动情愫的存在关注半点?
她根本就没有可以支付的情感。即便有,也会不屑地自己摧毁了丢掉,免得影响了自己一贯的从容。
这样看着她的男子只好自言自语,独角戏一般的寂寥。
“你信任过别人吗?”颜氏公子再次问,对上她冷凝静滞的眼目。总是问多答得少,她只有极少数的时候才会开口,冷漠的吝啬言语。良久他又自己转了话题,“我知道你提过一个名字。”
她的目光不移不动的注视他。颜烬阳的脸上光景朦胧,恍似沉醉在迷梦,“霍希。”他吐出令她微微动容的名字。
终于还是有所触动。颜烬阳弯唇而笑,挥墨泼纸般赏心悦目,似乎连天光都因这一笑而耀眼,“第一个问题和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