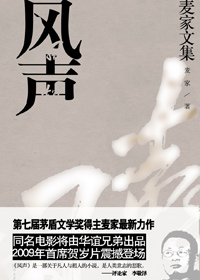遥远的回声-第22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学了,也有可能蒙德回来后和他一起喝酒去了。他并不因为自己被卡文迪什骚扰了,就担心基吉也会发生什么。
亚历克斯给自己准备了一杯咖啡和一大块吐司。他坐在厨房的餐桌前,面前放着听讲座时写的笔记。他一直想对几位威尼斯画家作出区分,今晚的幻灯片让他理清了思路,抓住了重点。他正在笔记本的空白处写字,歪呆欢蹦乱跳地进来了。“喔,看我今晚过得多开心啊,”他兴奋地说,“劳埃德对《以弗所书》的研究真是太有启发意义了。他从文本当中读出了多少意义啊!”
“你过得那么愉快,我很开心。”亚历克斯心不在焉地说。自从和他的教友混到一起后,歪呆每次回来总是如此风风火火,从不例外。因此,亚历克斯从不特别在意。
“基吉在哪儿?还在工作?”
“他出去了,不知道上哪儿了。如果你还要烧水的话,那我再喝一杯咖啡。”
水壶刚放到灶台上,他们就听见前门开了。让人吃惊的是,只有蒙德一人进屋,没有基吉。“你好,陌生人,”亚历克斯说,“她把你扔出来了?”
“她要赶着写论文。”蒙德一边说一边拿了个杯子,往里面加了点咖啡,“如果我留在那儿的话,她一定会抱怨到早上,那我就别想睡觉了,所以我觉得还是加入你们为好。基吉去哪儿了?”
“我不知道,我又不是他的保姆。”
“《创世记》
第四章,第九行。”歪呆得意扬扬地说。
“老天爷,歪呆啊。”蒙德说,“礼拜还没结束啊。”
“上帝永远不会结束,蒙德。我也不期望像你这样浅薄的人会明白这一点。虚假的上帝,这就是你所崇拜的。”
蒙德笑笑:“也许吧,但她真的很棒。”
亚历克斯哼了一声说:“我受不了了,要去睡了。”他撇下还在争吵的两人,回到了完全属于自己的那间安宁的小屋。卡文迪什和格林哈尔希搬走后,没有人再搬进来,所以亚历克斯搬进了卡文迪什的房间。他在门口停下,瞥了一眼音乐室。他已经记不清上一次他们四个人坐在那儿创作音乐是什么时候了。这个学期之前,四个人没有哪一天不挤在这个小房间里玩上至少半小时的音乐。可如今这样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同样逝去的还有彼此间的亲近感。
或许这种情况是伴随人的成长自然而然出现的,但亚历克斯却更相信是因为罗茜的死让大家更深入地了解了彼此。目前看来,这不是一段有教育意义的经历。蒙德完全把自己封闭在了自私和性当中;歪呆沉迷于另一个世界,这个世界的语言叫人无法理解;只有基吉还与自己保持亲密的关系。可现在连他也神秘失踪了。而在这一切的背后,一种相互猜疑的不和谐气氛正侵蚀着他们的日常生活。
一半的自己希望一切都能回到过去的正常状态,而另一半则明白,有些事情,一旦破碎,无论如何都无法恢复。想到恢复,他记起了琳,脸上不禁露出笑容。这个周末他要回家,要和琳到爱丁堡去看一场浪漫喜剧电影,这是恢复正常生活的开始。两人之间默契地认为不应该去柯科迪,那里有太多恶毒的流言。
但他觉得应该告诉基吉,他今晚就打算告诉他。但是,他需要等他回来。
基吉愿意倾其所有以脱离此刻的处境。他被关在地牢里已经好几个小时了,冰冷的空气刺入了他的骨髓,地上的一摊尿液已经结成了冰。可双手到现在还没有挣脱开。手臂和大腿上感到一阵阵的麻痹和痉挛,痛得他不时发出撕心裂肺的喊叫。最后,他感到绳结有所松动了。
他越过尼龙绳抓着下巴,头用力地摆动。绳子又松了许多,孤注一掷的努力让他产生了幻觉。他向左边一扯,又朝后面一拉,他反复这样,直到绳子最后松开,他才放声大哭。
第一个难关度过后,接下来的就容易多了。他的双手一下子自由了,虽然还觉得麻木,但总算自由了。手指冰冷,肿得如同超市里的腊肠,他把手伸进夹克,藏在胳肢窝下。他忽然记起寒冷是思想的强敌,会让你的脑筋放慢速度。
他不断地回忆和运动。现在他的手臂可以自由活动了,他可以在原地小跑。此刻,他希望自己有吸烟的习惯,这样他身边就有火柴或者打火机了,可以驱散这恐怖的黑暗。“官能被剥夺了。”他自言自语说,“打破静默,和自己说话,唱歌。”
手上如针刺一般,疼得他不停地扭动身体。他伸出手,剧烈地摇晃着,左右手反复地互相按摩,渐渐有了感觉。他摸摸石壁,庆幸还能感觉到粗糙的砂石。他担心自己的手因为血流不畅会造成永久损伤,手指依然红肿、发麻,但至少有了感觉。
他支撑着自己站起来,慢慢地抬起一条腿开始小跑。脉搏渐渐加快,恢复正常的速率后他就停下脚步。他想起自己痛恨的体育课,那个虐待狂老师和没完没了的训练、越野和橄榄球。“运动加回忆。”
他能活下来!也许。
清晨来临,基吉还是没有回来。亚历克斯担心地走到基吉的房门口,人不在。很难断定基吉是不是回来睡过了,因为开学以来基吉的床从没收拾过。他回到厨房,看见蒙德正埋头喝着一大碗椰汁爆米花。“我很担心基吉。我想他昨晚没回来。”
“你可真像个大妈,吉利。难道你没有想过他也许正和别人睡觉吗?”
“我想他至少会说一声的。”
蒙德哼了一声说:“基吉不会。如果他不想让你知道的话,你永远都不会知道。他可不像你我那样活得那么透明。”
“蒙德,我们生活在一个屋檐下多久了?”
“三年半了。”蒙德看看天花板说。
“基吉有多少个晚上是在外面过的呢?”
“我不知道,吉利。你不觉得,我自己也常常不在大本营吗?我可不像你,在这四面墙之外我还有自己的生活。”
“我可不是和尚,蒙德。但据我所知,基吉从未彻夜不归。我担心是因为不久之前歪呆还被达夫兄弟打得不成人样。昨天我也被卡文迪什和他的托利党朋友死缠着不放。万一基吉也被人缠住了呢?万一他进了医院呢?”
“万一他和人搞上了呢?听听自己说的话吧,吉利,你啰嗦起来真像我妈。”
“操你的,蒙德。”亚历克斯抓起自己夹克朝大门走去。
“你去哪儿?”
“打电话给麦克伦南。如果他告诉我我听起来像他妈,那我就闭嘴,行了吧?”亚历克斯砰的一声关上门走了。他还有另一层担心并没有告诉蒙德。万一基吉出去猎艳被抓了呢?那就真是个噩梦了。
他来到行政楼的电话亭,拨通了警局的号码。让他吃惊的是,电话直接转给了麦克伦南。“探长,我是亚历克斯?吉尔比。我知道自己可能在浪费您的时间,但我很为基吉?马尔基维茨担心。他昨晚没回来,这可从来没有过……”
“自从麦齐出事之后,你就感到不安了?”麦克伦南说。
“是的。”
“你现在在法夫园吗?”
“是的。”
“别走开,我过来。”
警察如此重视,亚历克斯不知道是该感到安慰还是担心。他心情沉重地回到屋子里,告诉蒙德警察会来。
“让他那张丧气脸走进这屋子,真是要感谢你了。”蒙德说。
麦克伦南到的时候,歪呆也来了。他摸摸自己尚未痊愈的鼻子说:“这次我和吉利站在一边。如果基吉和达夫哥俩缠在一起的话,他现在肯定躺在重症监护室里。”
麦克伦南仔细地询问了亚历克斯昨晚发生的一切:“你不知道他可能去哪里了?”
亚历克斯摇摇头:“他没说要出去。”
麦克伦南狡黠地看了亚历克斯一眼:“他是去找男色了,你知道吗?”
“什么找男色?”歪呆问。
蒙德没理他,盯着麦克伦南说:“你在说什么?你说我朋友是个变态?”
歪呆看上去更糊涂了:“什么找男色?你什么意思,变态?”
愤怒的蒙德转过脸对歪呆说:“找男色是同性恋做的事。在公厕里搭讪陌生人,然后和他们乱搞。”他用大拇指指指麦克伦南,“鬼知道为什么,这个警察认为基吉是同性恋。”
“蒙德,别说了。”亚历克斯说,“这个话题我们一会儿再说。”亚历克斯充满威严的口气让另外两人大吃一惊,话题的转换让他们摸不着头脑。“有时候他会去爱丁堡的一家酒吧。在圣安德鲁斯的时候,他从不提起此事。你觉得他被捕了吗?”
“我来之前查过拘留记录了,他没落到我们手上。”话音刚落,他的对讲机响了,他走到大厅里去接听。他的话传到了厨房里。“城堡?你开玩笑吧……我已经猜到是谁了。叫救火队赶去。我们在那儿碰头。”
他回到厨房,显得有些担心:“我想他出现了。我们接到城堡那边一名导游的报案,他每天早晨都要巡查,他打电话告诉我们有人在瓶形地牢里。”
“瓶形地牢?”三个人齐声说。
“那是塔楼地下的岩石里挖出来的一个地方,形状像个瓶子。人一旦进去,就出不来了。我得赶去现场看看情况。我会派人告诉你们事情进展的。”
“不。我们也去。”亚历克斯坚定地说,“如果他整晚都被困在那儿,他一定需要朋友。”
“对不起,小伙子们,你们不能跟来。如果你们自己去的话,我会留话让他们放你们进去的。但我不想让你们搞乱救援行动。”说完他就走了。
麦克伦南一走,蒙德就追问亚历克斯;“你到底什么意思?用那种态度堵住我们的嘴?找男色是什么意思?”
亚历克斯避开他的目光说:“基吉是同性恋。”
歪呆简直难以置信:“不,他不是。他怎么可能是同性恋?我们是他最好的朋友啊。”
“我早就知道。”亚历克斯说,“他几年前告诉我的。”
“好极了。”蒙德说,“谢谢你告诉我们,吉利。‘有福同享,有难同当’这句话算是到头了。我们两个还不够资格知道这事是吧?你知道是天经地义,而我们两个没有权利知道我们最好的朋友是同性恋是吧?”
亚历克斯逼视着蒙德说:“通过你们俩这般大度和平静的反应来看,我肯定基吉的决定一点没错。”
“你一定搞错了。”歪呆依然很固执,“基吉不是同性恋,他是正常人。同性恋有病,他们是变态,基吉可不是那样。”
突然,亚历克斯觉得受够了。他很少发火,但一旦爆发,就将惊天动地。他的脸刷地一下涨得通红,手掌猛地拍在墙壁上。“闭嘴,你们两个真让我羞于同你们为友。我不想再从你们嘴里听到那些充满偏见的词语。基吉十年来一直很在意我们三个,他一直是我们的朋友,他从来都和我们站在一起,从来没有让我们失望过。他喜欢男人不喜欢女人又怎么了?我才不管。这并不是说他对我们三个的爱等同于我们对女人的那种爱,也不意味着我在洗澡的时候还要时刻防范自己的背后。他还是他,我依然像兄弟一般地爱他,依然用我的生命来信任他。你们也应该这样。你——”他用手指顶着歪呆的胸口说,“你把自己叫作基督徒,却对一个抵得上十几个宗教怪人的人妄加评论。你不配做基吉的朋友。”他抓起自己的大衣。“我去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