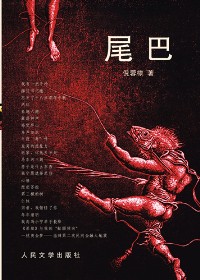尾巴-第14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因为礼拜六要补课,我不再接到周末的紧急任务。有时若心情好,就去陈琛家下几盘五子棋,说说学生会里的事情。
这一切便是我仅有的娱乐活动。
然而那天我补习完毕,在回家吃午饭的路上却鬼使神差地拐进了一家新华书店,想淘一本市面上难寻的外语辅导书,大海捞针了一番终无结果,正要转身离开,忽然一只手搭在了我的肩上。
我扭过头,然后呼吸一紧。
是王丰。
从年初“马可尼”落网转学到今天,已经有两个多月,按理时间不算很长,然而我却很难将眼前的男生同昔日的3班体育委员联系起来:面有菜色,眼眶凹陷发黑,面颊消瘦许多,头发凌乱,像是睡觉起来之后丝毫没有梳理,至于一身衣服,虽然干净,却总感觉古怪,好像是个空架子。
他的变化实在太大,也难怪我进书店的时候竟然根本没有察觉到。如果不是因为以前十分关注他的一举一动,我走在马路上可能一下子都认不出来。
那个曾经见义勇为的短跑健将,不复存在。
王丰将我暗怀鬼胎的愧疚和心虚错当成了意外邂逅的单纯诧异,苦笑了一下,讲:你好,你是以前7班的林,林……
表面上我和王丰都属于班干部,互相脸熟却谈不上真正的认识,于是赶紧自我介绍:林博恪,我想起来了,你是南蕙他们班的体育委员吧?
对,对。他说,然后惭愧地纠正:现在不是了。
我点点头说:知道,知道。然后岔开话题:真巧,居然在这里遇到,你……最近还好吧?
其实我知道王丰的日子是不会好过的。他后来转去的是一所寄宿制中学,据说前身是教会学校,地处偏僻,四围高墙,校风严谨,一个礼拜五天学生是不能出学校的,过着真正意义上的苦行僧生活。
果然,王丰的脸上浮起一种难以言说的表情,这种回忆的表情我只在纳粹集中营幸存者的纪录片里看到过,可他还是搪塞道:马马虎虎吧。
我深知内幕,不愿多问,正不知道怎么摆脱目前的尴尬局面,他却先开口了:这个,其实,我还想请你帮我一个忙。
什么忙?你尽管说。
他似乎在吐字出口的最后一刻还在犹豫:能,能借我五块钱么?
搞了半天,原来是借钱。五块钱对我来说不是小数目,可对王丰来讲可能更是天文数字吧。假如我没猜错,和当时大多数对早恋子女严加管束的父母一样,他们肯定大幅度削减了王丰每月的零花钱。经济制裁无论在什么年代什么问题上都是惩罚的杀手锏。那个曾经花钱赌球、在放学路上可以随意买饮料买报纸的王丰,现在宛如乞丐。
王丰说:不瞒你说,我现在每个月是没有零用钱的……但我会想办法还你,真的。
我没敢去看他诚恳的眼神,手有些颤抖地去翻我的口袋,那里有几个一元钢铡,另外我的书包里还有几张一块钱的纸币。
王丰面色回暖,不知是因为欣喜还是更加愧疚,补充道:我就是想买份《体坛周刊》,很久很久没看了,看完了你拿着,你再留个地址,一有钱就还。
我说不用急着还,报纸是你的,何必给我。
他却急了,讲:你不明白,我不能带回去,看完扔了太浪费。
我拾起翻找零钱的目光,惶恐而不解地看着他,手中的钢铡微微发凉。对方神色疲倦,语气中带着麻木和妥协,向我解释说:每次回家,他们都会搜我的口袋和书包。
5
邂逅王丰后的星期一,我被请到教导处谈话。
罪名是抽烟。
香烟是当天上午我在老师办公室得到的,金上海,就摆在我们物理老师的办公桌上,距离我们班的那叠作业本只有十公分,大概是哪个熟人给他的,没来得及抽。碰巧物理老师走开了,我趁着拿作业本的时候将它夹在手指之间带了出去,神不知鬼不觉。
至于抽烟的理由,自然是迫于精神压力。那天王丰问我借钱之后买了本《体坛周刊》,然后立即如饥似渴地翻阅,宛如在沙漠里苦熬了三天的幸存者找到了一大片绿洲。看完之后他依依不舍地将周刊给了我,留下了我们家的地址,告别。
当然,我给他的地址是假的,他不必还钱,真正欠了对方的人是我。这天夜里,久违的失眠和我重逢。我想到当初王丰见义勇为抓小偷的新闻报道,那个被窃的受害人是一个六旬老太,小偷偷走的是她的退休工资,幸好被王丰追了回来,才没让老人急得犯病。我母亲当年也有这样的遭遇,只是她没能遇到王丰这样见义勇为的好心人,那笔丢失的工资让她哭了两天两夜。
辗转反侧了一个周末,当我来到学校时,眼圈暗黑,犹如国宝。
中午午休的时候,我把那份《体坛周刊》悄悄带进图书馆,放到了阅览室的期刊架子上。然后走出学校,用身上仅剩的一块钱买了个打火机,躲在社区小花园的树林子里第一次尝试香烟的味道。
抽烟的那种感觉,一塌糊涂,却丝毫减少不了一个告密者和跟踪者的苦闷。反倒是身上这股味道暴露了我的行为,然后引来了其他的告密者。
我在掩盖烟昧方面是个雏儿,不像班磊那样经验丰富,而我抽完烟回到学校之后竟然傻到忘记漱口,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回教室,和不下四五个干部、学生说了说工作或者交作业的事情。结果不知道是其中哪个人向老师举报,十五分钟之后我们班主任就要我去教导处一次。
事已至此,我心倒坦然,走在路上步履平稳。
让那个告密者大失所望的是,在那里单独等着会我的并不是一脸凶相的教导主任螃蜞,而是地理老师龙虾。
——抽烟的滋味如何?
龙虾的开场白总是很平缓,其实他任何时候说话都这个语调,波澜不惊。从没有人见过龙虾发火,但我总觉得即便他发火,也不会和平时的风格有很大差别。见我杵在那里不说话,他也没有逼迫,而是拿起办公桌上的一盒红双喜,那显然是螃蜞老头把这个办公室暂时让给尾巴负责人时忘记拿走的。他从里面抽出一支,却没点着,而是放在鼻尖下面闻味道。
我不喜欢红双。
他自言自语道:有股酸味。然后他走到桌子后面,轻轻坐下来:你知道么,举报你的那个学生说,他这辈子还从没在一个品学兼优的班长嘴里闻到过烟昧——我们好像很久没有谈论过任务之外的东西了,来,坐下,告诉我出什么事了?
我犹豫了几秒钟,在那把颇具血泪史的“教导处审讯椅”上坐下,但是却没有其他人那样的恐慌,缓缓道:是王丰,他察觉到我们的存在了。
那天王丰用我的钱买了《体坛周刊》看完,交还给我的时候艰难地战胜了内心的踌躇,问:对了,1班的那个女孩,巫,巫梦易,你知道么?
我点点头。他终于还是问了,显然他们两个在那之后没再有过联系。
王丰:她现在还好么?
我:不知道,我们班和1班不在一层楼,很少看到她。
这其实倒是句大实话,巫梦易自从爱情友情亲情三方面均受到打击之后,十分低调,连原本和外校笔友的通信都断掉了。但后来我还是见过她一次的,那是我刚进入学生会组织部不久,某天中午在西教学楼的一楼大厅,当时快上课了,人很少。巫梦易捧了一大摞生物作业本在大厅台阶口摔了一跤,伤得不重,只是作业本撒了一地。她就一本一本地把本子捡起来,头压得很低,不去看周遭的世界,好像这世界上就她一个人了,而事实似乎也的确如此。因为碰巧几个学生会的人也在那里,有几个还是她曾经效力的宣传部的人,但他们只像观众和过客一样,因为学生会的一个指导老师和高二年级副组长也在场。而且她捡到一半的时候,那群人正好散掉,巫梦易昔日的同事们陆陆续续从她身边走过,上楼梯。没有人停下帮忙,甚至没有人放慢过脚步。我走在他们的最后面,发现有本本子就在我脚边,却眼睛一闭,跨了过去,再也不敢回头看。
这就是她现在的状况。
王丰对这一切一无所知,悻悻地“噢”了一声,然后讲:不瞒你说,我总觉得这所学校怪怪的,我和她那么保密,都会被发现,我离开之后经常想,是不是学校里有人在跟踪我们?
我倒吸一口凉气:你是说,老师跟着你们?
不。他摇摇头:未必是老师,做这么恶心的事情,也许是学生——搞不好,还是学校派来的。
我勉强挤出一丝笑容:别开玩笑了,怎么可能,学校派人跟踪学生回家?这说出来不太现实啊。
话是这么说……他挠挠头,不知道是因为我借给他五块钱,还是他从未想过我就是那个可恶的告密者,最后不忘叮嘱:总之,万一,你也那个的话,千万要小心呵。
我点点头,说我自然会小心。
只是,和他所期望的那种“小心”很不一样罢了。
——那么,这就是你抽烟的原因?
——我只是觉得,我把他们两个害得太惨了一些。
——你大错特错了,我们是在帮他们。
龙虾说着从椅子上直起身体:我知道这个世界有时候看起来的确可笑,十八岁之前和十八岁之后,很多事情就有截然相反的待遇,抽烟是这样,恋爱也是这样,“春天的时候,不要做夏天的事情”,这就是原则,我们的原则。
我当然知道这个“春夏”理论,我从没有怀疑过它的正确性:那我们是不是有些过火了?
过火?龙虾扬扬眉毛,拿起那支红双喜在指间把玩:你记得我的办公桌上,那块玻璃下面压的照片么?
他说的是“地理兴趣小组活动室”的那张桌子,的确用大玻璃压着一张照片。他是那种五官不显老的人,看上去四十出头,其实已经五十多了,我们一直以为照片里的那个十四五岁的女孩是他女儿。
谁知他却微微摇头:那不是我女儿,是我以前的学生。
6
龙虾在调来我们学校之前,曾在邻区一所普高执教。
当时他教高一和高二的地理,共有七八个班级。其中有个高一女孩是他大学同学的独生女儿,所以龙虾对她很照顾,两个人的关系特别好,女孩也不把他当成纯粹的老师。
那个女孩活泼开朗,聪明伶俐,并且敢作敢为。有一次学校内部行政层面的钩心斗角,差点使龙虾成为教学评估之类的玩意儿的牺牲品,眼看可能会和其他几个老师一起停职下岗,或者转去郊区乡下的三流学校。关键时刻,那个女孩和几个班干部豁出胆子敲开了校长办公室的门,交给他一张有两百个学生签名的请愿书,还打电话给报社的记者,这才“力挽颓势”,没让他们几个老师调走。
因为这个缘故,龙虾也不拿她当小孩来看待。那时早恋的势头还没一九九七年这么猛烈,还处于萌芽的初级阶段,但这个女孩却属于先驱人物,有了秘密男友。这件事情龙虾是有所察觉的,但起初并不在意,只是暗里旁敲侧击让女孩注意一点。女孩向他保证说不耽误学习,龙虾也就眼开眼闭,没跟她父母说。
后来龙虾到内陆地区支援教育建设一年。结果才去了四个月,这个女孩就自杀了。走之前留下韵遗嘱表明是遭人抛弃,遂自寻绝路,并且公安局尸检时发现她已怀孕一个半月。由于她生前从未透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