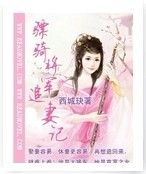骠骑行--霍去病-第53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惊讶的表现了。不过,这样的物件令我心中的疑团又深了一层,我对这洞里的人物来历有了一个大胆的猜测。===============丝衣拂地,黑发披垂,随意端坐在一张薄薄的丝毯上。面前的女子飘逸如青莲,神秘若幽兰。我好久没有见到这么身形高贵典雅的女子,心中只觉得她必不是普通人。去病冷冷地站在我身边,看到身份不明的陌生人,他有一种天生的防备心。我也一样,拉着他的手看着那女子。那女子约有二十七八的样子,以满含兴趣的目光打量着去病。她的声音打破了此时的僵持:“原来是大汉朝的骠骑将军?”不等去病回答,她又转头看着我,看着我们紧连的双手:“这位姑娘叫什么名字?”她看着我的目光甚为古怪,探究中又有几分惊讶的表情,就好像她久已寻找的一个谜在我身上找到了一般。我被她的目光看得不太耐烦,侧过头让去病去应对她。在这个河西出现这么身份难辨的女子,去病总要想法子打发了才好。去病的神情更为特殊,他紧紧盯着那女子,我捏捏他的手指他竟然毫无反应。我不动声色地观察着他们,相信答案立即就会出现在他们的对话中。那女子说:“霍侯爷是看着我有些面善吧?”“你……你是她?”去病终于开口了,那有些紧张的口气让我感到陌生,仿佛那个女子可以对他构成什么威胁,这种状况真是太特别了。女子笑了:“我是谁?她又是谁?”去病低了一会儿头:“你不是她,她不可能是你。”“我若真是她,你会怎么样?”女子故意蹙起眉尖,问他道,说话的样子倒像是一个亲切的长辈在与小辈逗趣。我听着他们哑谜般的对话,坠入了云雾中,心中原先对于这个女子的猜测,被去病这番反应搅得一片糊涂。“姑娘!”去病果断地抱拳,正色对她施了一个半礼,“此处汉匈正在交战,你继续滞留恐怕会有危险。姑娘要去何处,我可以分派一些人手帮助你。”这句话一出,他干脆利落地摆脱了那点内心的纠缠,礼数言辞皆稳重得体。那女子见他已经把双方的位置摆明了,也收起那点逗笑,随意拂一下袖子:“我能够来,自然就能够去,不劳霍侯爷操心。”我见去病无意再对她抱以恶意,也放松了一点警惕。我看到她的面前散放着一些纸墨用具,尤其是那白生生的纸张,在山洞天顶泄漏下来的柔光中分外注目。我俯下身体,用食指触摸着那纸张:“纸?”这是我在汉朝第一次见到纸张。大约此时纸张并没有发明,我最多只看到一些极其有钱的富豪在丝帛上写字。我看到那纸上还用墨笔画着一些图:“姑娘是个画家?”我知道汉朝的人根本不知道什么叫画家,最多有一些作画的匠人而已。她听着我的话怔住了,半晌才说道:“我不是什么画家,不过确实会略画几笔。”我回眸看了去病一眼,征求他的意见:“我想看看她的画。”去病说:“那就看吧。”我也不经过那女子的同意,拿起一张画,上面一个青年将领,黑发长眉,挺直的鼻梁边目光浑厚:“这是卫大将军!去病你看!”去病也看住了,目光从纸张的左边看到右边,我曾经在端午节的御道上见过卫将军一面,这女子画得极为传神:“画得很像呢。”她的画法与我平时在汉朝的壁画、画像石上看到的人物形象完全不同,用的是一种立体的描绘手法。这一切证实了我的猜测,这让我越发认定她绝非敌人。我索性脱开去病的手,蹲下去一张张翻那些薄纸上的画。我又认出韩说、张汤等几个我有限见过的皇上身边的红人,还有几个我便不大认得了。最后居然还找到了去病的肖像,画上的霍去病,英气勃勃也杀气腾腾,就跟我平常见到的他一模一样。我拿起来问:“能送给我吗?”“这张画得不像,不能送给你。”那女子手中在画着什么,“我再画一张像一些的送给你如何?”我正要走过去观看她作画,被去病拉住:“弯弯,你在这里等就可以了。”这女子能够隔着山洞便能辩明我们的行踪,这给他的印象太深,他生怕她对我有什么不利。我解释给他听:“她能够在山洞里看清楚我们不是什么大不了的,那个……”我指着山洞角落边一个不起眼的青铜物件,“那叫做‘潜望镜’,因为青铜镜子清晰度不够,所以做得太大,要不然我也可能发现不了的。”这在现代,是最简单的光学仪器,去病与这个女子相差了数千年的科学技术,自然不能够看懂其中的奥妙。去病注意地看我手指着的东西,疑光在我身上闪了闪,我也觉得自己有点冒失,不该如此多嘴。那女子道:“弯弯姑娘真是有趣得很。”她将手中的墨笔一搁,“画好了,你拿回去好好保藏吧。”我正要走过去看,去病抢先过去,拿起了那张墨迹未干的画。那女子忍了又忍,还是问了我:“姑娘既然……你怎么会和他在一起?”我说:“我和谁在一起这是我自己的事情。”我掂量着她话里的意思。“对,你自己的事情。”女子说,“我看,霍侯爷和你在一起很开心呢。”那边,正在看画的去病突然冷笑一声:“我是这样的吗?”我凑过去想看个究竟,去病三把两把揉成一团。我惊叫起来,伸手夺过纸团,怒道:“你让我看看再毁也不迟啊。”女子吃吃吃笑了:“我画的是霍侯爷的内心,他怎么愿意把自己的心思让人随意看?”去病涨红了脸:“休得胡言。”他拉着我走出山洞,临走对那女子道:“姑娘,我们大军撤走后,你还是自己留神匈奴人吧!”我担心他再毁了那纸团,将纸团紧紧塞在袖子里,准备等到他不在的时候再自己看看,去病那所谓的“内心”到底被画成了什么,弄得他这般恼羞成怒的。===============短短的午后就这样在这个小插曲中,被无情地消磨掉了。等我们重新来到我沐浴过的小水潭,夕阳已经开始西下。如果,我们两个不那么敏感,也许根本就不会发现这个女子的身影。如果,没有这个女子,那我们现在该做什么了呢?去病一直陷入在深思中,我总觉得他似乎对那个女子的存在有着别的什么想法。我没有问他,问他也没有用。我陪着他安静地回到白桦林,回到山木榉树林,找到坐骑,再陪着他回到我沐浴过的小水潭,找到了我的鞋子。他忽然昂起头,脸上那点沉重的思考已经抹干了,留下一点豁然开朗的神态,微微含笑。我看他神情改变,问他:“怎么啦?”他说:“我终于想通了一件事情,心里觉得很畅快。”是吗?天上的星星一颗颗跳出来,地上的草原一寸寸暗淡下去。我看着去病的脸,他的眼睛很大,清晰地倒映着我的模样。我看到这双眼睛的一边,闪起一个小小的火星。我知道这是他的部队召他回去的信号箭。他的问题想通了,我们的这场约会却应该结束了……战火间隙中,河西何处无战事?我说:“去病,他们叫你回去呢。”“哪里?”他一定是在想那个女人的事情太投入,连部队的信号箭都没有看到。我心中烦闷,随意向身后胡乱一指:“那是不是信号箭?”“什么信号箭?”他侧过头看我身后,笑了,手在我的身旁一捉,“是一只萤火虫。”一点幽绿的亮光在他的指尖闪烁。“河西也有萤火虫?”我站起来,有些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快八月份了,哪里都有萤火虫。”去病跟着我一起站起来,小水潭借着月色映出我们两个身影。仿佛听到了什么召唤,草甸子里的忽然一齐飞出来许许多多的萤火虫!它们在夏夜清明的月光中翩然起舞,那绿色的亮光轻若点絮,闪淡明灭难以捉摸,忽聚忽散如同轻歌曼舞。如此悠游,如此轻柔,在我们的眼睛前飘荡飞舞,星星散落。我们站在万点微茫中,身心都变得如雪花般轻柔自由,仿佛能够随着这万点荧光飘飞起来。他右手托起我的面颊,左手揽住我的腰……我的手臂垂下,袖子里的纸团落入了水中。薄韧的宣纸在水潭中缓缓舒展开来,如一页纯白的羽毛,漂浮在星光如萤,萤火如星的水面上。随着纸张的打开,那纸上的画儿也渐渐清晰。那画面中的霍去病确实画得很失败,一点儿也不象他,难怪他要生气。纸上的他,没有千里疆场的算计,没有万人性命的牵挂。纸上的他,笑得很放松,亦很单纯,如一个普通的初识情爱的双十少年,带着嫩嫩的幸福……宣纸上的墨迹逐步洇开,少年的形象也开始渐次模糊,仿佛被战争的硝烟弥弥掩盖,为他年轻的眉角重新抹上了一层苍灰冷厉。那白纸终被完全浸润,荡荡悠悠打着旋儿落入了深深潭底。独留一抹墨香,天地流芳。
第十七章 朔漠白日青锋寒
广袤朔漠静默如磐,明透如璧的天空上,淡淡的月盘若有似无。上万的铁骑满身热汗,仿佛要将身上的铠甲全部融化成铁水。战马呼哧出沉闷的喘气,在静谧中蒸腾出青色的热雾。战士们身上黑中带银光的盔甲泛着紫微微的血光,这是一路征尘一路杀戮给我们染上去的生命底色。无风的大漠分外枯寂,半垂的旌旗上散发着烽烟的气息,那硕大的帅旗上霍然凛凛,仿佛标枪一般矗立在铁骑的最前方。霍将军一身暗褐色的血衣已经分辨不出本来的色彩,身后万名以上杀气如山的士兵们等待着他的命令。一切,都只等着他……只等着他的扬眉出鞘……所有静谧都将随之消失,这天地都会在他的怒吼中改变颜色!仿佛是感受到了他那引领苍生的豪迈,一股从荒原深处吹来的飓风从我们身后冲奔过来。于是,旌旗向着前方笔直地飘扬,旗帜的绸料在猛烈的风中鼓动起烈焰般的吞吐。所有人的手指都捏紧了自己的武器,屏住了呼吸,无数双血红的眼睛如同心机深沉的野兽,遥望着黑色夜幕的正中心。紫黝黝的寒光从霍将军的刀鞘中缓缓而出……巨大的马蹄声顿时轰鸣而起!成千上万的声音以暴雨骤风般的速度灌满全场,震耳欲聋。霍去病的铁军风驰电掣一般仿佛从地底下冒出来的恶魔之血,泛着黑光,带着杀气,狂烈不羁地滚滚而出,带着雷霆万钧的勃勃雄风长驱而出!黑云一般的骑兵冲击到匈奴人的毡房前时,很多匈奴人还刚刚从睡梦中惊醒。休屠王部在草原上已经几天几夜不断地提高戒备,可是,他们总是需要休息,他们总是需要调整。可怕的汉族军队似乎不需要休息,不需要调整,昨天还在虢勒尔部一场大战,今天已经奔袭到了此处。骑兵队惊裂天云的奔腾中,我和我的保镖们紧紧跟在霍将军身后,他的马蹄向身后刨溅起无数砂石碎块,仿佛锐器一般切割着我们,那猛烈的速度让人根本没有半点可以思考的时间。突然,我的身边亮了起来,狂奔的大汉士兵一起点亮了火把,熊熊烈焰在青蓝色的天空下映出一片血红,仿佛一张撑大了血口的恶兽。风助火势,荒原的大风成全了此时的燎原大火,远远看去,我们不像一支骑兵队,更像是一大片滚动跳跃的地狱之火!“轰!”前排的骑兵队用战马的马蹄将休屠王部的牛羊圈,马场栏全部踢倒,践踏成碎片,紧接着,那火把统统扔入他们的营地。牛羊马群凄烈地惨叫起来,火把上还用了桐油,着了油的羊群仿佛一张活动的火海,冲出了羊圈在草原上疯癫地咩叫着,四处奔突,满身白绒的羊毛成了炙烤它们皮肤的火舌。被火受了惊的马群牛群纷纷越栏而出,在匈奴人的毡包群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