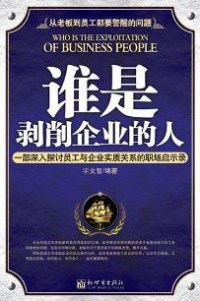谁是敌人-第26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过了几天梁丘华约我到老地方见面,我借口采办办公用品溜到市郊他的住处,他正伏案沉思,眼前厚厚的信纸上只有一行标题:金致厂的污染为何屡禁不止?
我吃惊地说:“前面的事还没了结又准备发动新攻击?点名道姓叫阵讲究的是证据确凿,不然人家会告你诽谤。”
“这个自然。”他摇头晃脑道。
我狐疑道:“又奉到哪把上方宝剑?”
“圣地德曼集团高管。”
我笑了起来:“真幽默,不想告诉我实情是吧。”
他一字一顿道:“这个题目就是他定的我一字未改,这名高管叫韦尔,他和我谈了两个多小时呢。”
“韦尔?”我惊叫道,感觉全被搞糊涂了,“你是说他主动和你见面,让你写一篇揭露金致厂污染问题的深度报道?”
“而且提供所需资料、数据,还答应找机会带我到金致厂区实地考察的要求。”他不紧不慢补充道。
“这,这,这……太难理解了,”我如坠雾中,“总部正组织人手撰写树立集团正面形象的系列报道,怎么可能自己往心窝里捅刀?”
梁丘华两手一摊道:“对此韦尔本人有一个合理的解释……”于是详详细细将前后经过说了一遍。
两天前有人通过医药部门渠道传递信息,说圣地德曼集团有位重量级人物要和他私下密谈。对方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呢?梁丘华左思右想不得其解,但躲下去也不是办法,遂硬着头皮答应了,不过提出地点、时间由他定,对方说没问题一切都好商量。他不客气地将见面地点选择在金华路上一家茶座,对面便是派出所。本以为是场鸿门宴,特意带了把水果刀壮胆,并找来微型录音机藏在上衣口袋中。后来事情的发展证明此举是多虑了,韦尔的态度十分和蔼,称赞他调查全面细致,善于发现别人容易疏忽的细节,是位很有想象力很有前途的记者。梁丘华被夸得摸不着脑袋,试探问你认为我写的东西与事实有出入吗?
这正是今晚要深入探讨的问题,韦尔说,我拜读了这篇报道,觉得文章存在某些不足。
哦?梁丘华问,哪个方面讲得不对?
韦尔沉着有力地说,金致厂实际排污情况比你估计的还要严重!接着列出了另外两条秘密排污渠道,强调说因为排放地点远离村庄,附近荒无人烟,尽管污染程度胜于溱南河却影响不大。当然这只是肉眼可以观察到的,实际上几年来冒着浓烟的两个大烟囱不知向市区排放了多少含有剧毒气体的废气,想到自己也生活在这片天空下,他恨不得每天带消毒面具上班。
身为高管前程和利益与集团荣辱戚戚相关,为什么选择背叛自己的事业?梁丘华沿着思路理所当然问下去。
韦尔掏出一张证件摊在茶几上,面色凝重地说我的另一个身份是国际绿色环保组织成员,保护自然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我可以失去职位失去工作,但不可以失掉自己的良心,自从发现金致厂污染的秘密,我一直暗中观察收集资料,就是想通过舆论将一切真相大白!
“好一段慷慨激昂的演说,我简直怀疑是否出自他口。”我笑着说。
梁丘华旋即播出录音,里面的腔调、语气、用词习惯确确实实是韦尔本人。
“一个忍辱负重的环保人士,你相信他的话?”他问。
我想了会儿道:“据我所知集团高层之间并不和睦,金致厂又是李斯特独自把持,不排除韦尔为了某种目的在李斯特背后捅刀子,我更倾向于权力之争……可作为高管这样搞法似乎太极端太冒险……”
“正确,英雄所见略同,而且两人交换名片后他说的第一句话就让我疑窦丛生,感觉他的来意并不单纯。”他打开录音机,调到开始位置然后播放:
“梁丘先生,晚上好。”
我说:“一句问候语而已,有什么问题?”
他脸色一正:“问题很大,‘梁丘’这个姓非常冷僻,以至于包括报社同行在内绝大多数人都以为我姓梁,时间一长也懒得纠正,一个外国人,凭什么不叫我‘梁先生’?”
“也许替你们穿针引线的中间人告诉他的。”我提醒道。
“那个人向来称我‘梁记者’,嘿嘿,在中南市我至少有六七十位朋友,可知道我姓‘梁丘’的连你在内不超过二十个,”他奇怪地笑了笑,“回到家后我躺在床上想了大半夜,陡然想到其中关节,所以才请你过来,”他突然朝我一指,“毛病出在你身上!”
“啊!”我傻了眼不知从何说起,又好气又好笑道,“你怀疑我是双面间谍,向韦尔通风报信?”
他站起身在屋里来回踱步:“我们之间认识纯属巧合,以你的身份和神出鬼没的行为完全有可能是奸细,不过,”他双手按在我肩上,“我自信这双眼睛不会看错人,梁丘华交的朋友没有孬种,因此压根没有怀疑你,但是你的女朋友——在玫瑰河边钓鱼的女孩,你能保证她没对韦尔提起过我?”
我心头重重一震,隐隐约约悟出点东西,只是还缺少一个关键环节无法连贯起来,想了想说:“此事事关重大,我,我暂时不能回答……”
他截口道:“当然仅仅是猜测之词,我只不过提出自己的想法,真相到底如此需要我们共同努力……”
“我明白。”
他见我无心讨论这个话题,转而兴致勃勃谈起如何利用韦尔进入金致厂区探寻秘密,我画了张图指出几处需要特别注意的地方,两人正趴在桌上研究得入神,安妮打电话叫我立即回单位。
“迟会儿行不行?还有点事没办完。”我说。
“不管多重要的事都得缓一缓,”她语气中透着焦灼,“李斯特要见你。”
下电梯没走几步安妮行色匆匆过来:“快跟我上楼。”
“好端端的怎么想到召见一个办事员,他有与员工谈话的习惯吗?”
“我还想问你呢,最近有无行为不检点或工作协调不力而被投诉?”
我想了想喃喃道:“按说不会,众所周知我在工作上勤勤恳恳任劳任怨……”
安妮摇摇头:“这一点你说了不算,得看李斯特怎么想。”
电梯很快到了九楼,从秘书台向东十多米便是总部最神秘的地方——副总经理办公室,能获准进去的人屈指可数。想到将直接面对深居简出阴险可怕的集团首脑,我有些紧张,深吸一口气,下意识理理头发整整衣领,做出一副镇定自若的样子。
“总经理,我是安妮,岳宁来了。”安妮站在门口响亮地说。
过了几十秒里面才传来一个柔和缓慢的声音:“Let
him
come
in(让他进来)。“
安妮做个请进的手势,并压低声音说:“忘了告诉你,李斯特喜欢员工用英语交谈,如果带点牛津腔最好。”
老天,我的英语口语水平本来就一般般,牛津腔?天津腔还差不多,再说我又不想获得他的欢心。
轻轻推开虚掩的门,踩在松软的地毯上感觉很不踏实,转过屏风,一个宽敞空旷的办公室呈现在眼前,偌大的空间内只有一张老板桌和一排沙发。老板桌背墙而放正对屏风,沙发离桌子差不多有八九米距离,其他竟无一物。两侧墙壁上似乎有点内容,从上而下遮盖着又厚又长的绒布直拖至地,整个屋内光线较暗,办公桌上的一盏台灯灯罩朝外,李斯特仿佛坐在黑暗之中,只依稀看出大致轮廓,无从分辨其面目。
很奇怪,李斯特的工作时间好像不确定,从未和总部员工一起上下班,因此来了这么长时间我居然没见过他一面。
“请坐。”
依言坐到沙发上与他遥遥相对,感觉很不舒服,这使我联想起在派出所实习时常见的场景:审讯员脸色严肃地正襟而坐,两只强光射灯将犯罪嫌疑人紧紧罩住,所有表情眼神的细微变化都在掌握之中。
“你是新员工,因为安妮的赏识才破格调到总部,我注意到员工们反应你工作努力,很多事情处理得非常出色。”
我微微欠了一下身:“谢谢您的鼓励,能得到大家肯定是我的荣幸。”
他好像在仔细观察我,两只眼睛炯炯有神,过了会儿开口问:“你多大了?”
“二十七。”
“对自己现在的薪水和职位感到满意?”
“超过我毕业时的预期,这里工作环境很好,充满进取和向上的动力,而且医药行业在中国有长远的发展前景,我们会做得更好。”
“如果你有要求,我是指个人利益方面,尽管向安妮、约翰甚至我直接提出来,不要觉得唐突,什么事情都可以谈,集团也会尽可能满足,通过协商解决是最好的,明白我的意思?”
开价了,我故意听不懂:“不……不太明白。”
他好像笑了一下:“比如说你可以带着一笔钱,一笔数目很大的钱,用汉语讲叫‘巨款’,到集团在南美、非洲等分部工作,享受带薪假期和优厚的退休金,这么说你清楚了?”
看样子李斯特对我的身份已产生怀疑,因而不惜重金开出大价码试探我的反应,微微一窒,我恭恭敬敬道:“很喜欢南美的风光,我会更加努力,争取早日获得您所说的那些待遇。”
李斯特“嗯”了一声,室内陷入难挨的沉默之中,良久之后突然说:“我们的宗旨是培养有能力有热情并且对集团忠心的年轻人,只要做得足够好一定会得到应有的回报,特别对于你而言。”
“是的,谢谢总经理指教。”我简短地说。
他点点头,过了会儿说:“没事了,你回去工作。”
走出办公室后感觉全身凉飕飕的,这才发现汗水早已湿透了衣衫,虽然只有短短几句话,虽然他的语气温柔得像个女人,却不啻于一场艰苦卓绝的马拉松,我从未经历过如此困难被动的谈话。
安妮一直在等我,见我便问谈得怎样,有没有谈及具体事情。我有选择地说了一遍,她乐观地分析说这是好事,证明李斯特对你的印象不错马上要委以重任,走,找个地方为你庆祝一下。
但愿如此。我懒洋洋道,直觉这场几近于摊牌式的谈话对我并非好事。
在停车场附近遇见温晓璐,叫住我说朋友送了两张音乐会门票,一起去看吧。我犹豫着正待委婉说明情况,安妮从后面过来直截了当地说岳宁没空,晚上我们有安排。
温晓璐冷冷道:“只是建议,没有时间就算了,我无权干涉他的自由。”
“不,你会错我的意思,我并非以上司身份说这句话,没有人能限制岳宁下班后的行动。”
“在我看来没什么区别,”温晓璐针锋相对,“所以我不想说太多,祝你们晚上玩得愉快。”
“不单指今晚,”安妮奇峰突出地说,“以后他恐怕都不能陪你,至于原因不需要我讲得太清楚吧。”
温晓璐脸色陡然变得煞白:“你是什么意思?”
安妮语气强硬地说:“需要我在这里当着岳宁把事情说开?”
温晓璐愤怒地瞪着对方,眼睛里似乎要冒出火来,突然转身驾车飞快离去。
“你们在说什么?”我呆呆地问。
“想知道答案?”
“当然。”
“咱们喝酒去,只要能把我灌醉,”她露出甜蜜而迷人的笑容,“你不仅可以得到答案,还能得到更多……”
“干杯!”我仰头喝掉后倒悬小酒盅朝她亮了亮。
她有些吃
![兽人之谁是雌性?![耽美]封面](http://www.sntxt2.com/cover/1/1518.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