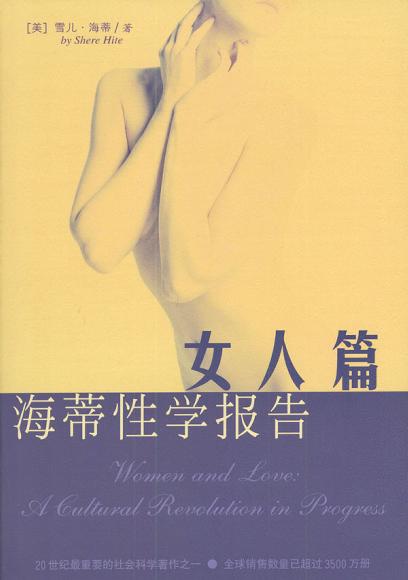报告政府-第40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不正当,而且总是要有人哭甚至有足够的哭吧?这就对了。没看见吗?如今天大地大不如钱大,有些家户相互讨账的争吵越来越多,丧礼上的泪水却越来越少,演员们刚好填补感情空白,洒向人间都是泪,接管了千家万户的悲痛。
他们不仅有一口可以出租的水晶棺材,不仅有布景、乐器以及音响等全套行头,还有表情的专业,很快就练就一套本领,包括催哭、领哭以及代哭的熟练技能。刚才还大唱《亚洲雄风》和《年轻的朋友来相会》,一换曲子,男声部,女声部,预备,走——眼泪说来就来,悲声说放就放,比有些孝子孝女们还要尽责。他们即便有时过于疲劳或者疏忽,忘了哭词,或者哭走了题,但节骨眼上一般不会失手,能准确及时地涕泗交流扑天抢地。男声女声提起来,再提起来,泪水是真的,鼻涕是真的,真像死了爹娘,这一条令人惊奇和满意。他们常常哭得女人们鼻子发酸,连角落里的狗和猫也被折腾出面容凄惶。
哭得好!用本地人的话来说,文艺道场合算,不像和尚道师那样偷工减料,也比老式道场更为现代化。
芹姐有时参加演出,有时也参加哭丧,有时又不见影子,不知去了哪里。她已是半老徐娘,但兰花指一挑,粉面恰到分寸地一倾,手帕在空口划出一道弧线,一开腔还是能令人心动。哀调是她的拿手好戏,能唱出很多套路。“霎时间天昏地又暗,爹爹爹爹你死得惨……”歌剧《白毛女》里的哭诉,有时也能成为临时即兴,一顺心就给你们免费加演。长哭当歌,她手帕捂脸的时候,每一个哭音入腔入调,转上七八个弯,上下游走,牵肠挂肚,酣畅淋漓,完全是创新一代哭风,是孝悌情感音乐化的嘎嘎独造——不愁人们不来围观,也不怕别的殡葬公司来抢业务。凭着这一条,她名角架子还能留下几分。根据明码标价,别人一个“点”要哭四十分钟,她可以少哭一半;别人有时需要披麻戴孝地跪哭,她从来只挂一条黑纱坐哭。如此等等,是一位哭星的特权。
她还有些特别讲究,比如见遗像上獐头鼠目歪瓜裂枣的,就决不出场迁就,而且陪死人不陪活人,卖哭不卖笑,不像有些人什么钱都赚。有一次,一个来喝吊酒的路桥建筑老板不知趣,自称以前是芹姑娘的歌迷,仗着曾经对剧团有过赞助,下巴始终抬得高高的,没等丧礼结束,就要她一起去“卡拉呵嗬(OK)”。她装作没听见。对方后来又请她到包厢吃酒席,谈笑之间,把她的手偷偷摸了一下。芹姑娘本来可以装糊涂,可以假惊讶或者假生气,把场面敷衍过去,捞一把也未尝不可——一杯酒一百块哪,半老头子要她陪十杯。
但这一天她特别烦,突然揭了对方的假发,在他的秃头上摸了一把。
对方吓了一跳。
“你摸我的手,我就摸不得你的头?”她瞪大眼。
酒席上一片大笑,使半老头子脸上胀成了猪肝色。别说是占便宜,这个曝光秃头逃都来不及了,谁知道这个疯婆子还会怎样?下一步不会大庭广众之下揪着他的耳朵骑上他的头吧?
“喝酒喝酒,”她决不让对方逃走,打定主意进一步调戏和蹂躏,“你的一百块钱呢,拿出来呀,让我看看,是真钱还是假钱?”
大概是护主救驾有责,一个管家似的男人冒出来了,“芹姑娘,我原来一直以为你羞花闭月沉鱼落雁,以为你们文艺工作者五讲四美……”
“停,停。”她伸出一个指头,“更正一下:赚死人钱的,不是什么文艺工作者。”
“难怪,死人钱赚多了,一开腔就像是棺材里跳出来的,人不分上下,话不分好歹。”
“是啊,我一睁眼就看见死人,看你也是个半死不死。”
“你们看看,一张嘴是茅厕板子。”
“不光是茅厕板子,还是毒药罐子。”她突然扭扭腰,挤出一脸媚笑,“大哥,你那癌症心肌梗什么的,还没查出来啊?还有你那肝硬化,脑血栓,不赶快去查?再不查就晚啦。我就等不急啦。”她看见对方的脸色已经由红转白,“大哥,你再忙也要想想后事了。你不要骗齐老板的钱,不然的话,到时候齐老板哪会来哭你?你也不要到外面沾花惹草,不然的话,到时候你的老婆只会找你的存折,也不会来哭你。你尤其不要得罪下面那些打工仔,到时候你总要有人抬棺材吧?总要有人挖坟筑墓吧?”她兴冲冲地喝下一口,看见对方的脸色已经白中有青,寒光闪闪,硬邦邦的,是从冰箱里搬出来的冻肉模样,“到那一天,要是不请本大姐来假哭几声,你麻烦大啦……”
她字字割血,一口气把对方呛得结结巴巴。那堆冻肉瞪大眼,挣扎着站起来好像要动粗,但啪嗒一声,自己先摔了一跤,哎哟哎哟地没起来,发现手机也摔在地上,于是忙着找什么手机部件。
看到这样的狼狈和混乱,她大出一口粗气——什么东西?呸,撒娇都还没学会,就想同老娘来过招?
她得意洋洋走出店门,被冷风一吹,快意里不免又有几分委屈。她今天有点邪,一开口就是大粪腔,如果再跳起来一插腰,不是个母夜叉是什么?她其实并不愿意这样。在很长的时间里,她讨厌男人但也愿意逗着男人玩玩,但她知道自己已经与男人越来越远了。她的举手投足可能还有点形,还不那么难看,但目光肯定已经粗粝,脸色肯定已经僵硬,浑身都是灵堂里的香灰味、蜡油味以及炮仗味,挎包里还藏着经常要用的黑纱。有了这条黑纱,全身就断了电。没有电的假笑,怎么说也是操着玩具枪抢银行,是拿着假钞票做买卖,人家可能行,但她不行,心一虚,只能带着香灰味夺路而逃。
一个同事来找她,要她上车再赶一个场子。于是她和同事们嚼了些方便面,撑着雨伞上路,在车上颠簸了一阵,掐着时间赶到另一个灵堂,看到了另一张遗像:其实是很多以前的一个同事,前不久死于车祸。她心里一动,想起自己当年的剧团和舞台,想起死者曾经教她读谱,禁不住痛痛快快真哭了一场。她哭自己一个大美人如今却落到了代人哭丧的地步,哭男人既不同意离婚又不断欠下赌债,还哭自己的女儿个子矮小脾气古怪……哭过点了,还止不住泪流。主家没注意她照例乱了哭词,不知她如何这样伤心,大为感激,往她衣袋里多塞了一个红包。
红包就红包。红包是个好东西。她已经赚了很多红包,然后把红包一次次花出疯狂补偿的快感。面膜一次做两轮。冰淇淋一次吃两个。皮鞋一次就提回三双。衣服是眼都不眨地买回来然后眼都不眨地送出去然后再眼都不眨地去买。一百块一件的衬衣,太便宜了。六十块钱的丝巾,那不是白送吗?要命的是,也许是带黑框的遗像看多了,眼下看任何人,眼里就闹鬼,一走神,视野中就有阴阴的黑框子就位。她揉揉眼睛,发现一个个陌生的面容都像在黑框子里迎面而来,一个可能将要死于车祸的遗像卖给她冰淇淋,一个可能将要死于毒大米的遗像给她做面膜,一个可能将要死于中风的遗像正在推销皮鞋并且打出一个喷嚏。悼词上他们的享年将是二十岁?三十岁?五十二岁还是八十六岁?……她不是给遗像多付了钱,就是给遗像少付了钱。
“你是一个能够偷看未来的巫婆吧?”女儿有次突然冒出这一句,吓了她一跳,发现女儿正笑眯眯地翻着一本外国卡通书。
她眨眨眼,黑框子也出现在女儿的肩头。
她大叫一声,捂住了自己的眼睛。如果她有足够的勇敢和果断,这一刻很可能就抠下眼珠,丢到河里去了。
女儿不知一句话为何这样吓坏了她,把她摇了半天,才使她醒过来。女儿也不知道母亲为什么后来总是不拿正眼看她。
女儿学习成绩不好。母亲就是在为女儿寻找教辅材料时,无意间瞥见了电视屏幕上的交响乐《山鬼》,不,不是《山鬼》,是她完全知情的《天大地大》。如果一开始她还只是好奇,觉得曲调有些耳熟,一旦看到作者姓名,就完全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半睡半醒的笛声,又巫又仙的唢呐声,突然坍塌或突然迸发一样的大鼓大钹……她都能回忆得起来。一个山鬼掉了脑袋,以乳头为目,以肚脐为嘴,恶战天兵天将,这些歌词似曾相识。稍有不同的是,《山鬼》多了些新的曲目,多了一群白胡子中国老艺人,还多了一些大钟大磬的排场,更容易让外国男女们惊奇。那个姓魏的,被王室成员和音乐大师们握手,在闪闪钨灯下被那么多人围着献花和采访,看来是理所当然。
后来的事实证明,她的震惊和愤怒基本上没有意义。有谁会相信一个国际性的当红作曲家,一个拿了洋文凭的魏博士,会改头换面地抄袭一个乡下农民的作品?更进一步的问题是:一个乡下人能有什么?那个乡下人是谁?就是老寅自己,也把以前的事情忘得一干二净了,忘记了自己曾经是谁。她找过一些朋友,还有朋友的朋友,但拿不出抄袭的证据,也无法让人相信她的精神很正常,只能越说越乱,把天气时装音乐零食法律心脏病现代化等等胡扯一通,刚好把别人的注意力引向神经。特别是省城里的一个小毛头,差不多有多动症,眼睛
是四处乱蹦的壁球,一张嘴无法在任何话题上停留五分钟,说任何一个五分钟也会被手机电话打断七八次。他同上一个小毛头一样,也是个报纸娱乐版记者,一听到魏博士的名字都睁大眼,好像这个大名一经说出,就有魏博士魏博士魏博士魏博士呵呵呵的层层回声,就有空旷大厅里神圣感和历史感的嗡嗡共鸣,决不可随便冒犯——虽然他坦陈自己从未听过魏的音乐。他对农民根本更不感兴趣,充其量,只对一个女演员的愤怒感兴趣。你什么时候认识魏先生的?说说吧,你们以前是什么关系?他是否伤害过你?说说吧,不然的话你为什么对他耿耿于怀?……他肯定有了想象中的大标题:名人情缘,名人孽债,都是特大字号。
小毛头打开了录音机,录下了她的大笑。
“大姐,您不要太激动。过去的事情已经过去了,没听说过一句话吗?痛,并快乐着。过去的事情是痛,但也是快乐,是我们回忆的宝贵财富……”
“大姐,我们都要勇敢地面对过去,面对生命的轨迹和情感的年轮……”
“大姐,你没哪里不舒服吧?需不需要我叫个救护车?……”
她拍拍小毛头的肩膀,撇下对方扬长而去,临走时丢下一句:“小兄弟,你的鼻毛该剪剪了。”
她觉得别人没有错,自己确实就是个精神病。她烧完汤总是忘了关煤气,买小菜则买进了局长办公室,看到邻居杀鸡居然去打电话报警,最后,她在自己最熟悉的十字路口迷了路:街道突然变得无比陌生,前后左右都是楼房,前后左右都是汽车,前后左右都是人,她不知道自己该往哪里走,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一定要往这里走而不是那里走,为什么一定要走走走走而不能停下来就躺在这里……丈夫喊了几个人,把她一绳子捆起来送入医院。医生给她打针,总算让她安静下来渐渐入睡。医生事后偷偷地说,他打的不过是蒸馏水,对这种癔病,可以采用这种心理疗法。
柳胖子登门来看过她,劝她不必太为难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