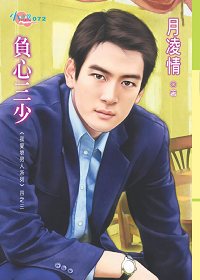三少女成长隐秘:木槿花开-第13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锦跃的口气里有着疲惫:“很美是吗?”
“很特别的感觉,在半空中欣赏。”
“人的心情很容易随着迁徙而改变,即使是一样的景色在异地便有着一种异样的感觉。”锦跃解释着。
我无声地认同。
她是一个习惯了奔波的人,在奔波里她有着自己的想法,无法轻易地被理解或者改变。
我回头看着她,脸色有点苍白。
“很不舒服吗?”
“不,只是有点担心安宁,我已经离开法国2个多月了。”
“是我耽误了时间。”
“回来的时候我就做好了心理准备的,清年的女儿会是你这样子的,即使有着挣扎揪痛,还是随着自己的心去选择。我一直相信你。”
我看着她温柔起来的表情,心间喜欢作恶的情绪作怪起来:“可是,我并没有原谅你。”
她的眼神坚定,却无声地看着我。一股子坚定的力量传达着,在我们之间。
法国的7月是炎热的夏天,明媚空灵的天空,给人分外清澈的感觉。
我深深地呼吸着异国的空气,矫情地说:“我的内脏里都是法国的异域风情了。”
锦跃在身后轻轻地笑着,带着满足。
法国街区的景色我都没有来得及观看,的士载着我们飞奔去HospitalSaint…Louis(巴黎最好的医院),锦跃的脸色开始变得更加地苍白,当一些近在咫尺的事实将要侵袭而来的时候,我看着她把自己的手指甲深陷进手掌,本来想对她说:“不是还有林聪在照顾她吗?”到了嘴边的词语却凝结了。
我并不知道待会该怎样去面对他。
医生和护士推着病床往急救室冲过去,锦跃瞬间崩溃的表情跟着过去,她焦急地看着病床上的小女孩大颗大颗的眼泪滴落下来。直到护士把她拦在手术房的外面,她瘫倒在地,无力地哭着。
这是我在法国这片土地落脚后半小时里发生的急速转变,安宁的病情恶化,在冰冷的手术台上接受任何器具的剖析清理。
我扶起锦跃:“别这样。我在这里。”
锦跃的眼泪更加汹涌,断断续续地对我说:“我害怕,我害怕。”
我的心酸涩起来,一个母亲的心这样的纠结,这样害怕失去自己的孩子。每个女子都有着最原始的母性光辉只等着时间的变迁把自己放置到母亲的位置上。
我抱着她:“别这样,没事的。”
我看着安宁消瘦的小脸上安静的睫毛停歇在脸颊上,一副宁馨可人的模样,只是在她的身上插着那些各色复杂的管子让人战栗。这时我才缓缓地将眼神收拢起来,和身边的两位白发苍苍的中国夫妇说话:“你们好。我是郁禾。”
老先生很涵养的样子说:“我们知道,锦跃把你带来了。我们是安宁的爷爷奶奶。”
奶奶温和地说:“叫我们爷爷奶奶就好。”
“嗯。爷爷奶奶。安宁的病情?”
“血癌在小孩子身上一直是多发的病症。一直找不到合适的骨髓,她就接受着化疗。”爷爷说完,疼惜地看着安宁。
锦跃从主治医生的办公室回来,面容疲倦。
爷爷很体谅地说:“现在安宁的状况已经稳定下来,你也不用太担心了,我们留在这里就好。你和郁禾一起回去休息吧。”
锦跃轻抚着安宁的脸:“如果她醒来,就马上通知我。”
奶奶走近了扶扶她柔软的肩:“你好好休息吧!我们在就好。”
锦跃在法国的家座落郊区,离市区有着很长的一段车程,我们坐着地铁,在陌生的人群里彼此靠近着。我能感受到她身上疲倦的气息。
最终忍不住问她:“林聪呢?为什么他不在安宁的身边?”言语里有着难以掩饰的斥责。
她看着我的眼神柔软起来,我看见了里面袅袅生腾的雾气。
进入隧道的黑暗,我听见她清冷的声音:“半年前,他已经离开了。也是血癌。”
像是一颗颗冰冷的石子滚动着,掉进了黑压压的枯井里,闷闷的一声一声的钝痛。
在静默黑暗的地铁里,我轻轻握起她冰冷的手,像握着小吉和习央那样轻轻地盈握在手,那是春天开始的时候小吉给予我的暗示和力量,在雪慢慢融化的冷气里一点点地让我恢复生气和力量。
在阳光重新倾泻下来,明媚了我们的面容,我看见了她眼睛里分外温热的泪水盈盈闪闪。
在异国他乡的地界里,我全身心地接受了锦跃,以一种介乎亲情与友情的内在情绪。
第二十三章 爱情在你离开后永生
锦跃的家很漂亮,虽然不是在普罗旺斯薰衣草田原的乡村里,但是法国郊区充沛的阳光里的小屋,路过了葡萄藤架子搭成的小径,满眼都是爷爷奶奶种栽得很好的花朵,在风中摇曳着明媚的花瓣。
“这是爷爷奶奶的房子,他们在大学的退休之后就来到这里生活。我和林聪一直居住在市区,他来到法国之后也有了自己的事业。”
夜晚我和锦跃一起躺在她的床上聊天,她告诉了我离开我们之后所有的故事。
离开了中国,她和林聪一齐来到法国。林聪利用之前多年的人脉开始了一间自己的画廊,也展览一部分自己和锦跃的摄影作品。林聪在读大学的时候就是美术系的,对这方面的熟络使得他的画廊经营得越来越好。而他的父母一直在法国这边做一些学术研究的工作。
锦跃说:“他一直是一个过分追求自我的人,所以在我19岁跟随他离开的年月里我们之间有着无穷的争吵。那时的他,相信着自己在摄影这个领域里是个天才。他的确有着很多人都没有的触觉很是凛冽和刺痛人神经的视觉敏锐。但是,自己认为是的总是在岁月变迁里被抹杀掉。他褪去了很多坚硬的外壳,重新好好生活。”
锦跃的眼睛盈满了月光的清冷:“小禾,我们永远不要把自己放置在一个过分高的位置,那样很孤独。最后伤害的只有自己。虽然他的事业一日一天地好起来,很多人都说他是一个很懂得经营的商人,但是我知道,这一直对于他而言是退却后的幸福。”
后来他们有了安宁,生活更加的美满幸福。
“我把安宁当成另一个你,加倍地疼惜。她的睫毛是最像你的。睡觉的时候很宁馨可人。”
我点头地微笑:“可是,你也还是看到了,我在事态变迁里激越地行为。”
“跟我一样,你看了我的日记是吗?我17岁的时候在水乡是有名的野女孩。”
我们一齐轻轻地笑,因为那一点性子里的激烈,因为那一点相似。
林聪查出血癌的时候已经是晚期。他并没有告诉锦跃,一直自己去医院做化疗延续着生命。后来在一次收拾房间的时候被锦跃找到了病历单。
“很难说清楚那时候的感觉。只是愣了很久很久,理清了思绪之后打电话去医院证实了实情。然后一路恍恍惚惚地跑到了画廊,看着他在擦拭着一幅幅我们最初的摄影作品,我从身后抱住他的腰脸贴着他的背。眼泪就倾泻下来。”我安静地听着她揪心疼痛的故事。
“我们都是很清醒的人,既然很多事情都无法去控制,就更加珍惜在一起的时光。那是我们最享受家庭的日子。搬到了他爸爸妈妈的家,一家五口的田园生活。”锦跃舒心地呼出一口气。
“他的病到了末期很难受,经常呕吐,什么都吃不下还常常把胆汁都呕出来。抵抗能力越来越差。我建议他去医院,但是他还是坚持要留在家里。那是安宁在学校的长径比赛,他坚持要去,我们坐在看台上,人潮很是热闹,我们看着安宁,她是一群外国小孩里最好看的小姑娘,穿着运动装很矫健的小孩子。但是却摔倒在了跑道上。血怎么也止不住。送到了医院,医生告诉我们安宁得的是血癌。林聪晕了过去,就再也没有醒过来。”
我惊诧着心疼着,这些伤痛就这样一并地倾倒在她的身上,眼泪流了下来。
“我曾经抱着安宁走到,医院的顶台,在边缘徘徊了很久很久。看着法国广袤清澈的天空。一瞬间就想一跃而下的时候。安宁轻轻地拽着我的衣服。你知道她对我说什么吗?”
“她说;妈妈,我想活下去。”我想象着安宁白兮兮的小嘴唇说出这样一句对生命的渴望的时候,眼泪更加无发生抵挡。那不仅仅是一种对安宁如此坚强的感动,更是对人本性中对生命渴望的感动。
我没有告诉她,而我相信她的心里有着一样的满足。她和林聪的爱情是最完满的,经历了青春的悸动和奔波,即使最后不能一起白头到老却在临死的那一刻彼此都深爱着对方。一起承受着命运的沉重打击。这是很多人在生活里最终无法抵达的地方,彼此心灵最最深的地方。
第二十四章 香榭丽街道里年轻的脚印
一个夜晚,锦跃告诉了我十年来她所有的幸福与遭遇,就像是那一个雪夜我第一次感受她的气息一样。翻卷那些日记的时候,我总是遗忘了她是我的亲生妈妈,甚至觉得她像是一个有着奇异经历的朋友,满身背负的疼痛和奇幻的旅程一并在我面前变成一片的流光溢彩。
骨髓的配型成功了,虽然那彻骨的疼痛让我渗出了一身的冷汗。但在玻璃窗外看着我可爱的小妹妹。激动的泪水盈满了眼眶,我多想跑过去抱着她对她说:“姐姐能救你,姐姐能让你好好的生活下去的。”
因为安宁的体质越来越衰弱,我很少穿着隔离服走进病房隔着玻璃和她默剧游戏。她总是在病房里笑得很欢欣。一朵几近透明的白色花朵慢慢地绽放着。我可亲的安宁。
在接受移植手术的前一个星期我接到了习央的电话:“小禾,融姐帮我找到了出工去法国的机会。帮一家服装公司排夏季的最新服装照。”
习央总是这样,用着她所有的办法要留在我的身边,有时候我总是想,她是不是一辈子都离不开我了呢?
在机场接到习央的时候,她把行李留给了助理:“我们去逛一天,我跟融姐请过假的了。”
助理一副唯唯诺诺的样子:“融姐交代下午就要试服装的。”
习央俏皮地说:“我就逃一下子,好不容易又来法国我要好好看看。”
“习央……”融姐的声音。
她无奈的叹气说:“去好好玩玩吧。精神养足了今晚就要拍照。”
习央灿烂的笑容:“谢谢了。”
她拉着我飞奔着。这还是我第一次好好地在法国的街道上奔跑。那样明快的心情是在医院里难得拥有的。
习央恣意的伸展着自己的身姿:“我回来了,法国。”
对我很明媚的笑容:“我有没有告诉过你我小时候是在法国长大的?”
我揽着她:“你的故事总是那么多,我不记得啊。”
“没良心的。我小时候是在法国长大的,法国的街道都有着我小时候的脚印。”
“呀。真矫情。是猪蹄印。”
“好啊!就让我这长长的猪脚踢踢你的猪屁股。”我们在街道上欢快地追到起来,善意的法国人看着我们微笑。
坐在街道里的露天咖啡座,习央很享受的表情:“还是法国的蓝山咖啡最正宗。”
“我还是喜欢小时候奶奶冲的茉莉花茶,清清淡淡的。”
“这就是区域不同文化不同。”
“真庆幸,名模没有说我是没有品位。”我打趣地说。
“对了,你妹妹怎么样了?”
“现在就等着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