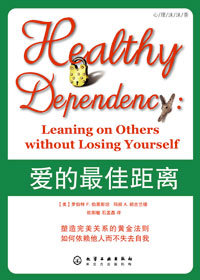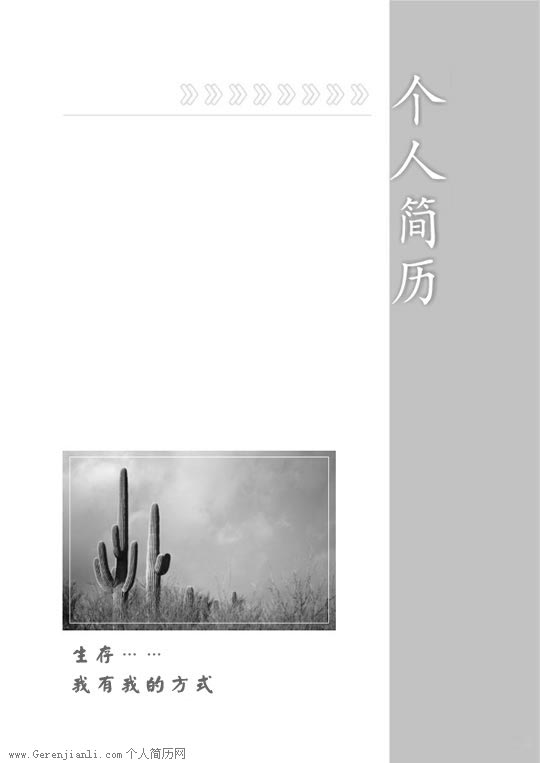秋天的最后一个处女-第7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情三分钟永恒。尤其多产细皮嫩肉。如云美女,一直雄居出口地位。偶尔有几个滞留本土,却也鹤立鸡群,不同凡响。”
“说得对,就是这样。你怎么知道的”俄罗斯没理会言外之意,乐哈哈的。“当然,你们老家也不错,百里杜鹃,驰名中外。去年花节,我们到阿丹家,彝族舞芦笙舞全跳。你们的那首《彝族舞曲》,美惨了。英子咬定是洋曲呢。”
冷冷回头,故乡像个闲坐的老年妇人。那场来得风光,去得慌乱的爱搅得她苦不堪言。除了月光惨淡,落叶翻飞,我再也记不得什么枯荣。不是生于斯长于斯的缘故,回头看她我都不姓李。俄罗斯不提起,我差不多已经把故乡遗忘了。
从红砖房出发,朝着太阳落山的方向走一百二十余里。如果是暮春三月,远远就会看见一座老城轻巧地伏在金灿灿的菜花上。蜜蜂的嗡嗡声催眠着除你之外的整座城镇。出来念书后,我第一次回故乡,却是在一个忙碌得让人讨不开眼睛的夏日,不论是茅草弯刘家老得褪了色的窗户,还是文昌宫女孩子绷得紧紧的腰身,都给我一种活生生的动感。听依云说,冬天的小城像一个玩累了的孩子,安安静静的,只有东一声西一声的狗叫。我家住在乡下,冬天学校放假,没在城里呆过。听依云说,她喜欢踩着薄雪上东山去。残碑边,断桥处,她都寻得着儿时的梦。她说,在这个城市只要你梦过,几世几年,你也会寻得着它。
我是在一个万木萧萧的秋夜离开故乡的,我坐在雷打坡上,数着城里的灯一盏灭了又灭一盏,南门河升起惨淡的雾,城虚幻如不存在的想象。连下山的路也看不清楚。我无端以为是爱情离我而去的缘故,久久地跪在这座年轻的山坡上,为永远失去的日子,也为这个城市的一砖一瓦默默地祷告。在我自私的心底,故乡是座不应该有秋天的城。我在秋天离开她,纯粹也是一种错误。
“不过你们家的确没湘西靓。河水呜呜咽咽,山坡笨头笨脑。”俄罗斯翻着嘴皮乱说乱有理,真讨人厌。
“可惜你要出嫁,谁也不会把湘西作嫁妆送你。”望望墙上几根粗野的线条,我低声叽咕,“也不配。”
二十四
有一种浮在梦边的感觉。泛泛的,连死亡的气息也没有。离家乡和月地都远远的。水波却老好地温存,夹杂着我无法控制的情绪。
上帝!我是怎样虚伪地感受着俄罗斯的存在。我复杂地想象起来。我的生命退缩到残缺的岁月。
逃学一般是在夏日的午后,太阳懒得不肯滑下山坡,老是站着不动,我们从没有玻璃的窗子翻出去。穿到学校外边的小河。河不深,搅的人多了,半节课时间,水浑得让人讨厌,在我们班上,我年龄偏小。这一先天不足导致我经常被人逮去压到水底。直到我应该说是懂事后,我仍不相信,除了空气,这世上还有另外一种会让人窒息的东西。
第一次高考结束,我带着少许的失恋和满腔落榜的苦楚,哀哀地坐在长江边发愁的那个傍晚,茫茫然的,还是不懂得什么是无望,什么叫难忘。
从那以后,每逢下水,我总喜欢躺在水上,不呼吸,不游动,让身体自个儿慢慢地下沉,下沉,直到水爬过我的唇我的眼睑。就像今夜一样。然而,如果说多年以前我的下沉是因为理想或恋爱的破灭,那么我今天的下沉却只是由于自己对自己的虚伪了。说起来,过去那些颠三倒四的日子,真值得怀念。毕竟啊,那是可以不考虑结果地生活的时光。我眼下虽然也是在四周的黑暗中下沉,可我的每根神经都在告诉我,我在离红砖房不到一千米的花溪河里泊着。我根本无法忘记俄罗斯在我的想象和愿望之间摇摆。
除了看俄罗斯画画,这半年几乎没有能让我集中精力的东西。包括她面红耳赤地和我争论“我们承受,我们拒绝”。我坐在圆凳上,很难统一我的观点。明明地举一大堆例子是为证明人所特有的拒绝性。结论却落到俄罗斯认定的承受上。争论下来,我自己感觉到我自己累和索然。一般情况下理智只承认看得见的东西。俄罗斯的左手总是霸道地叉在腰间,她常常把握笔的手伸得很远。光线不太好的时候,笔一丢她就不干了。墙上的画,我天天看都一个样。可是我已经习惯了她的笔尖离开墙壁的一刹那,习惯了她微微侧开身子让窗外的光充分照进来,习惯透过她的背影去看待她不易觉察的微笑和不安。我真希望时间永远死亡在红砖房。可是水漫过我的唇我的眼睑。我不得不另外换一个姿势。
夜,一如从前。
我看见俄罗斯坐在岸上。
承受和拒绝以外,我们还讨论什么呢?我努力地想,秋天的星光远远地游荡着。我真想悄悄地滑进水底去,就这样不了了之地结束我们的爱情。我清楚记得抱着浴巾走出红砖房时,我还有意无意地多看了一眼。虽然门关着,门后边还有门帘,可我想看见的我还是看得见。
二十五
推开七号寝室的门,波儿精彩地如下分派着。
“就这样定:结巴和那顺乌日图负责打饭拎开水。小江耐心好,菜由他洗。豆芽哥掌勺。我会精打细算,伙食费归我管。”
“哟,俄罗斯大姐,哪股风吹来的?屈尊寒舍,篷筚生辉。”那顺乌日图抢到门边来。字正腔圆,果然不愧为一室之长。
让俄罗斯坐上我当初睡的铁床,她接过“豆芽”递的茶吹了吹。“快计划你们的,省得哪次来你们寝室都空坐。”
“你是永远的客人,要不,请看现实的。”
这个那顺乌日图,俄罗斯一向赞不绝口,他时常侃蒙古包,献哈达,王洛滨给她听,上次俄罗斯生日他醉酒,狂言十六岁时他就喝过最烈的酒,骑过最快的马……
在舞厅弹了大半个学期贝斯,半个歌手也没追到手的结巴翻起身咧嘴直笑:“这可是波儿你自己说的,一百二十块,没吃的,没吃的找你!哈,休休想二两饭小半块霉豆腐就打发我,你说的,天天有肉吃。南哥作证,南哥作证。”
大家轰笑起来,三餐不继的日子结束在望,这可比年考万不万岁还要实在。
“派个弟兄拎两瓶”二锅头“炒几个菜。南哥他们难得来。”青皮寡脸的小江摸着枕套说,“还藏有三十二块钱。干脆结巴去打点,反正今天是你的值日。”
“这孬种种,前几天就哼没钱钱,跟着我吃吃……”
结巴一急,话更难讲清楚,盘腿坐在被子上乱骂。
“小家子气不断一天,结巴就不会好一天。”小江睁直眼。“上个月女朋友要我帮买许国璋英语,你没见我戒了半个多月的烟?”
结巴傻笑着,下床拖了鞋,接过钱,笑咪咪讨好俄罗斯:“我的亲姐姐,你喝”爱吃醋“还是‘椰风挡不住’?”
“‘椰风挡不住’”俄罗斯笑道,“快去快回,姐姐晚上还有课。”
结巴走后,波儿又吹开嗓子:“只是那顺乌日图,他这个北方佬,不准喝酒。他醉了,乱舞,敲锅砸瓶的,还了得?”
“喝他的,喝他的。骑士不喝酒还叫骑士?”小江干笑道。“损坏东西照赔。这是三大纪律八行注意所规定的。大家都是知识分子,丑话先行。”
“喝酒的人,每天多交一块钱。作为寝室的风险金,保卫科过问。好歹有孝敬。”豆芽在蚊帐里吼。
“也别订得这么死。人家喝酒是自个儿掏钱。”俄罗斯笑吟吟地插腔。
“吃烟喝酒各人随意。”波儿来劲了。
“我们最好错开食堂开饭时间,一家大小,安安心心吃。”
“和食堂同步开饭好——否则其他寝室来混饭吃不好说。”豆芽人无远虑却有近忧。
“同时开饭,乌鸦他们肯定来挟菜吃。结巴捞不到肉,要乱来的。”波儿忧心忡忡。
“他小归小,也不要一味由他。”我打着圆场。
“这是小事,凡是能吃的,都给锁好。肯定有人要偷嘴——我那两大罐燕窝,唉,两大罐。”
“锁是办法。就是怕馊。寝室里人多气杂。”
“再说耗子也不能等闲视之。”
“干脆养猫。”
“与其养猫不如养只老母鸡。我家就是靠母鸡发的。”波儿眉开眼笑。“每早上还可煮荷包蛋吃。妈,像住在家里。”
“凉拌三丝、油炸花生、西湖大排、芹菜牛肉、红星二锅头驾到!”门推开,结巴在店小二背后油口油嘴。
“第一杯,愿波儿持家有方,月月有余。”
“第二杯,愿小江媳妇不再对英语感兴趣。”
“别慌别慌,还有各人三朋四友来咋办?”
“每餐多交两块钱。”
“喝酒就喝酒,穷计较什么。”
“一次有三个或三个以上食客的,当事人不准跟着吃。”
“女朋友下访算不算?”
“算。咋不算?”
“别那么细气。传出去扫你们的脸。女朋友单枪匹马,加两块,带有陪食女,一分不加。”
“南哥言之有理,言之有理。死活我们还得在学校找则恋爱玩玩。”
端着酒杯,我为明天不饿轻轻地一饮而尽。
二十六
“南哥,我脸瘦,身子还是丰满的。英子说民间称这种现象叫强盗肉,真不?”
“真。”
“但我体型长不好。阿丹没讲的。”
“没仔细过。”
“我们系有个老师是色鬼。”
“中文系有三个。”
“他们追班上的女生吗?”
“没有。人到四十多岁。多半有色心无色胆。”
“吹牛。养情妇的多是四十迷感的家伙。”
“那是少数。”
“少数?香儿的小说怎么获奖的?她宣称小说的中心思想是二十一世纪的情妇比妻子多。”
“听她哗众取宠。全天下都吃了饭找不到事做也没这么泛滥。”
“你没听说意大利换妻成风。保不准还要修宪。”
“没听说。”
“搞不懂美国哪根神经毛病,前一阵子要取消最惠国待遇,现在又想阻挡我们加入WTO。”
“天知道美国谁在作主。网虫们说是克林顿的政治手段。”
“听说去年杜鹃花节有美国佬去你们家乡?”
“俄勒冈州的布匹商。又不是白宫。”
“我表舅也在俄勒冈州。”
“钱多不?”
“你以为年轻人个个都像杨致远?”
“腰缠十贯?那睡吧睡吧。明早是系主任的课。我也不想攀这门远亲。”
“他没收的书还没还给你?”
“可能他女人没看完。那女人会写诗呢。”
“《白鹿原》究竟如何,我记得它开篇鬼兮兮的。”
“如果写一半可以不朽。”
二十七
“有鬼意思。完全是些今天不知明天死活的小厂小矿。就连一个合资企业也没有。”在假日酒店门口碰见阿丹,她拿着十来张“求职推荐表”,准备去“梦工厂摄影机构”应聘公关小姐。
俄罗斯捏捏她的脸蛋依哩哇啦讲了几句日语,拉着我往师大走。我猜她们一定是讲英子的坏话。
人才交流中心设在一楼。此厅本是师大的舞厅。卡朋特软软绵绵的《昨日重现》,荡气回肠的萨克斯,应有尽有的女孩子——我没少光顾过。没防今天它摇身一变成为学子们展露才华之地,俄罗斯忘记安装博士伦,眼睛不大好使。我念了几家用人单位,都没有她导游的份。乱轰轰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