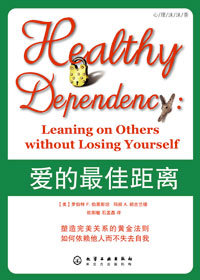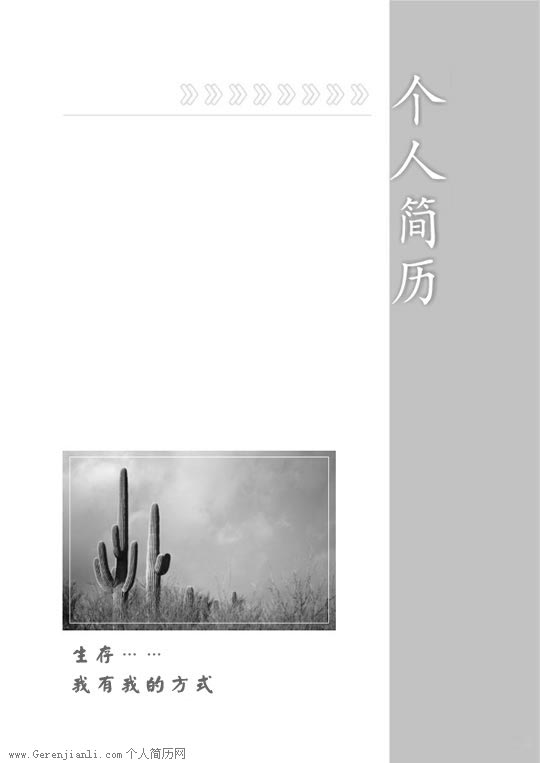秋天的最后一个处女-第24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天渐渐黑了。惨淡的灯照着一屋子的狼籍。生活了两年的红砖房,从头到脚渗出前所未有的荒凉。没有红枕头,没有花拖鞋,没有萨克斯的咏叹。墙壁上,‘上帝无言’四个字,绝望地站着,她根本没料到今天我会遗弃她。听任满肚坏水的松松和她相处,从她绝望的凝视,我也看出对她的漠然——甚而是欺骗,差不多将她吞噬。
“芳儿,还记得不,写‘上帝无言’那天,我醉洒,‘言’字多画了一横。”坐在只剩下稻草的床沿上,我打破知青般的夜。“一转眼,第二个秋天又要来了。”
“别尽说丧气话。回家放下背包我就来找你。”俄罗斯扮个鬼脸,“你坐好,我先去小卖部还钱。我可不愿像苏格拉底,到死都还欠着人家的钱。”
散堆在门边的行李一脸仓惶。我看见一只小耗子蹲在洞门口擦眼睛,在我暗淡的凝望里,它一扭身跑进去。对不起,小精灵,真的对不起,原谅我罢!回去告诉爸爸妈妈,俄罗斯天生胆小,我真有我的苦衷。
听到脚步声,我扭头看窗外。
几天前纸灰游弋的小院,除了夜,什么也没有。
九十八
没想到,走的时候,会是仓皇!
门虚掩着。松松送我们到路口他就转去了。
眼望着他推开门。眼望着他坐上木床,眼望着他东翻西翻。我放下背包。
“歇会儿,手疼。”我对我们撒谎。
院子里,有棵站着开花的树,每年从三月到七月。
俄罗斯放下皮箱,甩甩头发。在我面前,像夜一样。
院子里,真的有棵站着开花的树。从三月到七月。
“噫,你看!桥。”我喘着气。学校的铁桥跨过南方的天空。
“昨天叫去你不。”俄罗斯碰我。“快走,安子喊。”
“噫,你看,桥!”
“见了见了!”
俄罗斯对司机说到火车站。安子燃着烟。
我看见往事从桥上趴下来摸着院中那棵开花的树。
只一眼,我就累了。像自己抽空自己的蚕。
我真傻。真的。你想,一个铺着青石板的小院,一棵站着开花的树……
九十九
一群一浪的人影在我眼皮底荡来荡去。花裙子吗?为什么飘忽不定?长发吗?为什么拴有许多咒语?额上渗出汗水——见鬼!我的手自己发抖,一如前年,那片惨白惨白的月地。舞池里看不见现在,看不见未来。过去,化作一条美丽的花裙子,在我面前飘扬飘扬……
从西双版纳回来,俄罗斯一身花裙子坐在木棉树下笑咪咪地画红砖房。我因为在西双版纳办杂志的愿望破灭,老大不愉快,见俄罗斯花枝招展,很是不高兴。
“对于女人,年岁是写在心上的,花哩胡哨,你当你十六岁?”
“就喜欢,不服气?”她停笔,昂首挺胸,视死如归。
“看过通讯《女人为谁打扮》吗?”
那是篇小说,我知道。之所以睁眼瞎说,我有我用意。
“女人为女人打扮。”
后来听说阿丹和她一道去找人家换裙子,三个女人吵半天,没成。
舞曲完了。燕三回到我身边要烟抽。
“她至少也到了龙里,别干巴巴坐着。你搞得生离死别。”
点上烟,我一言不发,拿在手里把玩。好多人都为罗米欧哭过,但天底下只有一个朱丽叶。
又一曲开始。红的绿的灯接二连三熄灭。小提琴越过厚厚的人群落到我面前,蛇那般扭着身子。跟俄罗斯学拉的那把一模一样。
诺言、明天、叛离、开花的树……恍惚中,有人割开我的头骨。我从不相信注定的,可现在动摇了。一颗心差不多窜到了嗓门口。
我跑到隔壁休息室的长窗边。
眼皮下的延安东路,车如流水。黑颜色的尼桑车亮着红颜色的尾灯。我想,它定然会转过该死的红灯,掉头驶向东南方。车窗边那位穿花衣裳的乘客,定然会在湘西的街道被俄罗斯看见。那么,我的凝望,也定然会被她看见了。如此,她定然会一如从前那样摆弄着花裙子,对我嫣然一笑……
是的,我一直等着想告诉她:俄罗斯,花裙子漂亮。
全书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