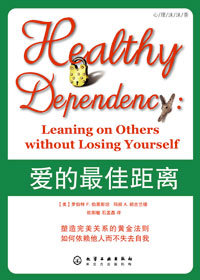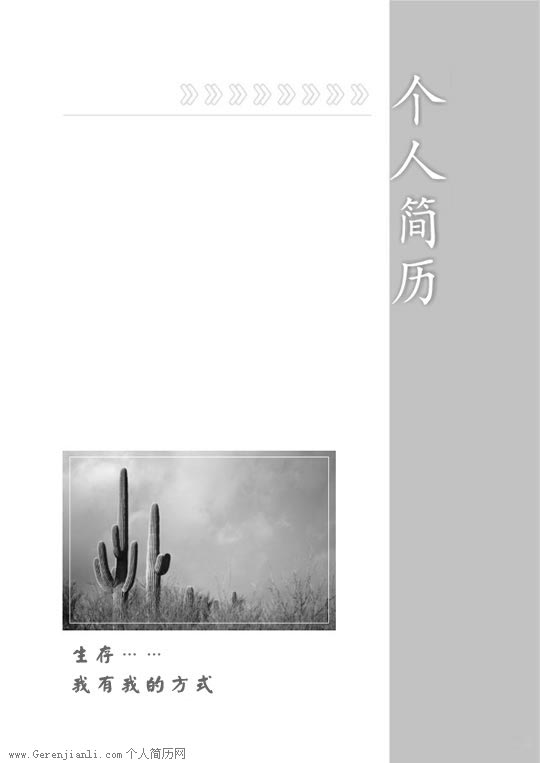秋天的最后一个处女-第21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青石板,太老的毛豆枝,半旧的钢琴,懂女人的那顺乌日图,娃娃脸的月亮,在我面前,都被玩弄了。不想到是最后一次聚会,不想到俄罗斯准备了两天,我一定转身就走。记忆中的中秋节是仁慈的,一点也没这般放任、下流。
八十五
俄罗斯没在家,红砖房里边半节黄瓜也找不到。我木纳纳坐在门槛前的石阶上,晃若那个死了第六个女人的白稼轩。在滚动着的旧空气中我想起数年后的一个晚上。
望南上气不接下气爬到新房门口时气嘘嘘乱想,要是再上一层楼,那就摸到对边的停美家去住好了。
俄罗斯还没有回来,望南渐渐看见,墙上的钟走在十二点半。他甩开衬衫,裸着上身,很深很深地放自己在沙发里。沙发是浅黄色的。属于那种坐上去让人想入非非的颜色。去年秋天结婚前朋友们说所有颜色中黄色是最具有包容性的。俄罗斯一听就乐意了,远巴巴跑到深圳订了比小孩子还要高的一大套。望南把腿伸展得舒舒服服地搭在茶几上,他自已为自已倒了一杯矿泉水。顺手摁开宽宽大大的电视。望南隐隐觉得自己也是从那一次近距离地了解俄罗斯的品味。过去在红砖房的日子认得真只算一种性友谊。知识告诉望南,避开淫荡不讲,黄色最多具有暗示性。朋友们之所以乱说,完全是王朔他们这也否决那也重估,要不纯粹就是《失乐园》正在中年人之间暗暗流传的缘故。
电视上刚刚报道完中国政府和美利坚之间在开始寻求新的对话,接着又宣称车臣第二大城市古吉尔梅斯今天下午两大油库被炸广大官兵花了近五个小时才扑灭。屏幕上火光冲天,男叫女哭。望南百无聊赖地关了电视,他掏出传呼机逐一逐二地查看信息。他不相信一整天没有人呼他。
这时候门铃响亮地叫起来。
俄罗斯回来了。
这段时间俄罗斯回家很晚。自从上个月她把古玩店转给波儿,她的生物钟就没正常过。望南曾经恶毒地设想过说不定俄罗斯过上了那种不三不四的生活。中产阶级女性对爱情的渴望与乞丐对面包的热爱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
玩罢。她总是这样回答望南的诘问,然后走进洗手间打开阿里斯顿热水器稀哩哗啦冲洗。望南坐在作为嫁妆的新房里总感觉自己也像嫁妆的一部份。
门钤一直在响,望南只好起身猫着腰去开门。
望南先生,你看真不好意思,这么晚了还来打搅你。门开了,不是俄罗斯。一个电线杆男人和清汤寡水的女孩子站在门前。是这样的,男人说,我们找过你好几次,但你们家一直没人在。是这样的,去年我们啤酒瓶伤你一事,现在公司已经作出赔偿方案,您看您……望南记起来了,去年他在海口混的几个老同学回来,大家一起去王记火锅店吃饭,席间啤酒瓶炸裂,他的一双脚被弄得血糊糊的,窝哩窝囊住了半个多月的院方才恢复。其间厂家来了几次,但都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而没有达成共识。一拖再拖。望南几乎上都把它忘记了。
送厂家两个代表到门厅时,望南嘴上是说等俄罗斯回来商量商量再答复,可他内心实际上已经接受了厂家开出的条件。做人嘛,做的就是一个见好就收。虽说瘦个子一会儿说‘您’一会儿又是‘你’的让望南很不舒服。
望南习惯性地坐在电脑旁把厂家的文件输进自己的文件夹。电脑是俄罗斯娘家陪嫁的。自从上个礼拜天望南去娘家告状无效后,望南每用一次,都有那种被人剥光却又要对着人笑的无奈。俄罗斯在家的时候他一般动都不去动。
电脑的屏幕一直闪闪烁烁,仿佛快要爆破一样。望南耐着心找出光驱重新安装一遍。他恨自己有那么一种生活在自己家里却有做贼的感觉。
深夜敲击键盘的声音清脆得像电影中爆炸前的定时炸弹,望南输到最一个字的时候,他紧张得抖抖颤颤的,血好像从屏幕里吱吱吱地流了出来。
结婚前望南可不是这样小的胆量。他对面住的是一个世界末日病患者。只要望南的门一开,他总要钻进来毁灭啦地球爆炸啦倾销。望南通常是拍着装修得花哩花哨的墙壁嘻嘻哈哈:这房子结实着呢!二十世纪的天空虽说漏洞百出,但是夜间的月亮该可爱的时候还是可爱。望南在思考着人类何去何从的大框架,他对这种“后颓废”热不起心来。
婚后不久,随着俄罗斯一天天的昼伏夜出,望南慢慢变得疑神疑鬼来了。先是过去那邻居演说的一幕幕在面前浮现,后来甚至连高温锅也不肯用。俄罗斯不在家,他差不多不敢呆在屋里。新房高高挂在八楼,横尸院落的惨况他想象过无数次。这会儿,望南偷偷看一眼墙壁上走得歪歪扭扭的闹钟,明明白白地感觉到,他马蹄形的烟灰缸就要四分五裂地炸开来。他腿压着的茶几,他血红色的书柜,书柜里那本指导夫妻生活的书,黑着脸的电视机,小姨子克隆来的大红袍金鱼,卫生间卧着的那只被批判得一声不吭的马桶,昨天才买的以安静出名的电子猫——一古脑儿都是要爆炸的嘴脸。望南紧紧地抱着手臂,嘴唇咬得死死的,浑身冷汗直冒。
这时候,茶几上的呼机剧烈地震动起来。
呼机上说,今晚不回家。
太阳绕过木棉树走了。一只麻雀翻落在表石板上,西望东张,举着它高度浓缩的脑袋端详我好几秒钟,啁啾一声,引来它的一群伙伴。它们一只比一只胆大,一只比一只不不要脸,有一对竟然当着我的面摇摇晃晃地做起爱来。我一动不动,大气也不敢出。
八十六
松松大作《论同居》获奖,组织上准备重温他拖了两个学期的入党问题。
在得月楼门口碰见松松,我转告他系主任的决定。
“不过以此作入党的台阶,有点伤风雅。”我客观地对这个字写得歪歪扭扭的江苏人发表意见。他不挂眼镜,难相信他也知书达理。听他们遒义老乡吹,高考前他一直是镇上的小流氓。若不是考试偷看到英语,下辈子也修不进大学。我看得起他是去年的一天下午,燕三带他来红砖房混饭吃。翻完俄罗斯为《我白天哭泣夜间欢笑》所作的插图,他用苍白的手指敲着畏畏缩缩的鼻子说三个月后他一定能找出弗洛伊德与《诗经》的联系。
“伤风雅?我看你是恋爱昏头了。”他夸张地耸起鼻子,并扭扭异常肥大的屁股。
“我是说,入党是严肃的事。同居这种社会现象怎么说都有点那个……”见他误会,我忙解释。我至今仍然是小团员一个,心目中,入党并不比考大学或忘掉初恋那么容易。
“要你这么说,妇产科医生更没资格入党,她们一辈子同阴道打交道。”
指不出其间质的差别,但我知道我错了。按恩格斯理论,生命只不过是蛋白质存在的形式。再说,人们离开阴道,有的拳养情人,有的寡欲,这同政治面貌不相关。
“不管怎样讲,你该请客。连俄罗斯都嫌你小气。”
“我可不愿离开学校时欠一屁股债。”
“倒也是。”我口是心非,“马妮呢,好久没见她面。”
“吹了。她现在和法律系的儿子。”话虽清淡,在我看来他萧条得像冬天的木棉。
我颠颠足球,悄悄幸灾乐祸。
“听俄罗斯说,湘西那边的人不好惹。”
“又没上床,什么好惹不好惹。”他又耸耸鼻子,露出尖刻的细米牙。“我不是学艺的,有没有沈从文黄永玉都无所谓。”
“那倒不一定。至少亵渎。你论文不是从她身上剥下来的有鬼。”
“任何一件成功的事的背后都免不了有这样那样的亵渎。”他拉拉领带,一副反强奸的嘴脸。“有朝一日,《秋天的最后一个处女》得以见天日,你会相信。不说人,连秋天也给你亵渎了。”
念及我对秋天的种种不满,我知道,错不在松松。一时间,只定定的望着他仿佛被强奸过的脸找不到话说。
这些年我一直认为秋天是属于农民的,也只有农民才关心秋天。当我在这个破破烂烂的季节,离开燕山,离开二中,离开那些雍肿的稻草堆,走进冷艳苍白的秋天,反倒落得像个被剥夺了耕地的农民,两手空空,衣不遮体。
“妈送来辣子鸡,我下午拎去红砖房,让俄罗斯准备小白菜算了——呀,同你一耽搁,又给院报的记者们撞上了。嘻!他们以为他们是约翰。钱塞勒。”
这功夫,图书馆那边跑来几个男女。最前边的女孩子,我敢说她没戴胸罩,一晃晃的,颇抢眼。
“好缠吗?”我熟悉这些记者们的德行,跟松松说的差不多,他们以为他们是学校的约翰。钱塞勒呢。
“应该没问题。”松松狡黠地眨眨眼,“我一句话就打发他们——你们能说下雨是天空和大地做爱,那么文章不过是稿纸被笔强奸的结晶。”
八十七
俄罗斯惊惊慌慌跑回来说,有人靠在第三棵菩提树抽烟。我不用想就断定是停美。
停美是秭归人。虽说和屈原沾亲带故,但她这一家族,前后左右都没有出产一个舞文弄墨的。母亲生下她不久就遁入空门,坐禅修身,走的路同三闾大夫完全相反。停美十二岁离开秭归。停美常抱怨,“可惜她来到世间晚了,否则该劝劝母亲。”她画过好几幅《屈子行吟图》,送给评委,连初赛都没通过,终究灰了心,干脆矢口否认自己是秭归人。《怀沙》那些优秀的诗篇对她来说也是陈如死水。
作为肖魂的女友,她是初恋,她是认真的。有次她陪我到镇上买豆腐脑,从王道到霸道,从包房到寺院,她滔滔不绝。我觉察出,她是那种敢于暴露肚脐眼而不敢坦露内心的女孩。
“肖魂忏悔,他太冲动了。是他的错。求你原谅。”在她对面的土坎上蹲了许久,等她抽完烟我这个当初的媒人缓缓开口。
“没必要。”她翻起牛仔衣领,蛇一样顺着菩提树滑下。“南哥,我五年级偷看到班主任的日记,上边有句话,圆珠笔写的,今天总算懂了——他说,‘初恋像豆芽,白生生的,放到菜板上了,还想长啊长。’”
“停美,别这么练达。作为男人,肖也有肖的想法,原谅他吧,这年头,恋爱是不容易的。”
“别为难我。算了吧,你知道,我很想一生一世。你不是常说,花儿谢了,还算花吗?算了吧,走呀,回去,俄罗斯在那边难得等。”
她走过来拉我。手冰凉凉的,仿佛在住事中浸了许久。淡淡的星光下,我望着这个读不懂《怀沙》的女孩,深深为肖魂感到可惜。千错万错还不是在你肖魂,众目睽睽之下,一点面子也不留……
“美儿,原谅他了吗?”俄罗斯远远地问。
“谁,初恋?我原谅了的。”停美快步走到路口挽着俄罗斯。
“希望工程又怎么了?全学校上百个党员也没像你这样卖命的。闹得谁都晓得你去酒店坐台。”
“我从小伶仃孤苦。你不知道钱对穷孩子的重要。”
“除了盖茨,钱对谁都重要,但最重要的是自己——哎,我问你,老板们坏吗?”
“也不尽像传说中的那样没有层次。第一个客人是惠通公司的。他要了两杯士天架,劝我回学校好生念书。有人Call他,给小费就走了,还挥挥手呀。”
“第二个呢,都说你午夜两点才摸回学校。”
小色鬼,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