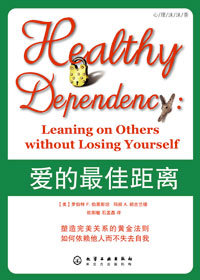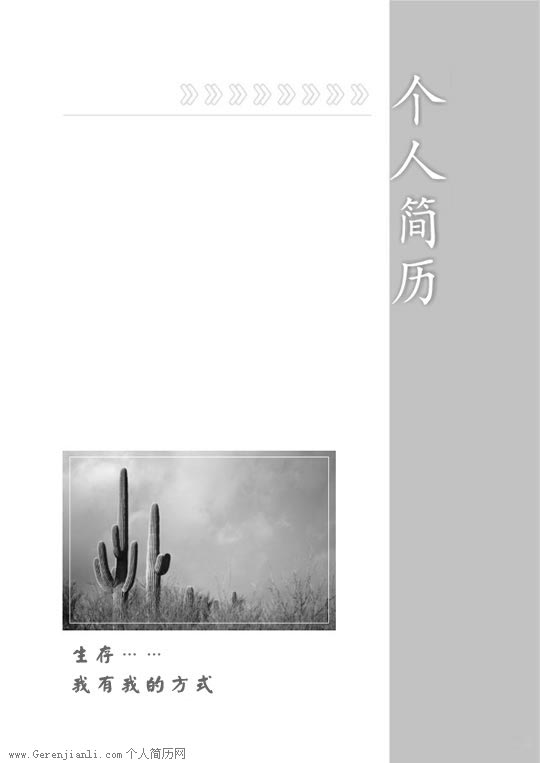秋天的最后一个处女-第20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我边剃胡子边对俄罗斯说我的决定。
谷风走的那天也是落雨,淅淅沥沥地淋得站台上孤零零的。好像要把所有生活过的痕迹和目的都冲得一干二净。俄罗斯抱着那本介绍发展主义的书,她破天荒地叨起安子丢在书桌上的烟,一副深思熟虑的才女样。我远远地回想起第一次到青岩的情景来。
已经是前年的事了。我正在埋头读着二年级的功课。由于请假的时间长次数多,我在教授们耳目中的名声开始扫地。班上组织去青岩采风,我醉薰薰地打电话给刚认识不久的谷风。他在青岩镇政府工作。一夜之间莫明其妙喜欢上诗歌。那天我实在讨厌班主任浮光掠影的玩法,只想找地方睡觉。
谷风带着穿红裙子的女朋友来车站寻我,一见面,握着我的手使劲地说若地的好话。若地是我在兰大的一个文友,诗写得苍凉中略显洒脱。有一天谷风送欧阳江河的书还我,我随口推荐了若地。等他听我说若地现在基本上不写诗只算命,这个华南理工大学毕业的优等生露出很是让我感动的茫然。诗歌受到圈外人士的关怀,怎么说都不容易。爱屋及乌,对他打扮得过于保守的女朋友我也客客气气。那时谷风因为姐姐在多伦多混得还比较华侨的缘故,谷风正在做着出国前的准备。他的写散文诗的女朋友据说连“别赋”都写好了,怀着一颗即将受伤的心单等他谷风远走高飞。那天也许是我被遗弃的心还没有复原,也许纯粹是酒精闯的祸。我口口声声说人的奴性是不懂得回避,尤其是看见悲剧而不懂得回避。我还隆重推出所有动物中人和老鼠是最善长于繁衍之乐。谷风的意思是我嘲弄了他的女人,嘲弄了他的爱情。第二天酒醒过来,不管我怎么样解释,他执意和我绝交。我再憨也明白这是红裙子枕边风的结果。女人要破坏什么,一夜的时间有多无少。
今年夏天,若地来红砖房听我说起这件事。他捏灭烟头,双眼无神地说,你能诱导他去读诗,女人唆使他厌恶你这当然不困难。
忧时子告诫过我,完美的生命在于承受得起他人的来来去去。我坐在矮矮的椅子上努力考虑过友谊和女人的问题。我发誓从今以后,再也不会到青岩去。世界宽阔得无边无际的,放弃一两个角落本来就是无关紧要的事。第二只熟透的苹果砸在牛顿的头上只是多余,说不定连原有的万有引力也会因他一时之怒而否定。况且自从我迁居红砖房后,过的大半是活生生的日子,在鲜艳的爱情面前,人世间值得一珍惜的东西少之又少。这是我的人生观之一。我听旁人说,谷风走的那天下雨,站台上只有“散文诗”和她的几个朋友。因为他是独子,移居多伦多的壮举,半点风声也不敢透露给他老母。他姐姐在电话中只敢声称,帮谷风找到一家助学基金会,在多伦多学业完后马上衣锦还乡。坦白地说,如果不是谷风给我写信,我已经忘却他了。
谷风在信中说他的母亲病得不轻。远在加国,回来一趟太不容易。
八十二
眉头一皱,额头上的蚊子果然给惊飞。我沉醉在我的游戏里时,俄罗斯狠狠戳我,老枪老调地发话。“就是不听,皱眉容易容易老。”她阻止的结果,我们家白天闲坐也燃着蚊香。青烟袅袅,颇有几分佛味。
俄罗斯和我都怕蚊子。夜间吸血的自不敢提,就是白天嘤嘤绕着枕边案头玩的,贴上身,也烦得要命。有天午睡醒来,见两只竟然停在尤沉到闺梦的俄罗斯鼻翼上缠缠绵绵地做爱,除了发现蚊子大多是两栖情人以外,我竟然惶惶然不知所措很久很久。
“红砖房有趣的事儿多着。只不过今天不为我们所觉察而已。”容忍不了俄罗斯对红砖房的淡漠。我的话说得像佛家那样浑朴。
“不见得。踏进社会,往后有好多时间让你回忆?说不定也像香儿她们一样,毕业就失恋。”
“谁说的?”我一骨碌翻身坐起。“命运在我看来像只羔羊,皮鞭都用不着拿。”
“你开玩笑。”
我木呆呆坐在床头,耶稣深凹的两眼直勾勾盯着我。
“你不跟我走?”
“跟你走?你说得轻巧。”俄罗斯吃吃地笑,“这些蚊子咋办?”
一直闷眉闷眼的俄罗斯这会子刁钻古怪起来,好像过去她一直设防着我。望着她,我突然有望着蚊子的感觉。
不时有蚊子冒着生命的危险穿过我的手掌,我只得韬光养晦,一心一意为俄罗斯赶蚊子。这时候,我才体会,英子写的“蚊子去了,没有再来的时候”并不是无中生有的话。
八十三
满是血丝的太阳趴在弯弯的白墙上挤弄着脸。干枯的眼眶缩减成一个点又慢慢扩张开。条椅上的晚报半吊着,脱臼的手臂那样晃哩晃当。红砖房那株火红的木棉。那株含着热泪拒绝我们到医院来的木棉,消散了。我野狗一样窜来窜去。
护士推门进来,她令安子灭掉烟,然后回头凶我:“都三个月了,你再考虑考虑,别以为孕是好怀的。”
“没办法。我连自家也难养活。”我哭丧着脸,还有大专文凭。学校不允许过份。
护士没言语。我看见墙上的两个白洞,狰狞不堪鄙视我。
永远忘不了这么一天,静悄悄的阁楼上,我眼睁睁望着我的儿子碰碰磕磕地滚下高高的六楼。他没呼叫,除了血痕,连叹息声也没有。但我看见他惨淡的微笑,唉,还有他惨淡的前额。好心的阿丹找人推算过,孩子是木棉开花的那几天怀的。她在电话中跟英子叽哩呱啦说——那几天她坐在木棉树下指导俄罗斯画《红砖房的午后》。
她听见俄罗斯有两颗心在跳。
一颗心年轻,一颗心苍老。
木棉开得饱满。
孩子就叫木棉。
这个秋天,木棉的母亲二十二岁,木棉的父亲二十三岁,木棉零岁。
我不止十次拍着零岁的木棉额头买弄,“噫吁戏,噫吁戏,长大做个当官的。”真的,就在前天晚上,我还在这样胡作非为地说“嘣嚓嚓,嘣嚓嚓,长大当个音乐家。”
俄罗斯没指责,我休闲地靠在她肚皮上,哼起流行在燕山的歌谣。
大河涨水沙浪沙,
鱼在河中摆尾巴。
哪天得鱼来醉酒,
哪天得妹来当家。
我把末尾一句拖得很长很长,直到俄罗斯伸手蒙住我的嘴惊叫:“你摸他在动。你摸。”
竖直耳朵听了半响,没啥动静,又东摸摸西敲敲,选西瓜一样认真。
“哆罗罗,哆罗罗,长大定是大富婆。”我没完没了,像个巫婆。俄罗斯爽朗地笑,满肚皮母亲的光辉。
她不喜欢女儿。说女孩子家,长到十八九岁,给野小子俘去,做母亲的,人前还要赔笑脸,咬着牙口口声声说婚姻自由婚姻自由。她做不来,也受不住。我呢,大约是看透了男人的缘故,倒千方百计想生一个女儿。脸蛋红朴朴的,蝴蝶一样飞来飞去。帮我松骨梳背,做好吃的给我吃——可是,就在刚才,我为什么要听安子的鬼话?我为什么要狼心狗肺地说,‘进去吧,别怕,我在你身边?’多点点固执,多点点责任感。这世上,就会多一种牵挂,红砖房就会多一抹色彩。
不过,经济来源呢?对了,大学文凭,社会上怎么说,读几年大学读得一个儿子?英子没错。三个月,怪就怪在避孕套是国产货。还不到六个月,六个月正好毕业,学业家庭双丰收。可能是女孩,男孩也不错。光天化日之下,做什么海盗,玩吉他。普拉蒂尼。这一生没到过维也纳。他一定得去。阿丹说我们可能分手。认得芳儿的第三天,飘毛毛雨,她和一帮女孩了在铁路上玩,安子断定嗓门脆生生的她不是处女。那个秋天,我二十二岁。恋爱的过程就是犯罪的过程。壁上空洞的眼眶直勾勾挂起来,楼房被拆走了。青春像被遗弃的稻草人,举着干枯的手,寡和地浮在我身上。
门开了。
吱的一声。
八十四
我目不转睛盯着燕子坡,吩咐阿丹:“月属阴,妇女先拜。”月亮出山了,笑盈盈的娃娃脸。
“月亮阿婆,好事多磨;长命百岁,与日同乐。”
阿丹们一溜儿跪在供桌前边凉席上,演员般背诵台词。待他们退下,男生又排成一排。
“快过来,安子!”我对安子拖沓很恼水。
“男子不拜月。”他怪兮兮抗议。
“随他。”波儿说,“也不让他作司仪。”
“一鞠躬,月亮姑娘学雷峰。”燕青人小嘴怪,乱玩幽默。除了停美,没人笑。
“二鞠躬,登月计划尽落空。”半晌没人吭气,波儿解释,“因为我们厌恶战争。”
“三鞠躬,但求月儿一生处女——”
“啧啧,还是那顺乌日图现实,懂女人。”停美假话真说,“没有肖魂,我嫁就嫁这样的人。”
古色古香的《快乐的农夫》演奏到结尾了,阿丹本人也优雅得像个仙子。我咽咽口水,思前想后,暗暗为俄罗斯只懂点画画皮毛悄悄难过。
“阿丹,你应该学声乐。”那顺乌日图由衷羡慕。他做作地行个江湖礼,反手把装满纸团的小碟子抬到供桌上,他宣布,谁得《忆月》谁打头。
摊开一看,我抓到的是《画月》,俄罗斯得《咏月》。
“谁的《忆月》,别闷着。”停美大声问。
“我我我,嚷什么嚷?”安子应声而出。月光下,他冷着脸,皮笑肉不笑,“我只会学鸡叫。”
“又不是周扒皮,谁稀罕鸡叫?”那顺乌日图第一个反对。
“一九九七年秋,那顺乌日图躲在比萨斜塔的阴影处向蛤蟆姑娘求爱。
他们约定今晚跳华尔兹,不料蛤蟆姑娘爱上波儿。为了爱情,那顺乌日图发誓终生不娶。他提出等波儿身体长胖就同他决斗。
浪笑声四起。盘腿坐在供桌下边的那顺乌日图的确有那么点蛤蟆样。
“可随心所欲,但不准阴损人格。”俄罗斯妇联主任般想得周到。“谁得《对月》。接着。”
“我乱编不来,给大家唱首民歌。”那顺乌日图爬起来猫头鹰那样清嗓子——
昨夜挨打挨得真,
精竹打断十二根。
精竹打断十二块,
没有埋怨哥一声。
那顺乌日图字正腔圆,赢得一片喝彩。
“阿丹为我们弹了曲子,《访月》就免了。《问月》是谁?”俄罗斯欧式眼睛一扫,假笑道:“哟,燕三,是你,该不会口占一绝吧。”
“你以为谁都像你望南那样会长亭呀我的青春短亭呀我的爱人!”燕三顶一句,丢人败姓地抬头大喊大叫,“月儿月儿我问你,嫦娥妹妹在哪里?”
“歇斯底里,这算什么?本执法念你初犯,轻饶你。待会儿拖钢琴回院部的钱,你一个人给。”燕三一直暗恋着的香儿大义灭亲,引来排山倒海的掌声和欢呼声。
“算了算了,干脆先吃月饼。”阿丹冒充和事佬,“在这个恼人的二十一世纪,看来要肚子饱了才有高尚的闲心。”
我本来想好了一首《咏月》的七言,现在被他们乱七八糟的一搅。诗,此情此地景,显得不类不伦。再听阿丹这么一说,越发觉得酸不溜秋。抓个广味月饼,一屁股坐在青石板上狠狠大嚼。
青石板,太老的毛豆枝,半旧的钢琴,懂女人的那顺乌日图,娃娃脸的月亮,在我面前,都被玩弄了。不想到是最后一次聚会,不想到俄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