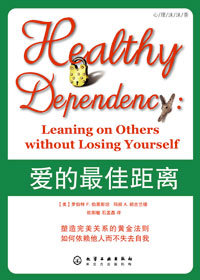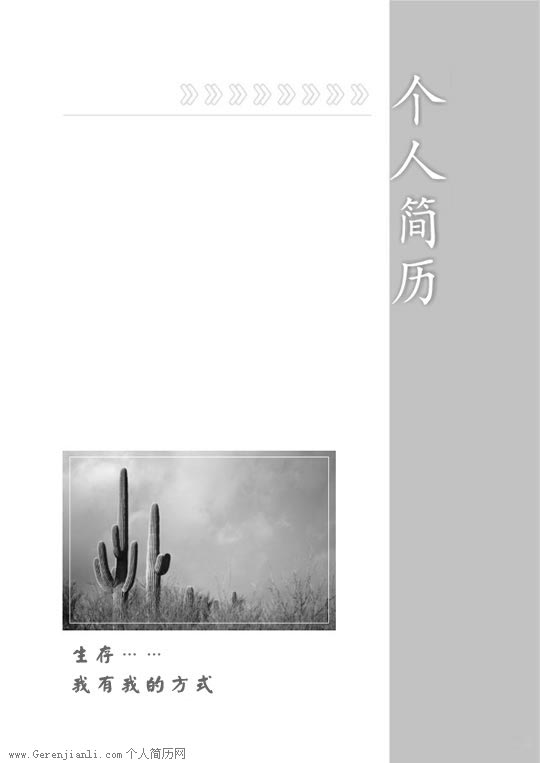秋天的最后一个处女-第12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
三姑娘听到端公依依呜呜的在堂屋里开始念神念鬼了,她说得小声小气。“怎么回事?兰老五的大爷爷解放前是刘财主家长工。有一天刘财主守屋的狗莫明其妙暴死。财主扭住姓兰的不放。也是兰家老人软,硬是给死狗披麻带孝大锣大鼓操办三天才脱手。据说当年还挂了挽联,叫什么‘黑狗老大人,孝男兰忠诚’。十里八里都传。”
“老一辈干的憨事,和你们相什么关了?”我以为是十大冤家九大愁呢。要说辱门庭,你大哥坐牢才是辱门庭。你甭管,我帮你劝解几句。实在不行去法庭告他。我请法律系的朋友们帮你当律师。又不是旧社会。我怕是不要王法了。
三姑娘不置可否的坐在木床上。我三口两口吃完鸡蛋正准备出门伸张正义,罗伯阴着脸站到红砖房门口叫我。
“小李,论理说呢家丑不可外扬,我罗家也算知书达理的人家。论理说呢你是外人,但是大家住在一个屋檐下,我也不把你当外人看。三姑娘跑出去我认了。她现在踏进我罗家的门就得听我罗家的规矩。我请先生来推算,说是家里要祭三天的脚。这三天不管兰家白家的人都不准进我罗家的门。你给你那群三朋四友打好招呼。你跟三姑娘说,三天后要坐要走由她。只是若要正正规规亲是亲戚是戚呢,叫她带个信给兰老五家,把礼节给我补清楚。砍了树子,乌鸦就不叫了。”
吃鸡蛋时我世纪末、爱情自由婚姻自由的想了一大堆,在这个五十年代的老生产队长面前,我只是憨痴痴站着。待他说完,我反而憨憨想:罗伯要在寨邻寨中做人。三姑娘这样走得名不正言不顺,叫他老脸往哪儿搁?再说,养个姑娘大也不容易。
“小李,按理说呢嫁出去的姑娘泼出去的米汤。我已经六七十岁了,还有几年活头我自家清楚。我会自家解释自家。你跟三姑娘说,若是要亲是亲戚是戚的走呢,我好在院墙边挖个侧门。她这样跑出去的,正门三七二十一天是跨不得。”
我唯唯喏喏,满口应承。婚姻自由归自由,三姑娘也做得过火,虽说是你自己过日子,但终生大事,确实应该从长计议。你一见到兰哥哥,翻墙跳院,一心想生米做成熟饭。要是有个三长两短,还不是哭爹喊妈。封建就封建一点吧。兰老五爱你,跟他兰家商量,大家都将就着点。
罗妈一声不吭。她像天底下软弱的母亲一样只有干坐在木椅上抹眼泪的份。在三姑娘从小长大的红砖房里,白吃了两个鸡蛋的我站也不是坐也不是。
四十七
菜花黄了,杨柳青了。春天,又有许多新朋友走进红砖房。他们带来广味香肠,尼采的情人莎乐美支持精神分析运动,中国需要进口女人等等好吃好听的。我乐支支,一有客人来颠着屁股忙这忙那。
俄罗斯对他们却淡淡然,礼貌得像只机器猫。自从松松半明半暗穿走华伦天奴西裤,她买的几张磁盘不翼而飞,对于光顾红砖房的新朋老友,通通小肚鸡肠起来。我呢,刚被英子停美她们从大男子主义的布袋里拎出,又披上所谓宁愿得罪十个女人也不肯失去一个朋友的袈裟。这颇伤俄罗斯的心。
从燕山赶回红砖房,见门背后立着碗口粗的木棒,奇怪之余,才恍然这就是俄罗斯自卫的武器。禁不往哑然失笑。这世道,有了黑夜,法律永远不会淘汰。马克思犯了个天大的错误。
先头一进院子罗妈就跟我唠叨,前天夜半三更,有几个人吃得醉醉的来找我,俄罗斯给喊起让铺。她做我的女友,好多时候,为照顾我的脸面,只得忍作大度,委屈以求全。有时俄罗斯好生生做着她的功课,突然光临三五个男女,少不得搁笔让座,泡茶备饭。夜深人散,扫地洗碗,已算份内小事。若有客醉,少不得心乱乱服侍左右,待他们安然入睡,才关门闭户,挽着哈欠连天的我上山另寻床第。“下次不理他们了。”事后沉不住气,我心烦意乱发牢骚时,俄罗斯往往中庸兮兮。
“何必呢?谁教我们家没客厅?再说,快都快毕业了。”
至而今,究竟有好多朋友吃过我炒的菜,究竟好多朋友睡过红砖房我已记不清。意识中,还找不出没对红砖房浮想联翩的朋友。
俄罗斯昨天的日记结尾处说:“拿我们的青春跟这些朋友周旋,一事无成的恐怕只会是我们自己。”
我深有同感却毫无办法。
结庐人境,难阿!
四十八
功课外的书,俄罗斯一般不大理会。像炒得热火朝天的《学习的革命》,她也不知道。
对此,我很是着急。
全社会都在反对林语堂,女人最好的出路是写诗而不是出嫁。况且又有专家暗示,除了母鸡,女人的思维老化得最快。我于是想方设法借来《恶之花》、《伊豆的舞女》大段大段读给她听。遗憾的是,她对此毫无兴趣。苦心孤诣的结果,她报以一脸茫然。我不安极了,暗自惊心,选来选去,难道抱回的真是个花瓶?
午饭时,见她把《名作欣赏》垫盘子,我再也按捺不住,厉声喝问还懂不懂斯文。她低眉低眼,一声不吭,半点有辱圣贤的过错样也没有。我突然对社会上背叛老婆拥抱情人的哥们理解极了。铁打的爱情流水的女人。他们说得对。和一个丧失灵性的女人生活纯粹是浪费。这时倘若门外有女行吟,我可能也会做出同样高尚的事。
“南哥,吃菜。别气坏身子。我听说作家锇死的不少。”俄罗斯挟块鸡蛋给我。轻声轻气像小妾。
“拿贾岛的诗垫盘子,亏你还算大学生,晓得不,‘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震憾了一代又一代的诗人。你试想想,一个”敲“字,几多空灵,听,那脆脆的回声。硬的不行,我使软点化她,好在我浸淫过古今中外数十卷名著,对情绪,收放自如。
“你昨天才说曹雪芹养活了好几万人,贡献比一个集团公司还大,贾岛又怎么了?算民政局?”
我于是绘声绘色告诉她那段半旧的佳话。
“这么说,贾岛又是诗人?”
“天,岂止是诗人,是大诗人呢。”我又好气又好笑。
“吹,会有这么多大诗人。韩愈呢。你说他碰到韩愈坐轿子。”
“韩俞是唐床八大家这首,相当于文坛霸主。你倘若认真读过初中就一定会记得他的文章。”
“屁,韩俞算个老学究,贾岛是个假斯文。”俄罗斯粗野地打断我,“你想嘛你想,这明摆着的,和尚胡乱喝了半碗清粥。眼见缸里米没有几粒了,心里烦闷之极。前天在陆家庄,约定一个女香客来上香,天已经暗到了这个地步——看来红尘人大多言而无信。成天吃素,米饭吃得多是事实,若不是叫保定来的叫化子白啦啦吃去半个多月的口粮,也不至于到这地步——和尚掩了门,苦着脸往河后边的馒头庵走。老尼姑是山背后陆家庄人,时常有三亲六戚送米送菜,何况女生饭量总要比男生小得多。向她讨几斤米,大不了下个月化缘回来还她。和尚赶到馒头庵门口,只见得夜静山空,月光如水,乌鸦心事重重地站在池子边的苦楝子树上,馒头庵关门闭户,和尚不敲门,你叫他推门?淫僧差不多。当然,也许是和尚读了两篇《南华经》,眼痛腰酸,自个儿到房子外边瞎走几圈。月明星稀,乌鸦南飞,蓦然回首,一别红尘十又九年,身没修成性没养定。落得个两鬓斑白,四大皆空。想要寻个一官半职,来个晚年娶妻晚年得子,又怕当今世上高手辈出,弄不好这惨淡的经营也保不住。越想越无地自容,只好推门回家长睡——他要是敲门,九成是个疯僧。那贾岛只注重文字而不考虑生活,看来也是浪得虚名。晚上做它一次和尚不就得了,偏偏大白天去街上比比划划,姓韩的偏偏下轿沉吟。后人更可恶,也一窝蜂跟着推啊敲啊。好在二十一世纪迫在眉睫,文人们都忙着打官司去了,否则,再挤到街上去附庸风雅,不出车祸才怪。我看南哥也是,好的不教,尽拿这些烂骨头哄人。
明知是俄罗斯强词夺理,我还是被捉弄得昏头昏脑,一时间竟无话反驳。
四十九
或许是我小时候时候贪睡的习惯至今还没改过来,也许是我看惯母亲晚睡早起,对俄罗斯的赖铺,我实在意见大得很。
第二天若是星期天,或许是几节无关紧要的课,俄罗斯一般不肯轻易起床。她回敬我‘能躺着就不要坐着’的话,见我不高兴,她又说她喜欢醒来翻翻书又睡的惬意——事实告诉我,她是在翻来翻去做梦。
“我们数世界之最,谁输谁先起床。”
不得不承认,红砖房是最前卫的,连民主也给普及到床上。
俄罗斯满口答应,数得心惊肉跳,却是十玩九输,到头来不是耍赖说不算,就是扭着我的耳朵一道起床。老实说,对这两个结局,我都是心不甘情不愿的。虽说重温旧社会士大夫举案齐眉的生活也不是不好,可是总不自觉地泛起那种下水推舟的滋味。因而只要有一丝希望,我都坚持到底。作为男人,能静静躺在床上看你的所爱梳头洗脸,烧水弄饭,应该属于比较红尘的。
“好好好,不算不算。我们辩一个论题,要不,猜谜语,讲故事逗人笑也行。”我经常宽容她。划出道儿,几乎都是我赢,记得实例有二:用诡辩胜她‘女人是人’的观点,靠机智中她‘十八女子倚门望’打一县名的谜语,然而,她每次率先起床,并不是因为败给我,要吗时间的确不早,要吗有人乒乒乓乓敲门,她哼哼唧唧穿衣拖鞋时,我的睡意也全无了。四平八稳躺在床上,无端觉得,让女人起床并不比让女人上床容易。
五十
俄罗斯摔筷子的声音很清脆。再准确点,就是迈克尔。杰克逊《Remember the time 》的过门。
看完《罗马假日》,已经是晚上十点半。天似乎要落雨,我们抄小巷到郊区车站坐车回红砖房。在车上,一时神经,谈到旧日情爱,俄罗斯抢白我:“想她了?去看看,怀旧是男人成熟的体现。”我没答腔,任由她发挥。“只要走过,自然寻得到痕迹。”
回到孤零零的红砖房,内心忖度:顾城失去的会在我这儿悄悄出现,怕没这样好事吧。其间必有诈。她摸钥匙开门时,我一针见血指出:“若今天的理解是为了换回明天我的理解,那先谢了。
小时候有本书花言巧语告诉我,除了母亲,这个世上,再也没有第二个女人会无缘无故宽容你。二十年来我一直牢记心中,从没见过例外。没想到这句话惹恼了她,甩我一人黑黑的床上。她自个儿去借罗妈的灶台炒饭吃。
夜是女人的。非不怪那些伟大的作品惊人的爱情都要夜间进行。玻璃窗透着一块灰色外,红砖房里什么也看不见。第一次靠夜靠得这么近,我差不多听见老木床咯吱咯吱解体。
俄罗斯炒饭回来,拉开灯,魔鬼身材在我面前晃来荡去。见没有我的份,我默默地撑起身解鞋带。‘天空没有翅膀的痕迹,而我已经飞过’,印度老头,你去骗小学生好了。
“男人为什么喜新而又不厌旧?”俄罗斯没觉察我的不快。吃了半碗饭,她才问,还扭过头望我,认真兮兮的。
“当新欢独食时,他好和旧爱睡觉。”
脆生生是筷子落地的声音。我慌忙侧身、闭眼、蒙脸。英子真的了不得,她曾经断言:当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