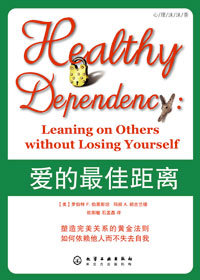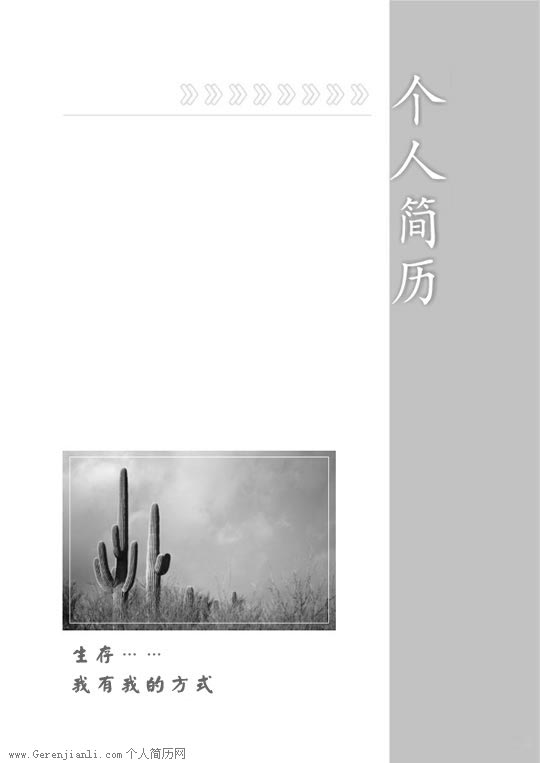秋天的最后一个处女-第11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像雨后春笋般出现一批成就卓越的艺术家:雷奥那多。达。芬奇、拉斐尔、米开朗基罗、乔乔纳、铁相——这个范围界限分明,往后退一步,艺术尚未成熟;向前进一步,艺术已经败坏——’”
“不听不听。绘画的作用在于对现实的肯定。你打击我?”俄罗斯白头宫女般感喟。“铁相,我的老师最佩服。有个叫,叫提香的,对,提香。我临摹过《忏悔的玛格达林》,参加县书画展,老师二话不说给压了。后来他书面告诉我,提香是歌颂性爱的,我气啊——不说了。我要听周邦彦的词。”
“夜半三更,哪去找周邦彦的词?”我本想夸夸她画了三分之一的圣母,见她颦眉,只好懒得说。
“那韦庄的也将就。‘昨夜夜半,枕上分明——分明什么’,”俄罗斯像一尊神。
“‘昨夜夜半,枕上分明梦见。’昨夜夜半,昨夜夜半——”我默念再三,始终记不起这首哀艳的《女冠子》。
“这样吧,我给你背诵《凤凰台上忆吹萧》。”我小心谨慎地讨好。
“嗯,名儿倒顺心。试试看”。俄罗斯没为难我。
“寸寸微云,丝丝残照。望望山山水水,人去去,隐隐迢迢。从今后,酸酸楚楚——”
“如此哀声叹气之作,难登大雅之堂?我要听《中国民间风情》。”
恭维双卿这首词的话还来不及说,俄罗斯一棒子打死。
“夜深了——”
“大胆!有你讨价还价的地方吗?”
“奴才错了。傩戏,源于……”
这叫情调吗?我苦笑。可是,为什么不挑灯夜读《瓦尔登湖》,要自讨苦吃地演着连篇废话?青春是我自己的,用它做什么,却不见得是我说了算。难道说我真有被奴役的天性?这样寻思,口中颠三倒四念着。我差不多听到鸡叫了。明天,一张纸那么厚的明天站在窗前。我从没对明天这样渴望过。
怪就怪在上海来的朋友。在红砖房吃完豆腐火锅,端着我泡的英德红茶,他热烈表扬我。宁婷则不以为。她说我结婚前肯定会处处体贴,洗小白菜拣折儿根,以后妻子轮班,一轮就是一辈子。为了表现我对女性的尊重和对自由的热爱,也想温习一下旧式夫妻所过的日子,我民主了又民主,宽容了又宽容——丧心病狂让俄罗斯过过老爷瘾,才一天,我后悔不迭。
四十四
从小酒店到红砖房,中间是一个荒废的院子。每天傍晚,总有几个年轻的学生在那儿谈天说地。没有买到蜡烛,我两手空空穿过院子时,看见有人相拥着在咝咝咝响的风中哭泣。心里很不是滋味。无端觉得,没有电,文明多少显得有些古怪。
俄罗斯去艺专还没回来,红砖房死水般无声无息。我坐在写字桌边,一闪一闪玩打火机。在这闪烁的光亮里,我又一次看见故乡,那座风咝咝响的城,那座我曾经愿意拥着我的初恋,悄悄度过一生的城。
第一封信
南哥:
生气了?整天瞎忙,日子就这么一天又一天滑过去了。也没给你写信,对不起。
不过,要是你知道我是怎么过的。你也许会可怜或笑话我。想告诉你,却又说不出个所以然,干脆你自个儿想吧。我只想说明,我比任何时候都规矩——至少南哥所嘱咐的,我都百分之百地做到了。那倒不是因为你要求(关心),而是我根本不愿在别人的面前放纵自己。相对来说,我更喜欢一个人,喜欢一个看着什么地方一动不动的发呆。也很少有所谓的空虚。要是我真想等什么人的话,我并不怀疑我可等上一百年。
南哥,我不想考虑你那些言外之意,不过我想说明,几千年前我就长大了。请你以后别再胡说“你还小还小”这类浑话。南哥自认曾经沧海,但有时未免夜郎自大。不知南哥是否想到,你所看透的人和事,为什么就不可能是同一类中的许多人和事?
当然,南哥大概不适应我的方式,那也得请你不要再用风雅女士的框框来套我。否则,你会觉得我一天比一天庸俗,是地地道道的小女人了。
祝好梦
Z
四月三日
生命是一个遗弃过程,爱情是其间的一座桥,涨水季节,桥没留神就给淹了。
第二封信
南哥:
就算你猜对吧,我不考试了。
南,我实在错不开时间,所以想九月份再参加自考。但愿你别太生气和过份哀叹白费心机——我可以想象你是怎样数落我。你怎么说都是对的,只要不影响你的功课。
准考证我取回来了,看着它总觉得对不住你。
我每天都是七点半起床——其实常常是六点半就醒了。以后的时间便用来想你。本来应该晚上想您,早上用来看书的,可是晚上总来不及思念就溜进了梦里。时间一长,便成了习惯。
南哥说的确实是道理,只是我觉悟不高一直难以贯彻。本来也想找几句道理来——转念一想,即使说了,也不过是我的道理,南哥是万万不会设身处地的。据我和南哥的历史告诉我,南哥的道理成熟的那天起,别人都是幼稚的了。
下班了,兰姐催走。
五月五夜
是什么时候,爱情从我身边走过,又是什么时候,爱情曾脉脉地注视我?我无可奈何地看到,青春是场交易,与其赌承诺,不如赌拥有。
最后一封信
南哥:
望着你消失在雨中,心一下子空荡荡的。无聊地在屋里窜了两圈,毫无理由地生起闷气来。
不知你坐的车是否开动,我已经开始给你写这封信了。
那晚独自走了长长的路,想了很多吧。
不管你的结论是什么,也不管是否于事有补,我还是要为我的胡言乱语向你道歉:对不起,真的对不起。
其实,我何尝不知道情至深处最脆弱,也知道那该死的情不自禁的冷嘲热讽和为了刺激你而开的玩笑会导致我们感情的危机。可是怎么向你解释呢?我只想说,只因为我太爱你,才千方百计让你感受一下你拖泥带水的爱给我捎来的苦痛。
说到拖泥带水,你是不会承认的。
感情上,你是个只注重过程的人。然而你却惯于以结果来为你的行为辩解。然而两个人的事情。并不一定要做出什么才算是事实。对女人爱用一种挑逗性语言。你以为这没什么,可别人会怎么想?我姐曾对我说过这样一句话:“小李子这种男人。绝不会放过任何一个他以为可到手的女人。”
南,我不明白,为什么这么久的日子了,你还有那么多藕断丝连。难道我对你的爱还不够?导致我们偶尔出现口角你就去找认为更成熟(更完美的)的?我并不是吃你的醋,我只感到它伤了我!
你抱怨我不相信你,可这些年,你细想想,你有什么让我相信的?你明知我是对什么事都过于认真的女孩,为什么还要常常向我撒谎、欺骗我?
南,我从没这样强烈的感觉到爱你,离不开你。知道吗?你让我害怕——我怕有一天会失去你。
求你看在我脆弱的感情上,体谅一下我。
你的Z
五月十二夜两点
掩上门,我走到荒芜的院子。那里已经没有人。连风也不再咝咝作响。只是夜不如先前黑了。稍微留神,看得见白杨树瘦高高的影子空空荡荡地挂在院墙外。我无端的觉得,自已站在了更加漆黑的夜里。
四十五
安子对我说过女人偶尔生生气比较有好处,而且也比平常好看得多。缘浅命薄,红砖房过去的上百个日日夜夜,我一次也没见过。闲暇无聊,便逐一找些堂正理由(比如说俄罗斯情商高,爱情使人心胸宽广)来解释。仿佛还真想不通,天底下为什么会有那么多恋人愁眉苦脸过日子。
自修完《北山移文》回到红砖房,门窗大开,绿的窗帘飘来荡去。收音机唱着印度尼西亚民歌《梭罗河》。俄罗斯依在桌上边哼哼唱唱地配着鸡尾酒,暴露出只有作为女人——而且是介于少女和少妇这间的女人才具备的很体面的曲线美。我轻轻倚在门坎边,沉醉在这片不为我创造却为我拥有的阿尔弥特花园。
俄罗斯穿着新款的白色长毛衣,右手的袖子松松卷起,像花溪公园那尊摘花女雕塑,又像秋天傍晚吹过麦田的风。独步学校的希腊鼻上闪烁着甜蜜的光泽,它们半隐半现,小猫一样顽皮。
轻轻绕到她背后,揽住她的腰,我吹着热气说:“小美人,知道你在家,打死我也不会憨痴痴在图书馆呆几个小时。”
她回头粲然一笑:“你吓死人了。”所有的柔情,完全堆在若有若无的酒窝,满满的,似那口传说中永不涸干也永不外溢的井。
卖牛奶的小贩在马路上高声大气吆喝,不时偷眼我家窗口,若没我这个方头方脑的男人,天知道他要吆喝到哪一年。
“南哥,Angels Kiss 是第一次配,没可可酒。枸杞酒替的,颜色不那么正宗。你尝尝。”俄罗斯轻轻摇晃着高脚杯。
“我才不喝什么天使之吻。我才不准你进什么大地公司。”推开酒杯抓住她的肩。我狐狸般嗅到一股不祥的气味。
“南哥,人家不得不去。”俄罗斯放下酒杯,两手绕着我的脖子,绯红了脸。“不得不去呀,合同都签了。”
“签签签,往后怕你工作不起。在哪个年龄做哪个年龄的事。你家送你来打工?天气这么爽,多好的看书恋爱的日子。你俗不俗?”
“打工也是学习的一种方式。”
“胡闹!香儿不是已经证明了这种方式?”
面红耳赤争半天,俄罗斯不但没回心转意,反倒劝我快喝酒吃饭送她去礼堂。两点钟大地公司的车来接她们。
我无动于衷,向楼板翻着一双死鱼眼。
对于爱,我可以迁就;对于女人,却不见得。
“我嫁给你了?”俄罗斯甩出这句话,拎起包,兔子般冲出红砖房。我气咻咻站到绿窗边,她已经跑得无影无踪。白花花的水泥路上,卖牛奶的小贩也不见了。
抬过高脚杯,我狠狠地一饮而尽。
四十六
三姑娘回家这天下午,罗伯在院子里跳着骂着足足闹到太阳落山端公走进院子才收场。吓得三姑娘坐在我床上脸青面黑大气也不敢出。罗妈偷偷煮了几个鸡蛋过来,三姑娘哪里吃得下,她捋起绣着荷叶边的袖子伸手捡一个递我。扮个鬼脸,我毫不客气地剥鸡蛋吃。
我搬到红砖房的两个多月后才听到小买部的店主说起三姑娘的。那时候她已经私奔有一年零几个月了。罗伯一直视她为掌上明珠,巴心巴意等着招个好女婿上门防老。天晓得她吃错了哪付药,才听说她在自由恋爱,天晓得一晃就晃进镇山村兰老五家去。罗家在燕子坡也算得上有头有脸的人家。虽说自从大儿子犯案后家道衰落,但还不至于潦倒到笑骂由人的地步。罗伯纠集家族中几十人去镇山村几次问罪,都因为逮不到三姑娘而怏怏而归。我曾经仔细打听过,但店主死活不肯说,支使俄罗斯去问,还被那糟老头指桑骂槐说几句,弄得俄罗斯讪讪的,好久不肯去小店买东西。
“你爸爸也是,人家不肯上门就棒打鸳鸯,又不是旧社会。”我撕块蛋白丢在嘴里细嚼细嚼的。“先头听他骂得有山有水,好像兰家祖宗先人都对不起他,三姑娘你也真是。”
三姑娘听到端公依依呜呜的在堂屋里开始念神念鬼了,她说得小声小气。“怎么回事?兰老五的大爷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