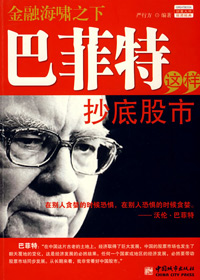蝶影抄-第1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人淡如菊味轻寒(代序)
钱红丽
有一句诗:寒来千树薄,秋尽一身轻。用来形容赵焰目前的写作状态很恰当。人到中年,好比人生走到秋天,一棵树一样,繁华落尽,剩下简笔和写意,特别淡,淡得可以站在树下看见淡青的天。但这种淡,肯定是有着丰厚底蕴的,由一种胆魄支撑。如今的文坛,小鬼当家,出版商适时端出千万版税的大餐,是利益双方一体化的共谋。当多年以后,再回头检阅,那不过是一阵风现象。无论哪一个朝代,真正的文学都是寂寞而少众的。文坛一阵风现象与文学创作是迥然不同的两个概念。像赵焰这样的一批作家,才是砥柱,他们的作品是有生命力的,多年以后去读,也不过时,即便现时并非那么火——真正的文学,注定不是靠一把火去延续的,它靠的是灵魂与灵魂的浸润与绵延,最后与时光握手言和。
最近,我们都很激动,源于赵焰的长篇传记随笔《晚清有个李鸿章》热卖,《百家讲坛》也在与他联系。于是都急急跑去询问什么时候去北京录制节目。只听他淡然一句,哪是这么容易的事情……事先我们激动着设计的场面都逐一退场。他就是这么一个沉得住气的人。迟子建今年在第三次领取鲁迅文学奖时说过一段话:作家就像一个赶路的人,一直走一直走,突然得了奖就好像迎面吹来一阵意外的风,感觉挺凉爽的,但如果没有这阵风吹过,这个赶路的人还是会一直往前走。我想,迟子建的恬淡明朗适合所有的写作者,没有名利,他们同样会独自一人坐在电脑前“赶路”……
宋代《全芳备祖》一书里,对菊花有过言简意赅而美丽异常的概述:所以贵者,苗可以菜,花可以药,囊可枕,酿可以饮,高人隐士篱落畦圃,不可一日无此花也。用来形容赵焰这个人和他的写作同样恰当——他的气质颇接近于菊,清淡,渺然,通透,散发出的,不是酒味浊气,而是药味清寒。如今的中年男,但凡稍有些成就的,其显著的标识,人未来,而肚腩先到,臃肿,拖沓,智慧愈少,酒量渐长,浑身上下,鬼气森森,让人敬而远之。赵焰是不同的,他始终保持一股气场,更多的是书卷气,这一股气也长。——就在这种长气里,同样还饱含着谦卑。古人一直说文如其人,这在赵焰那里很统一。总之,他是一个很明白的人,有足够的自省精神,所谓以人品立身,文品立言。
为什么说赵焰的写作接近于菊呢?那是因为不仅仅“花可药囊可枕”的本事,他简直无所不通,什么样的体裁都曾涉足,小说、学者大散文、球评,花花朵朵,不一而足,且持续稳定地增长。做一个多面手是很不简单的事情——所以我又常常说赵焰是一棵树,有发达的根须、源源不断的营养供给,这决定了他的强大体系。正是这种有体系的智性写作,让他拥有着永不枯竭的源泉。相比那些天才的感性写作,智性写作更值得我们尊敬,毕竟,感性是短暂的,靠激情的火花点燃,一旦熄灭,也就无法挽回,注定是短命的。而许多人的写作,只能从老根上开几枝树叉,最好的是在上面开几朵花,而赵焰则是整棵树,一种温州地区特有的四季柚,据说常年花朵不绝——现在我要说的这朵花,是赵焰的电影随笔。
电影随笔与读书随笔一样,同样是看似容易实则需要真工夫的活计。人人能写,但出彩的较少。所谓门堪低,若舞出七彩龙腾来,实在寥寥。说到底,写作就是在拼一种境界,视野开阔,阅历丰厚,看似信手而来,实际藏了气象万千。这是他的第二本电影随笔,延续了第一本的气场,像娓娓的人生,没有迭宕华丽,更显淡静平易。吃文字这碗饭的,仿佛都在心照不宣——写作就是不断地摒弃形容词的过程,山寒水瘦才是本质,一如我在文章开头引用的那句诗:寒来千树薄,秋尽一身轻。就是这个意思。齐白石晚年,略略于宣纸上点几滴墨,就是一只舒展好玩的虾,那得需要多少风霜作底呢?写作同样如此,去繁就简以后,丘壑都被掩护在冒似简静的几滴墨之下了。
我有幸作为第一读者,眼看着他在忙碌的间隙成就了这本《蝶影抄》。光影人生,不是用来走笔抒情,而是用来淡然呈现的,许多人生的道理,都埋伏在此,等着一个个同生共气的读者……
即将过去的2007年,对于这株赵焰牌四季柚,可谓收获破丰,他写下了十几万字的新安江走笔,出版了另一本关于徽州的思想随笔《千年徽洲梦》和眼下热卖的《晚清有个李鸿章》,另加这本《蝶影抄》。一个人的写作能量不是瞬间形成的,而是长久地积蓄,然后被他系统性地释放出来。一棵树,不是一夜间郁郁葱葱起来的,得益于沃土与底蕴的成全,无论一棵树还是一个人,都是如此。写作成全了赵焰,而阅读成全了许多喜爱赵焰的读者。
春天的N个瞬间
创刊不久的《体育画报》最近出了一个专辑,直接引进美国版的泳装特刊,好看。当我收到杂志撕开信封后,刚扫了一眼封面,脑子里便闪了一个念头:春天来了。是的,春天来了,活色才能生香。那些摄影师怎么能把一个人拍成一朵花呢?用很俗的比喻,就像一朵朵出水芙蓉似的。我看过一些模特其他的照片,近看,并不太妙。但她们此番组合,却是完美无比。都说漂亮的人不少,但拍起来真上相的,并不多。并不能怪那些姑娘们,一个人只有一个角度是相对完美的,是那些不太聪明的摄影师,没有发现她们的最佳角度。
春天的时候有些情绪是无来由的。譬如昨天晚上淘碟,看到莫妮卡·贝鲁奇的一部新电影碟片《我与拿破仑》,心头一热,就掏钱买了,买回来立即看,才发现又是一部烂片。其实我本不该这样的,这个漂亮而性感的女人自 《骇客帝国》当中露了一下脸后,近来的电影总是让人不忍卒看。这一部电影同样如此。40岁的贝鲁奇在电影中壮实得就如同一头母牛,而且恶俗无比喋喋不休。我最讨厌的就是电影中滔滔如江水的对白,不喜欢那些肥皂剧,不喜欢相声,甚至不喜欢现实中唧唧歪歪的人。有什么必要那样喋喋不休呢?有时候一个眼神,一个表情,就全明白了。想用言语来推动一切的人,其实都有点愚蠢。
这段时间,看碟还真有点多。自从今年春节完成《千年徽州梦》的写作后,本来想把沉重的徽州踢得老远,但盛情之下,又不得不从事另一项与徽州有关的写作。一个人很长时间陷入区域文化的磕磕绊绊是可怕的,那样的感觉如同蜘蛛,在那些千丝万缕的纠缠中无法挣脱。所以在我跌入徽文化山谷的同时,我总是拱动着挣脱的欲望。这样两相矛盾的结果,常常使得我在一段思考和写作后生吞活剥色彩斑斓的电影大片,比如说 《硫磺岛来信》、《汉尼拔前传》、《300斯巴达》、《香水》等。
还是谈谈《香水》吧——
德国小说家帕特里克·聚斯金德的《香水》是我在新世纪中看到过的一篇最好的小说,2002年我在一个周日的下午读完这部小说之后,曾经深深地倒吸一口凉气。故事讲述一个从出生起身上就完全没有味道的男子葛奴乙,对于气味,他有着无与伦比的鉴别力,能嗅出所有味道后面的时间、地点和意义。不仅如此,葛奴乙还能制造出独一无二的香水,他的制作方法并无不同,唯一区别就是,香水的原料来源于处女的体香,只要葛奴乙挑选中的女子,便不计一切代价将她杀死,然后,攫取女子的体香……小说的奇妙之处,在于一种匪夷所思的想象力,并且,这样的小说本身也有着内蕴,它让我们意识到无限的可能性,发现和指引一条路径。这样的感觉,就像在我们的面前荡漾着一线蛛丝,缥缥缈缈,看我们是否能顺着这根细腻无比的丝线,攀援,然后深入一种无限。
电影当然是成功的。导演是曾经拍过《疾走罗拉》的汤姆·提克威。看得出来,汤姆·提克威一如既往他的才气,还是想从形而下的故事中拍出形而上的云腾雾绕来。但我感觉他做得远远不及小说。与文字相比,影像所具有的穿透力显然要弱很多,影像很难凝固成坚硬的锥子,它无法锥得进去,并且扎出血来。文字一直是一种奇妙的东西,有时候,它的排列是可以铺出一条路来,它可以引领思绪一路走上去,深入到一种混沌。或者,文字本身就如同蛇一样,可以倏然游走,然后努力接近。一个人要想深入一个地方,必须借助于文字,拥有一种潜走穿行的咻咻感觉。
当然,影像也是有着长处的,它的长处在于制造一种整体氛围,让你感受到一种文字无法表达的综合。相比较而言,在这样的故事中,我在文字中可以嗅到香水的味道,但在电影中,更多地,我只是感受到一个诡异的故事,以及香水的千变万化。
除了看碟,这个春天里最欣慰的事情就是在新安江两岸看到大片大片的油菜花。虽然这样的行走携带着任务,但本身,还是快乐的。阳光暖洋洋,我走在燃烧着的油菜花中,头晕目眩。我的身体浸淫一片春色,我的眼中一片金黄……这样的感觉无与伦比。在新安江畔行走的时候,我总有点魂不守舍,我想独占这样的风水宝地,而独占的方式,就是在最美丽的风景处……呵呵,这样的行为总有点情不自禁——这同样也是来自春天的诱惑。
“香水”一直有着信号的意义。在飘曳的面纱后面,究竟是些什么呢?电影中那个制作香水的老师傅说:“世界的本质就在于它有着一种味道。”的确是这样,味道是可以穿越时空的,顺着味道溯源而上,后面往往是记忆,是细若游丝的路径;至于路径的后面是什么呢?天堂?地狱?——不知道,反正,那是一种无法捉摸的无限。
春天里大片的油菜花似乎也具有同样的意义。油菜花金光四溢,一派天真无邪。这样的天真无邪同样是有蛊惑力的,因为它携有,无所不在的香味。
温暖的暧昧
在我看来,索菲亚·科波拉的《迷失东京》应该算是好莱坞2004年度最好的一部电影了。它的好在于有一种恰到好处的克制,让人暖暖生香。这样的克制就同之前的《花样年华》以及后来的《卧虎藏龙》。看《迷失东京》是在2005年的一个冬夜,窗外飘着漫天大雪,我呷着茶躲在屋子里。自始至终,电影都有一根无形的红线在牵引。一直到结束,我才算松了一口气。好片的意义在于,它会在身临其境中体味到情感的温度,能在落花流水中享受着阳光明媚的精神远行。
一男一女。男的是逐渐过气的好莱坞影星哈里斯。一个有魅力的老男人。当身边的光华夕阳一样一点一点褪去时,那种悲哀和无力便如墙角边的苔藓悄然爬上来。哈里斯来东京是为拍摄一则威士忌广告,因为拍摄不顺利,他不得不在东京呆很长一段时间。在陌生的城市,哈里斯更切身地体味到异国他乡的孤寂,空气一样无所不在,然后,便是疲惫,便是厌倦——不仅是对生活的厌倦,也是对生命本身的厌倦。这时候,一个年轻女子出现了——她叫夏洛特,是一位年轻美丽的大学毕业生。在与一位摄影师结婚后,夏洛特陪着丈夫来到东京。因为丈夫寡趣而呆板,夏洛特同样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