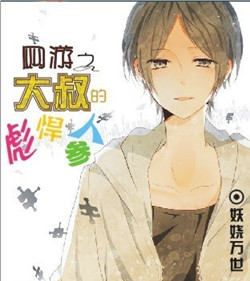新派小说之大话童年-第4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在那人生的开端部分,我的种种顽愚劣行真是不可胜数,都是真的。然而,我有错。。。。。。吗? 从我爸爸对我的教训看来,我一定是错的。但我知道我的爸爸,他那时候,至少在教训我哥哥的时候,他肯定是错的。因为小孩子,原本就是如此。
我的哥哥(2)
我的哥哥(2)
我哥哥,作为学校家属楼孩子圈中与沈二麻子并列的老大,实属泛泛之辈,只是因为年长于大家而已。从小到大的哥哥,既没有给大家出过什么鬼主意,也没有什么坏心眼,其事迹乏善可陈。
关于我哥哥,记忆中印象最深刻的是:他常常早上担着一担尿桶,去学校的厕所下面用大木勺勺满满的两桶屎尿。然后用肩挑着,匆匆赶往围墙之外百米的菜地里给我爸爸种下的蔬菜施肥。他人比那担尿桶高那么一点点。才早上七点左右,我从床上爬起来,拿着水杯刷牙,常常就看见我哥哥担着那一担空尿桶回来,脸上沾上了屎尿的痕迹,一付并不是很愉悦的样子。他人性子急,挑着满满的一担屎尿走的很快,远远的可见,那屎尿点点的飞溅而出。而他在施肥的时候,据我爸爸皱着眉头的唠叨,是很不令人满意的:他的动作快速马虎,老是分脏不匀。
小时候,我哥哥是很吃苦耐劳的。他一不怕脏,二不怕苦,三不怕累。还真的很耐劳。以前学校有口水井,但是常常没有水,所以只好到校外去挑。一个作为水源的地方是直线距离两百米之内的一口水井。如果那个围墙的洞补好了的话,就需要弯弯曲曲多走上里的路;另一个作为水源的地方是三里路外的大泉溏。不管是去到哪里挑水,我哥哥都是挑着那担家里最大的铁桶,以减少来回的次数。他从小学挑到中学,是伙伴们中最能挑的。
小时候,我们兄弟在家里的分工,就是我哥哥挑水挑粪,我洗碗筷并扫地。
那时候,我哥哥一开始是很让妈妈生气的。小学一年级他就留级了。他总是因为他自己说的看人家打乒乓球而很晚回家。而妈妈呢,老是骂他烂番薯。
但是那烂番薯,对弟弟却不错。他常常带我出去捡拾那些彩色的烟盒子,拆开用来做打包包的包几。我记得有一回,他还拿了五毛钱,叫我和他一起去看录象。但可惜的是,那一场录象,我们去的时候,已经在上演了。我们才看了不到半个小时,就完了。
他还曾经从同学年建那里借了一些课外书来看,并且允许我站在一边也看看,我于是也看了一些。特别是那本《格林童话》,那时候,我真的太喜欢了。我至今还记得那时候看的一些故事情节,并且如今还买来看看,仍然觉得很喜欢。它在我心里有着至高无上的地位,就象博尔赫斯所说的:那是德国人所写的最好的一本书。而那本金庸武侠小说,原本破破烂烂的,没有了封面,那时候我都不知道叫什么名字。我还没有看完,我哥哥就还了书。但我老记得是讲杨过和他姑姑小龙女的。我记得看的时候,我老想着自己要是杨过就好了。特别是在看到那坏道士*了小龙女的时候,我心里是觉得很生气很惋惜的。我一直相信,就是那本书给我埋下了偏向于喜欢年纪大于自己的女孩子的种子。
我哥哥曾经跟他的班主任老师的儿子刘水根要好,还去他家的谷仓抓过麻雀。而我们一群伙伴,也曾经跟着刘水根上山玩。因为就他年纪最大,所以大家都相信了他,拔了一种野草的呈圆珠状的根来吃。结果一个个喉咙感觉渴的要死,喝水也无济于事,那种难受啊!比生病还可怕,真想把喉咙挖出来。。。。。。
那一次,好像就刘水根一个人没有吃那个东西。而我哥哥呢,好像是在大家都吃过那东西之后也一样的难过。但我们却是通过他才认识了他的这个好朋友。
我现在都有些怀疑我哥哥的难受是装出来的,怀疑那事情是我哥哥跟刘水根窜通好了,特意整我们的。
读小学的时候,学习成绩特别不好的同学,就得要留级。我妈妈在饭桌上常常要讲到哥哥小学一年级留级的丑事。而我哥哥总是在一两天之内的什么时候对我傻笑着说:我读小学一年级的时候,班上还有个女同学,读了十八年的小学一年级,至今还在读小学一年级。那时候,我相信我哥哥说的话是真的。但是现在,我就有点怀疑了。
因为我想起我哥哥也有过奸诈的时候。比如,每次吃东西的时候,我哥哥总是吃完自己的,就来吃我的。而我也因为学了那篇什么孔融让梨的课文,懂得了礼义之道。我不但每次有什么好吃的,分为两份之后,都先让我哥哥挑了那份多一点的。而且我哥哥后来吃完了自己那份,还要吃,我总是再给他一些。但他向我要的多了,我便逐渐认识到孔融的错误之处。然而,我哥哥吃惯了。不论我把东西藏在哪里,他总是能找到,并以他从来不留下一星半点的犯罪特征让我察觉就是他偷偷吃掉了的。再比如,从小到大,我们兄弟两都是睡在一张床上,直到我们家自己建了房子。那时候,并不是家家都有电风扇的,我们家就没有。家里常用的是那种棕树叶做的扇子,而且还不是一人有一把,而是我和哥哥两人共用一把。我记得有一个夏天的晚上,实在是很热,热的几乎睡不着。我和哥哥约定两人轮流相互用扇子给对方扇风,他让我先给他扇一百下。而我给他扇了一百下之后,他就说他不来了,他要睡觉,明天再说。而到了明天,他又说先欠着。
但是那时候的我,只记得我哥哥因为跟金根欺负老趟子,玩他的小*而被爸爸狠狠的教训过一次。只觉得他因为怕我爸爸而特别老实。还不懂得将一些事情联系起来想想。我一边在心里盘算着如何在数到70的时候,趁着哥哥的心不在焉,一下子跳到80,然后再81、82的数;一边大声数数;一边卖力的给躺在床上先是傻笑着,后来几乎已经睡着的哥哥扇着他一开始所要求的“大风”,把蚊帐都吹的一下又一下飘飘荡荡。。。。。。
。
我的爸爸
我的爸爸
小时候,我老觉得我的生身父亲,一定是一个腰缠万贯的大富翁。我一直幻想着他会来接我回家,而且好几次都梦见他了。在那些美梦中,我总是得到吃不完的五颜六色的大把大把的糖果。我把它们摆放在自己的面前,我一颗也舍不得吃。我想等我哥哥来。
我爸爸虽然是所谓为人师表的人民教师,但更是一个玩世不恭的家伙。爸爸说那些带有*意味的玩笑话,在地方上是出了名的。我从小就说话有些不注意,甚至常常不亦乐乎的说些带有*含义的话语。这都是受了我爸爸的影响。我从小就听习惯了爸爸的那些话,根本不以为怪,根本不知道那是不能说的。从小到大,当我说##/#/##等等的时候,我就像是说一件很寻常的家用物件一样根本不知道羞怯与羞耻的存在。我从小就说话有些不注意,甚至常常不亦乐乎的说些带有*含义的话语。这都是受了我爸爸的不良影响。我从小就听习惯了爸爸的那些话,根本不以为怪,根本不知道那是不能说的。
我们地方上一直是以编爆为主要外销产品。在编爆生产上,有一道工序叫做栽引,是将一短截一短截的引线栽插在那并列着一排排小小洞口的六边形饼盘上。读小学的时候,每年暑假里,我们兄弟都是坐在家中载引,每人要交十三个栽好的引饼。我爸爸在另外一个地方教书的时候,有一回被问到:文老师!你常常说那些话,水平之高,令人佩服!你做那些事情,是不是也很厉害啊?未必吧!要现在有九个八个的女人站在面前,怕也吃不消吧?而我爸爸却简略的回答说:这,小事一桩啊!我跟栽引样的,一个小洞一个小洞的来对付。
小时候,爸爸总是戴着那顶灰蓝色的鸭舌帽,样子相当怪。我老想跳起来掀起它手一扬将它扔得老远。
大概是我稍长的时候,爸爸又学会了剃头的手艺。买来了几种剃头的工具,将我们哥两往他自制的木凳上一按,一个一个来。剃完站起身走到镜子前面一照,样子是十足的丑,十足的怪。从那个时候起,我第一次萌发了要上理发店的愿望。在此之前,不管头发是多么的长也没有过这样的愿望,即便是从路边的理发店经过,也很少往里面望一眼。一直到我们兄弟读初三的时候,爸爸给我们兄弟所理的发型,只有一种:就是《红楼梦》上所说的“玛子盖似的”,旁边没有一点毛,就中间一簇毛。而且刚开始的时候,还并不是特别的像,丑的只想一把?下来。
小时候,农村里都是用那种做编爆的长长的红色的纸条擦屁股,我们家用的是爸爸从学校搬来的废纸。其实家里也有卫生纸,但爸爸和妈妈总是说是女人才用的。有一次在学校的公共厕所,我看见伙伴用的竟是卫生纸,从此才知道不只是女人才能用。小时候,家里的经济条件一直不大好。但在买零食的时候,爸爸比妈妈是更为舍得的。我记得那时候大家都还没有吃过葡萄,可是爸爸却带着我在县城的攘攘人流中问过价犹豫着走开之后又回头还是买了一斤。
记得小时候爸爸带我到萍乡公园,坐那种空中转圈的飞机。那时候,太阳是火辣辣的,而那飞机上的座位也是滚烫滚烫的,但是爸爸坐在我的身边。虽然我想离开,虽然我也想问问爸爸:你热不热,座位烫不烫?但我既没有离开,也没有问。
很小的时候,爸爸带我去过一次长沙,买了一杯红色的冰水,很多年以后我还向同伴们炫耀,因为我们家那边几年以后都还没有得卖。而我在长沙街头,最高兴的事却并不是能吃到这种红色的冰水,而是能看到捡到很多彩色的烟盒子。那时候,与同伴们做一种游戏时,如果拿它的纸张充当制作材料的话,比普通纸张珍贵十倍百倍。
每年暑假,家属楼的老师们都要拉来一小车一小车的煤炭,在水泥地面的篮球场上,用那做煤球的器具做煤。到我们读初中的时候,我记得我们总是利用那个老师当年举重用的铁棒子来砸碎那些筛出来的煤块以便将它们掺上黄土并做成煤球。
我初一的时候,就开始在我爸爸的指导下开始做煤球了。我跟哥哥一起,兄弟两同样高高卷起裤管,打着一双赤脚。从初一的时候,一直到从学校家属楼搬走,每一年的暑假,我们按照一定比例,利用铲子与耙子将少量的黄土与大量经过筛子筛选出来的燃煤混合搅拌均匀并成堆,再将那堆经过铲和耙之后仍然是黑色的煤堆从上往中间挖出一个大洞。接着,我哥哥用大铁桶,我用小铝桶,兄弟两挑来一担又一担的水往煤堆中间的大洞里倒,一边倒就一边搅拌,直到煤堆像土块一样变成一块均匀细润的泥巴。最后,我们兄弟两就站在那堆黑色的煤泥巴旁边,用那个接近一米高的手工制造煤球的器具一个一个的把一两千个我爸爸所要求的标准的煤球做出来。
制造煤球的过程中,那乌黑的泥水总是在我将那器具向那堆煤泥巴提起掷下并着力旋转的过程中飞溅到我的脚上、腿上,甚至是脸上。而我挨到的骂比我做出来的煤球还多。我爸爸像旧时代主人雇佣的忠实监工一样,站在一边,指手画脚



![[剑三]基三传之大战随便来封面](http://www.sntxt2.com/cover/1/1601.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