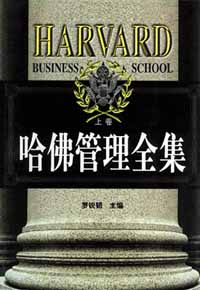站在时间之外-第16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了我的面颊。这更使我感到自己的难堪,虽然我知道这是无所谓的,即使小曼端着什么东西从厨房走出来,薇薇看了小曼之后看了看我,我没有表情的脸。薇薇露出了些许的不快。
当人们在用嘴用餐的时候虽然不需要语言,但没有语言的吃饭却似乎必然存在着某种危险。这时候人会把一些行为与动作留作语言:吃饭野外的手势,嚼的声音,喝汤时的声响。些些许许的声音能够那么清晰的传荡着,似乎掩饰着某种悸动,使人压抑。这不是我们所需要的氛围,一如它现在成为现实一样。我想要打破这局面,但又不知该说什么。这也许就是问题的奥妙之处。
我放下碗,略微的向逢薇薇说:
“这”
“这”
我并没有说下去,因为同时小曼也说出了那么一句话。我本来是向着薇薇说的,到这里已经显得不妥了。饭并不是我做的,小曼却在问我们。
突然间我们都放肆的笑了。
小曼侧向薇薇问,
“饭菜可口吗?”
薇薇点了点头。
“很不错,比我做的好多了。以后有时间我要多多向你学习啊!”
“不能啊,你一定是深藏不露者。”
我提议我们把这些餐具放下留待我明天收拾。但先是小曼,而后薇薇也坚持要洗刷完毕才能感到安然。她们两个去了厨房洗刷。我茫然若失,打开电视机之后一直有一个念头在提醒我应该做一些有意义的事。但我害怕自己这种因专注而紧张的感觉。也许真的会让自己不知所措。
她们两个的说笑声突然传了出来。小曼在擦拭着手上的水,薇薇在挽着自己的发,在一起向我这边走来,这种谐和使我产生了某种错觉。仿佛这一切都在美好之中,而在这之前,不管是小曼轻视薇薇还是薇薇对小曼不屑一顾都是无所谓的。她们坐下之后,宁静露出了破绽。也许在这之前,在走进小客厅之前,在洗刷完毕之前她们就一直都是安静的各顾各的。这种矛盾和感觉我知道不是因为我,而是因为我的存在。因为至少在事实上我加入了她们两人的生活,她们一起在掩饰的什么。
“他坐在这里真像个寡人。”
小曼突然说出了这句话,不论被薇薇听到还是被我听到都无所谓。薇薇用轻轻的笑声应和了她,而我也不得不从我自己的沉想世界中回过神来,加入了她们。
“寡人,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吗?”突然觉醒的我有些茫茫然。
“你说呢?理解有很多途径,你一定进入了其中的一条。”薇薇故作高深地说。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但你不用臭美,我说的却只是你坐在这里的孤寂形象。”
小曼的这种解释反倒像是要澄清什么似的。
“那么你知道我想什么吗?你是认为我必然在想佳丽三千的事吗?”
“那又怎么样,只要是你就行了。”
薇薇觉得这是无所谓的事,小曼却露出了不屑。
“如果是现在,谁愿意做一个男人的玩偶呢?”
“并不能这样说啊?毕竟每一位皇帝都有自己的李夫人、杨贵妃,更何况武则天也是皇帝呢?”
我向她反驳,显然有些为自己辩护的味道。
“但是无论你说的哪一种都是少数女人才有的,三千分之一或几百分之一啊。你能想像吗?多少的宫怨情仇啊?”
现在似乎我突然间摇身一变成了那些朝代的隋皇明帝了。
“不好的是体制,并不是男人或女人的问题。难道现在不是这样吗?”
“自然是。”
许久未曾说话的薇薇漫不经心似的说。
让我不说话
薇薇依稀记得在自己17岁的时候父母才正式离婚。而在这之前他们已经长久的分居了,长的甚至大于薇薇的记忆。而之所以选择那个时间竟然是因为给薇薇一个交待。父亲是一个在本城小有名气的演员,但却常常的不回家,在一年之中见不到两次面。回家之后对薇薇也是冷冷清清的,对母亲同样没有好气。身上永远散发着葡萄酒的气味,仿佛这就是他的气息一样。薇薇说后来有一段时间,大概是中学的时候,她有些依恋这散发着酒的气息的感觉。父亲对自己的不好深深的印在薇薇的记忆里,也许是有一次薇薇漫不经心拿起父亲放在桌子上的手机,这时父亲从洗脸间走了出来。由于害怕,薇薇松开了拿着手机的手。手机掉落在地的巨大声响把母亲惊动了出来。父亲给薇薇一个耳光,并骂了一句“婊子养的。”的话。这给薇薇的打击很大,以至于现在都不敢理会这一个词的意思。也许正是从那时开始,薇薇认为自己不是父亲甚至不是父母的女儿。因为那时,母亲的愤恨的眼睛死死的盯着父亲,完成着不被人知的话语。这种印象即使是在许多年后的今天依然使薇薇感到历历在目。仿佛这种破败的结果可以被永远的烙在心里。也许薇薇一直都想要在忘记。但对于自己,母亲却从来不谈及身世的问题,甚至使得薇薇一直感觉自己是否一直都是一个被遗弃的孤女。
“直到去年母亲去世之前,我才彻底的感觉到即使是有母女关系的我们也是在若既若离的尴尬之中相处的。似乎包括以前的和父亲在一起的时日。即使是在父亲离去之前我都有一种感觉:我的这个家是可有可无的,而这亲情也是可有可无的。因为母亲一直养育着我却使我感觉不到爱。和她的那些学生相比我似乎只是一个和她住在一起的、称呼她为妈妈的、享受她的给予的学生。我和母亲似乎一个保持着一种莫名的距离,像是一种天然的正负极。在和母亲的生活里我一直有一种奇怪的感觉:是否的只是父亲的女儿或者我和他们都没有关系。而这种感觉的忽隐忽现使得我甚至对母亲的抚养都很少清晰的做出感恩的判断。母亲给我最好的生活、要我学钢琴、学奥数、进学习班,给我买最喜欢吃的、让我穿最喜欢的衣服…。这又能代表什么。她给我买的衣服越多我越感到空虚,我越是难以忍受这没有感情的亲情。而母亲也总是不说话,不论是否有什么秘密。我总感觉不到生活的幸福。但我又不敢去颓废堕落。因为在母亲来说我几乎是她人生的全部,除了和亲戚的交往之外她几乎没有什么要好的朋友,休息是就经常在家,不停的做家务,辅导我的作业,听轻音乐或上街买东西。这是她和父亲分开后养成的习惯,也是我印象中的全部。后来我去外地读书,她我生活可能就更加荒凉了。我曾经试图经常和她联系,但往往在打电话的时候不是一开始就尴尬就是说不几句话就无言了。这真的是一种痛苦。甚至有时候我努力回家,结果都不能给她带来什么快乐。母亲四十三岁就去世了。而她生下人时却只有十九岁。多么可怕啊!这是什么和什么恐怕永远都是秘密了吧?”
薇薇陷入沉思。仿佛在她的心中关于对母亲的感觉都是复杂的,甚至不知道在母亲和自己之间到底存在的联系是什么。
“我难以准确的把握对母亲的理解,一如对父亲的感觉。”
薇薇喃喃的说,陷入了痴呆。仿佛不是为了对我,而是在向一个自我言说的自己而说的。
我跪在地上,就那样情不自禁的伸出了手,抚摸了似乎早该泪水涟涟的薇薇的脸。
薇薇怔了一下并没有拒绝我。她抓着我的手,紧紧贴在自己的脸上,好象安于这种怜惜。
小曼突然站起的身影惊动了我,我突然的意识到自己所在地方,对这一切感到莫名其妙。我没能说什么。小曼走向了洗手间。
“你怎么了?”
薇薇问我。
“不知道,也许没什么,没有吓到你吧?”
我怔怔的说,同时发起呆了,脑子里感觉一片空白,仿佛行走在某个白色而漫无边界的夜里。什么和什么都混在了一起。仿佛下雨的黎明天空翻起的鱼白肚一样无边无际,难以把握。我又看了薇薇一眼,她在看着我,也是面无表情的。她在发呆,在想一些事情或在空白一些思绪。
小曼走了过来,似乎是从远方走来的。她穿过客厅,打开了门扉走出去并把门安然的关上。薇薇拉了我一下。我几乎无动于衷的摇了摇头。
“她已经生气了,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这样对薇薇说。
“你可以对她说清楚,这是你的性情,并不是你要漠视她。”
我站起身走向门外。小曼站在外面,这是我未曾想到的。
“你很过份啊!”小曼这语气像是在质疑而不是为了责怪。
“我知道是我的不对。但并不是不尊重你。……你也知道,我是一个伤情的人,这…也是因为情不自禁。希望你能够理解,并且不要在意。”
小曼并不听我的说辞,向路边走去。我没有心情拦住她,也不想这样做,因为也许这本身就是毫无意义的。但愿小曼能想到我的心情,并且理解我。无论如何,该发生的都己发生了。
小曼坐上了的士。我在门外站立了片刻,在走向屋里之前我看了一眼尚未义街六号。那座曾经的房子在黑夜里有一种东方沙漠中的幽灵气息。但一如这一排房子一样。它身在这城市之中,给人一种孤独的秩序。我不仅慨叹;做为每一座房子的特别之处也会和每一个人的特别之外一样的在这漫漫长夜中的城市里注定孤独吗?尚义街六号是如此,尚义街六号的曾经的过客是如此。而在我这里同样是尚义街的事。我是否是能够面对一些和此同样的悲哀呢?至少在这特殊之点是那么的不被理解,而且似乎一直不能被理会。
薇薇不在沙发那边,甚至似乎不在屋里。这使我心中惊慌,使我错愕:是否刚刚我送的是薇薇?抑或是我把薇薇和小曼一同送走了。我正在错愕我野外薇薇却从里间走了出来。拿着一把吉他——那是老房主留下的唯一的乐器。
“你会弹吗?”
薇薇问我。
“不会从未接触过。”
“那么你喜欢听什么。”
“不知道,不如就弹《漫步时间里》吧?”
“为什么要选这首呢?其实我不想弹。换一首吧?”
“那随便吧,反正我是无所谓。也许什么都好听也未可知。”
于是薇薇就坐在地毯上背靠着沙发。我也这样的坐下,而且把头放在沙发上仰面看到了天花板。薇薇久久的安静着。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她在想什么。但我知道,我只需要这样的安然若素就好了。好一片安静之后响起的清澈的乐音。
“这一首是德彪西的《月光》。”
薇薇在提醒我。因为在我来说一个题名就有一种流动的感觉让你形容它,认清它并且深入它。旋律与感觉之间的对话一直在摇曳,使心寻找到一处港湾之间浅浅的月亮之光。
我站起身去,把灯光灭掉。回到原处静静的聆听。
“这一首是《即使被雨打湿》》”
“《蓝天鹅绒》。”
“《绿色菲尔斯》。”
“《通过你》。”
“《挪威的森林》。”
我不禁泪流满面。因为此处票据的音律不是同样可以传到尚义街六号吗?那死去的魂灵也许重又复活。只为这倾听。我难以自己,很多时间从此渡过,很多时间以前的某一个夜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