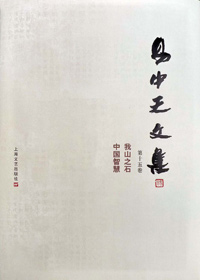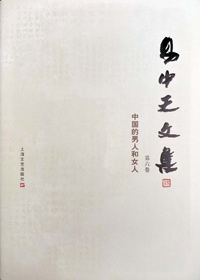��ѧ��:�������ļ� �ڶ�������ѧ������-��9����
�������Ϸ���� �� �� �� �ɿ������·�ҳ���������ϵ� Enter ���ɻص�����Ŀ¼ҳ���������Ϸ���� �� �ɻص���ҳ������
��������δ�Ķ��ꣿ������ǩ�ѱ��´μ����Ķ���
��塣��������������뿴����
�����¡���ѧ�����ʣ�5��
���ĵ���һ˼�룬�ڡ�г����ƪ�����ʮ����ȷ����Ϊһ�����壬���IJ����ر��ͺ��ų⡰г�ǡ������������˵������з���裬�������裬������䣬������䡣��֪г�����������ӡ������ǣ���ǿ��ָ����г�������岻�ţ������ױס���������Ҫ���ף������ڡ���Ϸ�����������������綫��ö�ޣ���������������κ��Ѧ�ۣ�������ʱ�á���κ�����������п���������������֮�ǡ�����ڮϷ������油����������Ϊ�����Ĵ�֮��г����Ʃ����֮��С˵����������С�������˴Ŵ������г��������������μ����������Υ��������ֹ�豩������������������������ڼʹ�������������䡱�����ǰ����ɣ��Թ���������Ҳ����������ǿ����г��������롰������ʱ��������롱��Ҳ���DZ��������֡�dz�������ס������Ժ��������̺���̡����ŵ�˼�����壬�����Ҫ������������ҲС��ȡ��Ҳ��˼��������һ�µġ�
��������Ȼ�������μ�����Ҳ�ã�����Υ����Ҳ�ã����ߡ���ʫ��ƪ����ġ��������ԡ�Ҳ�ã�����һ��������ã�������ȷ��Ŀ���Ժ�ʵ���ԡ���ˣ����ĵ�����ԭ��Ҳ��ֻ��һ��ʵ������ԭ�������ͼ������ʿ��µ���������ԭ��ͬ������ͼ��Ϊ����û���ã�ʫ��Ӧ�ñ��ϳ����������Ϊ������Ϊ��Ӱ�ӵ�Ӱ�ӡ������ﵽ���Ե���ʵ������ʿ���������dz�֮Ϊ���Ķ���������ġ�Ŀ�ġ�����Ϊ���ﶼ���������Ʒ�����˵��������������ͼ��Ŀ��Ϊġ�¶���Ҳ�Ϳ��ܱ���ʵ�������Ҳ����ʵ�������Ͽ�����������һ�۵��������������֮�������������ԡ��ġ�Ϊ������������Ʒ�������ġ�����������ȴ������������һ���������µ����֮����Ҳ����˵�����������������վ����˵������������վ���������������أ�Ч���������������ֻ��Ϊ�ˡ����˼͡������ھ��������������IJ�˵����Ψ����֮�ã�ʵ����֦����������֮�Գɣ�������֮���ã��������Ա�������������������������־��������ѧ�����ã������Ȼ��ʵ�������������������֮�У��������ڶ����ԡ������������ġ�º���ʶ֮�ϡ������ڡ�ԭ����ƪ�����İ��⡰�������������Ӳ�������������֮���ĸ��ݣ��������һ���ڱ����۲������������ʹ����Ҳ�Ͳ��ٱ��ἰ�ˡ�
�����෴�����ĵ���һ���١��ٶ�����ǿ����ѧ��������������������������������ã�ʫӦ�á��������ԡ�������ʫ��������Ӧ�ܡ������˷硱�����ָ����������¡��������ģ���������������±���������г������Ҳ���롰������롱����г����������Щ�۵��ڡ����ĵ�����һ���ж�α��ἰ�����һ�ר��д�ˡ�������ƪ����˵��Ϊ��ʹ��ѧ�ܹ��ﵽ����ʵ��Ŀ�ģ����Ҹ��˵ĵ��������Ǻεȵ���Ҫ�������Ŀ�������ѧ�����������������������ھ�����ҵ���ǡ����ӡ�������������α����ศ��ɵ��������档��˵��
�������Ծ��Ӳ�������ʱ������������ҵ�����������ԏ��У�ɢ���Ա��⣬������ʣ�ԥ����ɣ����ı���γ���������ر����ζ�������������Դ��ģ������ʱ�ԳҼ����������ˣ�Ӧ����֮ʿ�ӡ�
�����¡���ѧ�����ʣ�6��
����Ȼ�������ġ��롰�Ҽ�����������֪ʶ�����ڡ������Ұ��ʱ�͡�������ˣ�ʱ�����ڷ⽨��ҵ�����ֲ�ͬ��ʽ���ˣ����ǵ�Ŀ�ģ��������ǿ���������ޡ��롢�Ρ�ƽ��
������
����������Ӧ�÷���������������������ҵ��һʵ������ԭ��������������������������ԭ��������ƪ˵����������ʿ����֮���ģ��ǹ����ö����IJ�Ҳ������ʵ�������ö����IJɡ���Ҳ�����Ķ���ѧ�Ĺ涨������ѧ����Ӧ����ʵ�õģ�����ͬʱҲӦ���������ģ�����˵�ø�ȷ��һЩ��������Ϊ��ѧ��ʵ�õģ��ű����������ġ���Ϊ����֮���ģ���֮��Զ���٣�����֮�ԣ�������������Ʒ����Ȼ����������֮��㷺��������ȻҲ�����ڴ����в�����Զ��Ӱ�죬����Ȼ������ʵ�֡�������֮��Ŀ����ʵ��Ŀ�ģ�Ϊ�ˣ�����ʮ��ǿ����ѧ��������ʽ�������ڡ���ɡ�ƪָ����
������Т�������䣬ɥ�Բ��ģ���֪���ӳ���δ����Ҳ�������ӡ���α���ʳơ����Բ��š�������ǧ�����������ӡ�ׯ���Ʊ�����ν����Ҳ���������ɱ�˵��ν���Ҳ���������˵�������Ա���Ĵ�֮�䣬��˹���ӡ�
����Ҳ����˵������������������Ϊ�����Բ��š����ˣ�������������Ϊ�����Ժ��á����ˣ��Լ�����������ͬ��������������ʽ��������˵һ���ء��ġ������ʥ���ˡ��ڡ���ʥ��ƪ����һ��ʼ��˵��
����������Իʥ������Ի�����������飬�������ܣ��������£��ɵö��ţ���ʥ��֮�飬�����Ĵ��ӡ�����ʥ�������ڷ�����ӷ�ɣ����ڸ��ԡ�����־������ģ����Ŷ����ɣ��˺���֮��뺣�����֮����ӡ�
��������Ȼ����־������ģ����Ŷ����ɡ�������֮��������ֿ����������ʵ����ʽ���ɡ����������ţ���ͬƪ��ν���λ�����ʵ���������ǡ�ʥ�ġ���Ϊ��ѧ�ĵ䷶���߱������ʡ���ˣ���ǿ����ѧ������Ҫ�Եġ���ɡ�ƪ��������һ��ƪ��˵����ʥ����ǣ��ܳ����£��Dzɶ��Σ�������Ȼ������ָ�������ν��ʥ�ˡ���Ϊ����֮���������ǡ��Dzɶ��Ρ��ĸ���ȴ�������¡���Ϊ�����ᷨ�������������������Ծ����ʵ�����Ѿ���������ʽ���ɣ�������������ѧ�����ѧ���Խ�ʯ��������仰�������������ʥ�͵ľ���������֮����Ҳ���Գ�Ϊ�����¡�����Ҳ���Ա���Ϊ��ѧ��Ʒ��������Ϊ���Ǻ��ڡ����ġ���������Ϊ���Ǹ��ڡ��IJɡ������ڡ����ġ���ֻ��ʹ���dz�Ϊ���䣻���ڡ��IJɡ�����ʹ����ͬʱҲ��Ϊ��ѧ����Ȼ�������Ŀ��������ڡ����ġ���Ҳ��Ȼ�ḻ�ڡ��IJɡ�����Ϊ���������ġ������������ǡ����������ʡ���������Ϊ���壬��Ȼ����һ��ʹ�Լ��Ĵ���������IJɡ��߱�������ʽ�Ĺ��ܡ������������µ��֮����ɽ�����֮�Σ������λ���ʵ֮�£�����ǧ�˰�̬֮�ģ�������Щ�����ǡ���֮�ġ�����������Ȼ��ȻҪ�����IJɣ���ô�����ڡ����ġ��ľ��䣬���в��߱�������ʽ�ĵ����أ�
�������ĵ���һ����˼���ڡ�ԭ����������ʥ�������ھ�����ƪ��˵��ʮ���������ǣ����˵�ڡ�ԭ����ƪ�������Ǵӡ�������������������֤���ġ��Ĵ��ڸ��ݵĻ�����ô���ڡ���ɡ�ƪ���������Ǵӡ��ɡ������ʽ��������֤���顱����Ҫ���塣��ˣ������������һ����ǰ���ѧ������һ����������ʽ�ṹ���Dzɶ��Σ�����������������ʽ�ṹ��Ӧ����һ�����ݵ���Ȼ���֣���˵����txtС˵�ϴ�����
�����¡���ѧ�����ʣ�7��
��ˮ����������ᣬľ��ʵ���������ĸ���Ҳ���������ģ����AͬȮ��Ϭ����Ƥ����ɫ�ʵ��ᣬ�ʴ���Ҳ�������������飬��д����������֮�У�֯������֮�ϣ���Ϊ������Ȳ����ӡ�
������ν���ĸ��ʡ�������˵һ������ʽ������ֻ��һ�������ڱ��ʵ����ڱ��֣������������͡����ࡱ�����š�ˮ���롰ľ���ġ��顱�롰ʵ��һ��������������������ʸֱ�������Ļأ���Ȼ֮ȤҲ������Ʃ��ˮ��������ľ��������Ȼ֮��Ҳ���������ơ�������ν���ʴ��ġ�������˵һ�������ݱ���ͨ��һ����������ʽ���������Լ������绢�����û�а��ƾͻ���ΪȮ��һ�����������������ʾ����Ȯ��ı������𣬾����������������ѧ��Ʒ���ڵ��IJɷ������ʾ����С�˵����𡣸�������ˣ����Ҳ����ˣ����Ե�ʢ�紾�ġ�����������Ȼ�ǡ������������¡�������ҵ��ġ��ܴ�������Ȼ�ǡ����������ա�����˿��ӡ�Զ�������������ʼʢ�������ܴ��������տɴӣ�����������֮��Ҳ��������ʥ������������ˣ��¼�����������ˣ�����һ����������ʽ��ʾ�ž��ƾ������������ʡ����֤���ˣ����ijһ��������ݺͱ��������ģ���ô������ʽ�ͱ���Ҳһ���������ģ�������˵Ҳһ�������ijһ�������ʽ�ͱ��ֲ�������ôֻ��˵���������ݺͱ���Ҳ�������á�
����������������������������ʽ��ͳһ��ԭ����������֤����ѧ��Ʒ������һ����������ʽ�ṹ����ѧԭ������ѧ��Ϊ�����鷢��Ϊ���¡��ġ����ġ����ǡ����ԡ����ֳ����ġ��IJɡ������顱�롰�ɡ�����ͳһ���ศ��ɣ�ȱһ���ɣ���Ϊ���ݡ�����������������ԡ��⻯Ϊ���IJɡ�������ͨ�����Դǡ���һ�н飬���������������������������������ġ������ԣ��DZ�Դ�����ġ����IJɣ��ǽ�������ԡ���������Ǵ�ǰ�ߵ����ߵ��м价�ڣ��DZ��ֺʹ�����ԡ��������ֶΡ����ڡ��ԡ��������ƿ����ȽϿ��������⣺������ѧ�������ԴǺ����֣��������֣�������������ࣻ�����赸�����������붯����������������������ɫ�������������ԡ����ں���Ȼ������������������μ������ӹ���ʹ֮��Ϊ�������ԡ��������ԡ��������乲ͬ���ɡ�����ʥ��ƪ˵����������־���������ԡ�������ɡ�ƪ˵�����IJ��������ԡ�����������ƪ˵������֮���ԣ�������ġ�����ԭ����ƪ��˵������֮��Ҳ�����֮���ա�������ǿ���˶ԡ��ԡ��������Ρ�ʹ֮��Ϊ�����ԡ��ı�Ҫ�ԡ�����Ʒ����������һЩ�����ԡ����ɵ���������ʽ�ṹ���������ģ�ν֮�������ǽ�����ɻ��淶�����������������ġ����ԡ���������츣����ﵸ�����ǽ����������ʽ���Ķ��������赸�ġ����ԡ�������ǡ��ּǡ�˵�����ʸ�֮Ϊ��Ҳ������֮Ҳ��˵���ã�֮����֮����֮����ʳ���֮������֮������֮̾���֮̾����ʲ�֪��֮��֮��֮��֮Ҳ��������ġ����ԡ��������ԡ���֮���Ա��롰���ԡ�������Ϊ����֮���㡱����Ȼ�����Ѳ����Ա�����У��ǵý����������ԣ����ԣ����ɡ�����һ���൱���ϵĹ��ͬʱҲ�����ĵĹ۵㡣Ҳ����˵�������Ŀ�������ν��ѧ����ν�����������϶����˵ġ����ԡ��ı��ֺʹ�������ֱ��ֺʹ������ǽ�����������ǽ�����������ļӹ���װ����ʵ�ֵģ����������һ�֡��ġ��ɡ�������һ����������ʽ�ṹ��
������
���������Ϸ������ǿ��Կ����������������ѧ�ı����ۺͷ�ӳ�ۡ�ʵ���ۺ������ۣ������������������ศ��ɡ����Ƕ�ͳһ����ѧ�ı����ۡ�����ѧ�ı����۳��������ǿ����������������Ĺ�����ѧ���ʵĹ涨��
������һ������ı����ǡ�������������ѧ���ڵ�һ����������ٶ��ǡ���������Ȼ���֣������ѧ�ǡ���֮�ġ�����������֮���ߴ���ǡ���֮�����ܹ������ߣ��˵�֮��Ҳ��������ԭ������
�����ڶ�������������ֱ����ʾ�Լ��������IJ���ͨ��һ�����н������ֳ����ģ���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