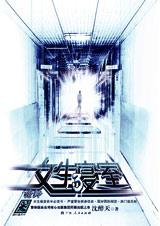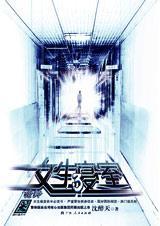男生女生金版故事集锦-第2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我最讨厌的就是孩子,对我而言,他们除了添乱之外别无它用。
当阿吹第一次和我打招呼的时候,我没什么好脸色。
“你好。”那天我出门时,她站在走廊里发呆,见到我后莫名其妙地来了这么一句。
“我很好。”我不想和她有任何纠葛,应付了一声,拔腿便走。
“能救救这只猫吗?”她用央求的口气问。
猫?鳞人公寓里怎么会有猫?
回头看去,我注意到她的眼圈红通通的,显见是刚哭了一场,脸上的泪痕沾染了灰尘,脏乎乎的。衣服比她瘦小的身材大了一号,从老气横秋的款式判断,应该是她母亲用自己的衣服改做的。
一只又脏又瘦的虎斑猫趴在她的脚下奄奄一息,艰难地呼吸着,仿佛随时都会断气。
“它是从哪儿来的?”我阴沉着脸,“这里不许养宠物,你不知道?”
“它是只野猫,在以前的住处,我喂了它一年剩饭。后来我搬到这里,以为再也见不到它了,没想到它跟了过来。”她抽了抽鼻子,“求求你……救救它。”
我在心底里发出冷笑,她大概不知道,除了孩子外,我第二讨厌的就是猫。
“给它喝点肥皂水。”我说。
“管用吗?”她瞪圆黑亮的眼睛,仿佛满怀希翼。
我当然不可能告诉她自己是随口胡说,而且这样很可能把猫害死。我一声不吭地离去,听到她在背后大声道谢。
晚上九点多,我干完了杂活,拖着沉重的脚步回到公寓,正在开门,她溜了出来,脸蛋红彤彤的:“谢谢你!它吐了很多东西出来,没事了!”
我愣住,刹那间不知该如何回答。
她从口袋里掏出一个苹果,塞进我的手里:“我没有别的东西……收下这个吧。”
走进屋子关上门,我感到一股没来由的心烦意乱。端详了一眼苹果,它和那个小丫头一样面黄肌瘦,我冷哼了一声,把它扔进了垃圾桶里。
面部肌肉的抽搐,将我拉回了现实。
杨森静静地注视着我:“你的表情真有意思,忽晴忽阴。”我虚弱地注视着阿吹的遗像,照片上的她笑得很灿烂,和她向我道谢时一样灿烂。我曾
经很疑惑,为什么在阴暗的鳞人公寓里还能笑出来,她的回答很特别:
“除了笑,我还能做什么呢?”
杨森拍了拍我的肩膀:“葬礼结束后跟我走,我给你看看阿吹的日记。”
“……你怎么也叫她阿吹了?”
“我觉得那是个不错的名字。”
四
从杨森的办公室出来后,我径直去了酒馆。
不用我开口吩咐,服务员便心领神会地为我烫了半斤白酒,加上两盘下酒菜。
**这一行最招人讨厌的地方就是,有时得趁别人心灵最脆弱的时候去套他的话。这很正常,剖鱼自然要从柔软的鱼腹下手,没人会蠢到在鱼背上动刀。
我感到自己就像是一条被开膛破腹的鱼,而刀子就是阿吹的日记。
她是这样记录我俩的最初相识的:“对面住着一个阴沉的中年人。母亲和继父好像对他没什么好感,嘱咐我别去招惹他。我不会去招惹他,我从来不主动招惹任何人。但是他救了我的猫,而且当我道谢时,他显得很害羞,看来人果然不可貌相。”
没想到在她的眼里,我的尴尬变成了“害羞”。
我举杯一饮而尽,辛辣的液体让身体重新涌上热气。灰色大衣的身影在我身边晃动,阿吹的继父坐到了我的对面。
“路过时看到你在这里,正好有些事想问你。”他板着脸。
我闷不做声地倒了一杯酒,示意他有话快说。
“阿吹被害的那天,你真的醉得不省人事?”他咄咄逼人地问。
“谁跟你讲的?”我剥开一粒蚕豆放进嘴里,“要是**,就以他们的话为准。”
“我听说你和主管这件案子的**是高中同学,还是多年的朋友。”
“你想说他在袒护我?”我冷笑道,“据我所知,你也没有不在场证明。”
他倏地站起身:“你想污蔑我?我为什么要害她?”
没等他把话说完,我伸手揪住他的大衣,向下一拉,他就毫无悬念地重新坐下了。他挣扎了几下,怒骂的语言刚到舌尖,便被我冷冰冰的声音冻了回去:“听好,我同样没有谋害她的理由。要是你想用男人的方式谈话,我愿意奉陪,否则,你可以自己滚出去,或者我送你滚出去。”
“挫败感让你开始胡思乱想?”我讥讽地说,“平时我并没有看出你有多喜欢她。”
“有些感情用不到挂在嘴上!”他激动地解开衣领的扣子,“我要是对她没感情,也不会把她埋在家族墓地。你一个外人凭什么断言我家里的事?……是不是阿吹对你说了些什么?”
“她什么都没对我说。”我重复了一遍,“什么都没说,尤其是你。”
他霍然起身,这次我没有阻拦,目送他怒气冲冲地走出酒馆。
我说的是真话,阿吹始终没有对我提起有关家庭的话题。她很喜欢,也很擅长绘画,以前我总觉得她长大后肯定会成为一个浪迹天涯的流浪画家。
阿吹送给我一幅画,上边画着她的母亲,继父,以及她自己。阿吹的母亲用手搂着女儿,露出亲切的笑容,阿吹也在微笑,笑容酷似母亲。
女儿长得很像母亲,有时也是一种幸运:跟着再嫁的母亲生活,继父不会因为在她身上看到别的男人的影子,而生出许多不快。但这条规律在阿吹的身上失效了。
站在母女二人身后的那个男人,直眉瞪眼,紧紧地抿着嘴,一副气鼓鼓的模样。这是她送给我的,除了苹果之外的唯一礼物。我本来不想收,可她再三坚持,理由是我
救了她一命。
其实经过并没有那么夸张,那是她的猫得救后三天发生的事。
我拿到了工钱,去饭店慰劳了一下肚子,心满意足地回到公寓的楼下,听见楼旁的胡同里传来谩骂声。
“你盯着我干什么?喂,你别装哑巴。我会掐死你,信不信?”
人在心情舒畅的时候,就容易多管闲事。我走过去拍了一下那家伙的肩膀,他把阿吹按在墙上,直眉瞪眼,污言秽语。在他扭头的瞬间,我的拳头和他的鼻子来了次热切的接触。
他惨叫一声,刷了个仰面朝天,捂着鼻子向我怒目而视。
“你盯着我干什么?喂,你别装哑巴。我会掐死你,信不信?”我恶声恶气地吼道。
他愣住,脸上有种被人重复台词的尴尬和惊慌。大概他察觉到我是个言出必行的人,爬起来后逃得飞快,转眼就没了踪影。
“这家伙好像住在三楼。”我嘟哝道,回头看看阿吹,“你招惹他干吗?”
“我没招惹他。”阿吹说,“他脸色不好,我就多看了他几眼。”
“这里的人脾气都不太好,不喜欢被人注意。”我警告道,“以后别再做傻事。”
“为什么?”她问。
“不为什么!”我没好气地说。
她被我的态度吓到了,过了半晌才嗫嚅道:“……我不会变成那样子的。”
阿吹的日记上记录了这件事,最后加上了一句话:“为什么这个世界上有人不喜欢被人注意呢?”
“是啊,为什么呢?”我自言自语道,“因为……”
我闭上了嘴,即便说下去也没有任何意义:那个喜欢缠着我问为什么的女孩已经死了。
做医生时,我目睹过许许多多的死亡,唯独这一次,它取走一个鲜活生命的同时,在我身边制造出了一个幻影。
夕阳照在对面的椅子上,阿吹歪着脑袋,神色迷惑:“为什么?”
我咧开嘴傻笑,老板走过来,叹了口气:“你喝得太多了。”
五
走出酒馆,我觉得身体前所未有的轻盈。
天和地的界限变得有些模糊,街边的柳树挥舞着光秃秃的枝条在跳舞。我伸直双臂小跑起来,很快变成了狂奔,很快撞在电线杆上。在我回过神后,感到微凉的晶体落在鼻尖上,今年的第二场雪降临了。
几个行人从我身边路过,露出鄙夷厌恶的表情。我早就习以为常,仰天狂笑起来,笑声让他们加快了脚步,似乎怕我会冷不丁扑过去咬住他们的裤脚。
视线划过灰色的楼体,原来我已经跑回了公寓的楼下。我努力寻找着自己的房间,忽然发现黑色的窗口闪动着奇异的光芒,一闪,又一闪。那种古怪的颜色让我联想到了……鬼火。
我揉揉眼睛,这不是幻觉。临走时我关了灯,但没有拉窗帘,这是什么东西在作怪?
酒意一下子消散了,我三步并两步地上了楼,走到门前轻轻一推,门开了。
伸手点亮灯,客厅里并没有人。我小心翼翼地背靠墙横着走了进去,以防被闷棍打晕。确认屋内没有不速之客后,我刚要松口气,却被水族箱内的东西吓了一跳。
我只养了一条鱼,因此里边应该是空的,可现在却多出个黄白相间的玩意,像根烂木头似的浮在上边。
那是一只猫,阿吹养的那只野猫。它大张着嘴,露出尖利的獠牙,神情狞恶。
阿吹死后我再没有见过它。它怎么会跑到我的房间里,难道仅仅是为了追随主人而去?
我给杨森打了个电话,告诉了他这桩怪事。
半个小时后,他大驾光临。
他不顾我的抗议,敞开了所有的窗,不消片刻,呼啸的北风就洗清了屋内残存的温暖。
“总算没有臭味了。”他关上了窗,坐在沙发上,“猫淹死在鱼缸里,和酒鬼醉死在酒馆里一样,都不是什么值得奇怪的事。。”
我打了个喷嚏:“你认为它是穿墙进来的?”
“厨房的窗没关。别解释了,我知道你想说这样可以当冷藏室用。”
“它既然能看到二楼一扇开着的窗,为什么看不到鱼缸里没有鱼?”
“猫的心思人猜不透。”他笑得很诡异,“就像你的心思我猜不透。你没关进水口,好像是在等着它钻进去似的”
“我现在的心思很简单,你在糊弄我。”我讥讽地说。
“我是在糊弄你。”他正色道,“我怕我认真起来,会忍不住骂你个狗血淋头,再揍你个七荤八素。我让你回忆阿吹的往事,进展如何?”
“毫无头绪。”我摊开双手,“无责任猜想的话,公寓里任何人都有犯神经作案的可能。”
“那我再告诉你一件事,希望有助于你的思路。”杨森居然没有发火,“一个小时前,法医递交给我一份报告,阿吹的口腔和食道内有轻微的烫伤……你的脸色怎么这么难看?”
我脸色难看,是因为阿吹曾经在我这里烫伤过一次。
那次帮她解围后,阿吹每次遇见我,都会有意无意地试图和我聊天。我冷漠的态度并没有冻结她的热情,直闹得我头痛不已。
入秋后不久的一天傍晚,我像往常一样,坐在楼前喝茶乘凉。那段日子手头吃紧,没多余的钱喝酒,就只能用热茶来缓解酒瘾。阿吹不知从哪里冒了出来,拎着茶壶就喝了一大口,马上惨叫起来。
“笨蛋!”我吼叫道,“你是渴疯了还是没长脑子?”
后来她告诉我,她不小心吃了根干辣椒,辣得半死,见我在喝茶,慌慌张张之下想要饮水漱口,结果火上浇油。
她的母亲和继父都去上班了。出于人道主义,我硬着头皮把她带回自己的家里,做了些简单的处理。好在烫伤不重,恢复了片刻,她便可以说话了。
我送她回家,安置她躺在床上后,想要离开,却被她死死抓住了衣襟。
“陪我一会儿,好吗?”她用含含糊糊的发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