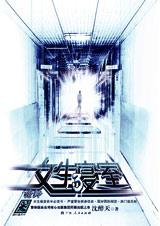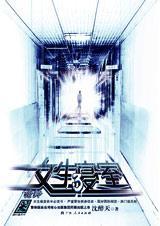男生女生金版故事集锦-第113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一个娴熟的锁匠,趁楼道里无人时,以最快的速度打开门锁,然后换上他带来的锁芯。等待杜依的弟弟进门后,寻机再将锁芯换回去,这并非不可思议。但除去那个神秘的锁芯不谈,那把钥匙为什么会掉在门口?
想到这我不禁苦笑起来,按照这条思路设想下去,就等于认同杜依的观点:她的弟弟消失在异度空间。
我绝对无法相信这种匪夷所思的东西,但是如果想要推翻它,只有一条路:按照杜依所说,造出能用那把钥匙打开的锁。
我来到工作台前,死死地盯着钥匙,它泛着清冷的寒光。这是那个神秘人物留下来的唯一线索,他就像幽灵一样存在于杜依弟弟的失踪前后。没有任何人可以确定他的存在,同样,没有任何人敢于否定他的存在。
“给我时间和耐心。”我取出纸和笔,“除非我主动联系你,否则别来打扰我。”
“你一点没变。”杜依冷冷地说,“还是这么专横跋扈。”
三
如今制锁的厂商越来越狡猾,他们喜欢把钥匙做成比较奇异的模样,以此来让顾客觉得安全性很高。但在专业的锁匠眼中,都是无聊的花招。大部分十字花锁甚至还不如老式挂锁可靠,简单不等于粗陋,复杂不等于精密。
那可以收缩的,乱麻一般的匙齿显然是采用了有记忆效应的镍钛合金,而银白色的匙身很可能是含铬的特种钢,只有这种坚硬的金属才能在中空的情况下,内藏复杂的伸缩机关。
我已经画了几十张草图,涉及到的零件越来越多,多得几乎令我暗暗心惊。钥匙就像人体的骨骼,每一处都有其相应的作用,这已经不是弹子锁能够承受的范围,甚至不是现有的金属材料能够制造出的锁。
一阵尖锐的耳鸣打断了逐渐混乱的思路,我疲惫的合上双眼,用手指轻轻揉着隐隐作痛的太阳穴。每年冬天身体状况都会很差,然而耳鸣却是首次出现,这可是个不好的兆头。医生曾经叮嘱过,如果发生了这种状况,就要尽快去就诊。
可惜我不甘心放下手头的工作。我早已厌倦了整天小心翼翼的活着,与其苟延残喘,倒不如坦然面对死亡。
耳鸣愈发强烈,我去洗手间用冷水浸湿毛巾缠在头上,以往用这种办法来遏制头疼,没想到对耳鸣也有效果。大概是脑部血管开始收缩,我陡然清醒了许多。
这把钥匙绝对不是一把万能钥匙,事实上,万能钥匙根本不具有通常钥匙的形状,它是很多部件的组合体。
由此判断,能够造出这种诡异钥匙的人,特长肯定是制锁而不是开锁。即便如此,普通民居的防盗门对他而言,还是像一张可以轻易捅破的白纸。
我想到了祖父说过的一句话:“制锁就像是出数学题。同样是看上去很难的数学题,出题的思路却可以分成两种。深奥和诡诈。深奥虽然看上去更有技术含量,然而代价是成本更高;诡诈可以控制成本,可稍有偷懒,反倒会弄巧成拙。”
弄巧成拙?……我打了个激灵,难道我被钥匙的复杂表象所欺骗,实际上它的很多部件仅仅是起到迷惑同行的作用?
北风掠过,老旧的双层木窗发出痛苦的呻吟。我下意识地看了眼窗外,隔壁烟囱里冒出来的白烟从缝隙中钻进些许,幻化成一个阴笑的幽灵。
我很清楚,自己面临的是一个没有任何底限的可怕对手。
四
“陪我去你家看看。”第二天一早我给杜依打了电话,“你什么时候能来?”
“今天不行。”她周围的噪音很大,“上午和下午都要考试。”
“晚上也没关系。”
“晚上我要去医院照顾爸爸。”她顿了顿,“要进考场了,我关机了,中午再说。”
我思考片刻,用羽绒服和围脖将自己裹得严严实实,然后出了门。
天气很寒冷,长时间走路的感觉很陌生。上次我乘坐公共汽车还是秋风乍起的时候,一转眼已经过去了三个多月。
杜依的父亲是位**,未曾谋面。她的学校离我家很近,有一次她陪同学来配钥匙,由此结识了我。这是个好奇心很强的姑娘,否则便不会因为感觉我和别的锁匠有些不同,就时常找些借口来陪我聊天。
她率先提出要和我交往,我略作思考,答应了。她了解我的身体状况,知道我是一个随时随地可能咽气的病人,所以我认为这种感情更大程度上是天真的怜悯,而并非喜欢。如果这样能让她感觉良好,我又不排斥和讨厌,为什么不呢?
那的确是一种天真的怜悯。没过多久,她就体会到了我的沉默与冷漠,并且非常不理解。其实这没什么奇怪:终日面临死亡阴影的人,要想不搞得神经崩溃,那是必备的特质。我想要活得久一点,就得学会情绪平稳,处变不惊。
更何况我还是一个必须具有相当逻辑思考能力的制锁人。
杜依的家很快就到了,上一次来还是去年她生日的那天。我把她送到楼下,然后独自离去。当时她邀请我去见她的父亲一面,我拒绝了。没有任何父亲愿意自己的女儿和我这种人交往,比起构筑虚幻的浪漫,我宁可面对冷酷的现实。为了她的情感,为了我的生命。
我走进楼道门,正是上班时间,楼里很安静。来到二楼,我找到了杜依家的房门。这是一道墨绿色的防盗门,无论是油漆还是锁,都很陈旧。
我俯下身观察着门锁,黄铜的金属表面氧化严重,灰蒙蒙的不见光芒。
“你找谁?”警惕的男低音在背后响起。
我回头看去,一个身披草绿色军大衣的中年男人虎视眈眈地盯着我,胳膊上带着治安联防的红袖箍,想必是刚才在楼外注意到我的行踪,跟了上来。
“我是杜依的同学。她今天考试,忘了点东西,叫我来帮她取。”我撒了个很常见的慌。
他没吭声,伸手做了个示意我开门的动作。
我掏出钥匙,缓缓地插进钥匙孔,转动了两圈,锁开了。
中年男人脸上的表情轻松了,解释似地说:“年底小偷比较多,我们得注意点。”
我报以微笑,见他转身下楼,我轻轻地吁了口气。刚才我取出来的是自家的钥匙,凭借羽绒服肥大袖口的掩护,做了些假动作而已。钥匙并没有完全插进去,至于转动的则是藏在钥匙槽中的一根铁丝钩。
既然我可以在别人的眼皮底下不被发现地开锁,那个人自然同样办得到。
我拉开门,天蓝色的擦脚垫跃然入目。走进去关上门,掏出了工具,手脚麻利地取出锁芯,寻思了一下,再装回去。看了看表,前后历时两分半。
这是个足以把风险降到最低的时间,而那个人的动作只会比我更快。看准了时机,做这些事完全不会引人怀疑。
换了锁芯之后,他躲到了哪里?无论是楼梯还是楼外,反复进出都有给别人留下印象的危险。那么,最大的可能就是躲在屋内。但他又是如何把钥匙交到杜依弟弟手中的呢?
客厅和卧室的栏杆都装着粗粗的栏杆,根据铁锈判断已有相当的年头。
我感到胸口一阵刺痛,难道这那个人也消失在了异度空间?
五
回家时,太阳还没有升到天空正中。我站在门前掏钥匙,一只白色的小狗从红砖房的后边跑出,黑豆般的小眼睛闪闪发光,向我汪汪地叫个不停。
我不知道它的主人是哪位,一年多来,它对这里全部的住户表现出了超乎寻常的警惕。我曾经试图用香肠换取安静,不料它却吠得更起劲。
我打开门刚要进屋,小狗猛地冲上来咬住了我的裤脚。那张平时看上去滑稽可笑的小扁脸,居然带着种难以名状的愤怒和恐惧。我清楚地看到它白色的尖牙刺穿了裤子,厌恶和慌乱同时涌上心头,猛地一甩腿,小狗飞到了几米开外,打了个滚,迅速地跑掉了。
我挽起裤子看了下,好在它没有咬穿毛裤,免去了打狂犬疫苗的危险。
出门对我来说的确是个危险的举动。我坐椅子上气喘吁吁,前胸和后背有种割裂般的痛楚,太阳穴涨得厉害,最要命的是,又开始耳鸣了。
耳鸣是比头疼更讨厌的存在,后者还能靠镇痛片压制,但耳鸣却没有特效药。我烦躁不安地把外衣揉成一团扔到床上,勉强坐在工作台前,研究从杜依家卸下来的门锁。
杜依说过,她家里的物件保持着弟弟失踪时的原貌,那么这把锁自然也不例外。
我拿起放大镜观察锁芯:岁月已经磨平了七年前曾被拆卸过得划痕,只有锁孔处凌乱的划痕可以证明它的经历。我踌躇了片刻,决定拆开它。
很快,我看到了它的内部构造:氧化严重的锁簧展现出灰中带绿的颜色,几根线虫似的黑色物体卡在弹子间,那是日积月累的灰尘被钥匙搅拌所成的形状。没有任何特别之处,非常普通而标准的弹子锁。
我用镊子伸进锁壳,费了半天劲,夹出了减震和固定用的橡胶圈。它老化得不成样子,但还是可以依稀分辨出锁芯在上边的菱形压痕。
那家伙为什么偏偏选择了这种古怪形状的锁芯?!
耳鸣声更加强烈,我用手使劲拍打额头,强迫自己冷静下来。
我站起身,在屋里焦躁地来回走动。就在这时,屋门忽然响起了砰砰的闷响,莫非是杜依来了?
走过去随手打开门,一个白色的东西倏地钻了进来,撞倒了衣帽架,一头钻进床下。
是那只小狗!它疯了吗?
我抄起扫帚,小心翼翼地走到床边,伸进里边挥动着。很多零件被我装箱放在床下,拨弄了半天除了带出一大球灰尘外,小狗毫无反应。
万般无奈,我只好用力挪开床,要是这小东西咬坏了重要的东西就糟糕了。
挪了大约半米宽,我看到它蜷缩在两个纸箱的中间一动不动。用扫帚柄捅了捅,它丝毫没有反应。我硬着头皮揪住背上的毛想把它揪出来,它忽然动了,身体一扭,恶狠狠地向我的手上咬去。我的大脑瞬间空白,本能性地把它扔了出去。
不知过了多久,我从半昏迷状态中醒来,发现自己的上半身仰面朝天地躺在床上,双腿拖在地面,手中还抓着一团白色的狗毛。
屋门开着,想必它已经跑了。我走过去关门,看到对面的马路中间停着一辆轿车,几个人站在车前四下张望。
走过去,我得到了答案:小狗在穿越马路时,被轿车压成了两截。
陡然间,我感到血压升高心跳加快:或许这就是答案?!
六
杜依是在次日的傍晚到来的。
对于我自作主张地给她家的房门换了锁芯的事,她并没有表现出气愤。不是因为旧钥匙可以打开新锁芯,没有给带来任何不便,而是因为我告诉她,我制造出了她要的那把锁。
“你的脸色很不好。”她皱眉道,“是不是太累了?”
“别担心我。”我疲惫地说,“一会儿就该轮到你的脸色不好了。”
边说话我边从抽屉里拿出了一个形状诡异的玩意:乍看上去,它就是一个拇指肚大小的铁疙瘩,但菱形的尾部和前段的扁平的缝隙证明了它并非如此单纯。
她的脸色果然变得苍白:“这就是你做出来的东西?”
我点了点头:“相信我,我敢说只有这种形状,才能匹配你带来的钥匙。”
“可……可它不是一把锁啊!”
“这是你家的门锁。”我举起来让她看个仔细,接着拆开它,抽出锁芯,把那个铁疙瘩塞了进去。装配完毕后我来到门前,卸掉门锁,装上了这把改造完毕的锁。
“带有弧度的匙身是个烟幕弹。”我对她解说道,“钥匙的伸缩机关就是为了能顺利的插进任何锁芯,无论原先的锁芯是什么样的都无所谓。世上没有任何锁匠会去制造这种寄生式的锁,所以也就极难有人猜想出它原本的形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