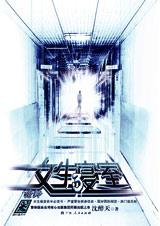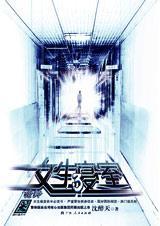男生女生金版故事集锦-第110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我想回家。”傅蝶冷淡地说,“改天再去办出院手续。”
“可以。你的挫伤和脑震荡恢复得很好,没理由继续留你住院。”
钱一夫答应得很痛快,傅蝶忍不住有点诧异地瞟了他一眼。老头儿张开手指梳理被风吹的凌乱的白发:“不要对你父亲的态度抱有成见,我认为他为了怕给你添麻烦才一言不发。”
“这算是安慰吗?”
“不,我在阐述自己的观点。安慰顶多算是个创可贴,说有用也有用,说没用也没用。”
有趣的老头儿,傅蝶想,和他相比父亲依旧那么乏味。一大早报警说发现了倒吊在电线杆上的尸体也就算了,面对**的询问,含含糊糊地做不出明确的答复,任谁也会把他当成可疑的对象。
“要不要我送你回家?”钱一夫问。
傅蝶摇摇头:“不用,我认识路。”
“嗯。身体感觉有什么异常,就给我打电话。”他递给傅蝶一张名片。
在公共汽车上找了个位子坐下后,傅蝶看了看时间,下午三点半。汽车将在一个小时后抵达终点,再步行十五分钟,就到家了。
她不喜欢割喉巷,但是除了那里没有别的地方可以去。
“人生就是由一个又一个谎言交织而成。就像那个老头儿,他明明非常不希望我离开医院,但他找不到限制我自由的借口,于是故作豁然地任我离去……算了,他起码没有像别人那样假惺惺地阻止我,以那里刚发生过凶杀案,回去不安全为理由。”
汽车的引擎轰鸣,在别的乘客眼中,这个女孩的双唇翕动更像是在低声唱歌。她很清楚他们的想法,所以可以坦然地自言自语。
“寂寞到自己和自己说话,多么悲哀啊。”
半年前在教室里和她说这句话女孩长着一双猫眼,嘴角的笑容带着七分讽刺,三分厌恶。傅蝶困惑地看着她,以前曾经在巷子的水泥台上开心玩耍的幼年同伴,即便因为岁月的变迁变得逐渐陌生,用同情的口气加重尖酸的目的仍然难以理解。
“至少这些都是实话。”傅蝶是这样反驳的,“你呢,你听到的话有几句是真实的?”
女孩狠狠地瞪了她一眼,扭头走向不远处目光茫然的三男一女。这五个人此时此刻正躺在停尸间,再也无法对她报以莫名其妙的敌意。
友谊究竟是靠什么维护的?傅蝶不清楚,但是这些昔日的同伴向来惧怕自己的母亲。母亲是个烈性子的女人,不苟言笑,受不了任何刻薄,在小巷的邻居中人缘冷淡。母亲活着的时候,这些同伴和他们的父母退避三舍,死了后,他们若是展现出如释重负的反应倒更自然些,可实际上他们却开始仇视她和父亲。
割喉巷行将拆迁时,邻居们争先恐后地涌入拆迁办公室,与开发商代表讨价还价。最终出台的补偿方案相当苛刻,但他们别无选择似地在上面签字画押。起初傅蝶以为他们急于搬离这条声名不佳的小巷,搬家公司的车队集体到来时,她发觉自己错了。
向生活多年的故居做临别一瞥的目光多少应该带点眷恋,而他们的眼中充满憎恶,这种憎恶赤裸裸地指向他们父女二人。
(为什么在**调查杀害流浪汉的凶手时,他们竭力为父亲开脱?为什么在父亲洗脱罪名后他们反而嫌弃惧怕父亲?)
“下一站,和平大街,下车的乘客请提前做好准备。”
电子报站器的女声平稳而单调,傅蝶忽然打了个哆嗦。那个猫眼女孩的父亲从割喉巷搬走后,在和平大街开了家小饭店,她死去的那五个同学常在那里聚会。
她知道那家饭店的地址,虽然从未打算光临,但她知道。
五分钟后,傅蝶下了车。她沿着和平大街步行了几百米,看到一个悬挂“酒香不怕巷子深”条幅的巷口,走了进去。
巷子很狭窄,而且还是个死胡同。巷口有三个孩子蹦蹦跳跳地玩着跳格子的游戏,旁边两个边晒太阳边择菜的老太婆在絮絮叨叨到的聊天,她侧身躲开一个竭力保持平衡的孩子,一对从三层居民楼门洞里出来的情侣,以及两个心不在焉的环卫女工,总算找到了那家饭店。
夜来香饭庄,俗得不能再俗的名字。她吁了口气,以前割喉巷附近有家同名的酒楼,规模要比这里大上十几倍,这位昔日的邻居当时是那儿的厨师,看来他心中一直渴望自己能当上老板。
贴着花里胡哨玻璃纸的大门紧闭,黑底金字的牌匾布满灰尘,想必要么是生意惨淡,要么是来这里的客人对整洁并不怎么在意。
傅蝶伸出手推门,刚接触到冰冷的铝合金门框,胳膊滞涩在空中。
我来这里做什么?他们认为是我害死了他们的孩子,我来这里做什么?
她眯起眼睛,一周前,在她慌乱地躲避那辆杀气腾腾冲过来的白色面包车时,依稀看到车门上印有夜来香饭店的字样。
她想起父亲告诉她,想要杀害她的人已经被捕了。这家的女儿死了,父亲进了公安局,剩下的应该只有一个很可能处于歇斯底里状态的母亲。
(我怎么会稀里糊涂的来到这里?难道我的大脑真的问题严重?)
“不好意思,我们这里暂停营业。”一个伙计模样的年轻人拎着个菜筐,出现在傅蝶身后,无精打采地对傅蝶说,“请让让。”
傅蝶怔怔地目送他走进饭店,正打算离开,忽然听到饭店里传来声嘶力竭的惨叫。门猛地被推开,那个年轻人面无人色地狂奔而出,把傅蝶撞了个趔趄。
六
办公室宽敞而空荡,家具的颜色非黑即白。傅蝶坐在角落的椅子上,面无表情。
钱一夫脸色铁青地端详着手中的照片:背景是一间杂乱的屋子,不锈钢器皿在日光灯下闪闪发亮,颜色僵硬得犹如死人的面孔。照片正中是一口热气腾腾的大铁锅,一个穿着豆沙色毛衣的人匍匐在锅口,后脑勺凌乱的黑发漂浮在沸水上。
“我们的法医和你的反应差不多。”坐在办公桌对面,年龄和钱一夫相仿的男人说,“真够惨的,喉咙被割开,上半身几乎煮熟了。”
“割喉足以致死,为什么还要把她推到沸水里?”
“看来你直接排除了自杀的可能。”男人托住下巴,“医生的直觉?”
“人类的本能。”钱一夫耸耸肩,“就算极端仇视自己的人,也不会选择这种自 砂 芳 法。”
“她有足够的自杀动机。女儿死了,丈夫涉嫌杀人未遂,面临牢狱之灾。”
钱一夫没有回应这句话,走到傅蝶面前:“你怎么会到哪里去?”
“不知道。”傅蝶目光迷离,“漫无目的,和逛街一样。”
“这里是公安局,思考以后再回答。”钱一夫小声警告她,“当时你告诉我要回家的。”
“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前一秒在想一件事,接下来大脑一片空白,等自己醒悟后,时间过去了很久?”
“每个人都有过,尤其像你这种年纪的孩子。”钱一夫沉思道,“绝大部分情况下,这种情况称为走神。”
“那么极少数情况呢?”
坏点。钱一夫心里默念这两个字,说出口的却是另外的话:“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是不是医生和老师一样,格外喜欢分析别人?”傅蝶望着办公桌后的男人,“你要逮捕我?”
“不,你随时都可以离开。”
傅蝶用一种既像起身又像鞠躬的方式站起来,转身走向办公室的大门。
“我劝你还是回医院,毕竟你家附近刚发生了杀人案。”
傅蝶的嘴角浮现出微笑:“我知道昨晚死的是五个孩子父母中的一个,今天又死了一个,我觉得你应该把注意力放在他们身上。”
“现在这些孩子都在想什么?”发牢骚的声音很响,在走廊上清晰可闻,“明明是为他们考虑,招来要么是麻木不仁,要么是明嘲暗讽!”
你误会了,我只会冷嘲热讽。你误会的原因是没有认真思考我的话。
她走出大楼,决心一定要直接回家。
末班车上的乘客大多昏昏欲睡,她的头脑出奇地清醒,盯着窗外的景色,似曾相识的感觉像一根黑暗中的黑色发丝,无踪无影地掠过她的鼻尖,很痒。
又到了和平大街,她的脸贴到窗上,睁大眼睛。巷口的条幅一掠而过,这里会不会变成第二个割喉巷?那时他们嫌弃的会是谁?她咧开嘴,不无恶意地笑了。
“终点站,铁路文化宫到了。”
电子报站器省略了后面的提示语,终点站到了,谁都得下车。
下车的只有傅蝶一个人。附近的工厂早已下班,回车场边孤零零矗立的文化宫废弃多年。这栋建筑的后边是个驼峰型的黄土堆,它巧妙地挡住了割喉巷的轮廓。爬到顶端,看到那条由两条奄奄一息的红砖楼夹出的小巷,心情会骤然低落,恰好吻合面前的下坡路。
傅蝶走进漆黑的小巷,心脏跳动得很快,但她没有感到任何恐惧。她不讨厌黑暗,只讨厌隐藏于黑暗中的那些物体,譬如墙壁,电线杆,菜窖。
她的母亲死在菜窖里。
那是个阴沉沉的傍晚,雨点细密且寒冷。年幼的她呆呆地站在客厅里,邻居们聚集在后院,发出各式各样的惊叹。
那里有个地下菜窖,一个小时前她兴致勃勃看电视时,母亲去了后院为晚饭做准备,再也没有回来。饥饿促使她去寻找母亲,菜窖的门敞开,她低头看去,母亲仰面朝天地躺在黑色的泥土上,五官扭曲,喉咙处长长的裂口格外醒目。
父亲回来后发出的悲鸣以及邻居们的议论纷纷重新在她的脑海里回响。
(你们凭什么认为是母亲主动招惹了那个流浪汉?你们凭什么?!)
愤怒像是一记重拳,狠狠地将她砸回了现实。她伸出双手不停地摸索,疯狂地寻找家门。
一根木刺扎进了掌心,她找到了那扇门。她笑出了声,笑得泪流满面。
七
钱一夫坐在飞驰的出租车上,此时已是后半夜,车轮碾过覆盖路面的尘土发出的沙沙声清晰可闻。他竭力平静自己的心绪,回味方才和老朋友的对话。
“对于割喉巷的事,你知道多少?”傅蝶离开后,他开门见山地询问。
“你算是问对了人,那儿正是我以前工作过的分局管区。解放前它叫歌后巷,因为那里出了个著名的女歌星。二十年前那里又诞生了一个金嗓子,我在文化宫里听过她的歌声,真是令人心旷神怡的演出。可惜后来她生了一场重病,嗓子毁了。”
“傅蝶的母亲?”
“对。十年前她死的时候我去过现场。喉咙上的伤口看起来像是他杀,但经过法医的检验,实际上是场意外。菜窖里积存的二氧化碳让她头晕目眩,昏倒时被身边木箱上露出的钉子划过她的咽喉,窒息而死,可是……她咽喉的肌肉似乎有点问题,否则区区铁钉根本造成不了那么大的伤口……喂,你的脸色怎么那么难看?”
(那种奇怪的现象很可能是坏点造成的,但是我在十年后才知道了这件事!)
“没什么,你继续说。”
“有些居民向我们反映,很可能是一个流浪汉做的案。我们想找他调查,他似乎听到了风声,逃得无影无踪。后来验尸报告证明此事与他无关,就中止了对他的搜捕。半个月之后,听到这个流浪汉被杀的消息时,我的第一反应,没准是死者丈夫的复仇。他始终不肯接受我们的结论,闹得不可开交,非说我们包庇凶手。”
傅远山的容貌浮现在钱一夫的眼前,老实巴交的人犯起倔脾气就算天塌地陷也难改变,这是亘古不变的真理。
“那是一天半夜,有个下夜班回来的居民看到傅远山躺在小巷正中,电线杆上倒挂着一个人,他吓得半死,赶紧跑回家打电话报了警。傅远山醒来后一口咬定是自己杀了人。他发现流浪汉偷偷地溜回来了,怒火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