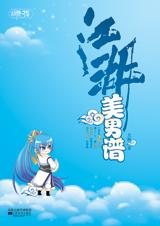美男十二宫-第90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代堂主,既然已经知道了临公子的下落,您是不是要回去了?”
我沉吟了半晌,“‘沧水’兵力动态如何?”
“边境的守军抽调了近一半,全部回京师待命,很可能是要出兵,但是对哪出兵,暂时收不到消息。”她的回答让我的心又是一紧。
华倾风最近都是宿在军营,几乎无暇回府,无形的紧张气氛都在表明这一次‘沧水’的大动作务求一击必中,毁灭性的进攻。
“我不回去。”我轻轻摇了摇头,“‘沧水’动态不明是不是?那我就让它明朗化吧,替我传话给‘云梦’,安排一场上官楚烨回程被刺杀,命在旦夕的事件传出来,传的越大越好。”
“是!”她转身进入内堂,不一会,手上捧着两把钥匙回来,“我们会随时关注您,华倾风往日的习惯稍晚些时候传递给您!”
出了大门,我的脚步也开始轻快无比,许是备份的钥匙已经偷到,许是月栖安然无恙的消息让我终于放下了心头的一块石头,我背着手溜达在街头,欣赏着繁华的景致。
忽然,我的眼前,看到一抹紫色,静静的站在街边,看着小贩飞快的扎着纸鸢,紫色的大眼中闪过酸涩。
小贩拿着糊好的纸鸢,在手中试试,轻飘飘的彩色纸鸢摇摇摆摆的在空中转了转,那紫色的眼眸顺着纸鸢的方向,睫毛眨动中,流露一丝艳羡。
递过几个铜板,他接过纸鸢,唇角,扬起淡淡的笑容,无暇而纯净,明媚清透,看呆了小贩,也看呆了我。
似乎感应到了我的目光,他转向我的方向,眉头一皱,周身的气息顿时散发出排斥和抗拒,所有的纯真都消失,只有那绕在身上的冷然和生人勿近。
我立即缩了缩脑袋,双手刚拱了起来,声音还未出,他已经飘然到我面前,冰凉着语调,“别乱喊。”
他是怕我喊什么爷还是喊什么君?
似乎他对自己是华倾风小爷的身份很排斥,但是对正夫的身份也一样讨厌,那他?
我懂了他的眼色,可未必有其他人懂,这不,一个不识相的女人就远远的冲了过来,“平湖少爷,平湖少爷,我可等着您了。”
镜池的眼眸深处,闪过极度的厌恶,不是针对眼前的人,而是那个称呼,偏偏不识相的人呱呱的一通话,根本不给人制止的机会,“平湖少爷,我上将军府找您几次,都说您要嫁给将军了,先恭喜您啊,以后就是将军的正夫了”
噼里啪啦一通说,我发现,镜池的脸越拉越长,冷的快要结冰了,而她居然毫无察觉。
袖子一摆,他直接绕过她的身体,理也没理的朝前走去,我呆了下,快步的跟了上去。
“平湖少爷,平湖少爷”那女人脚步飞快,气喘吁吁的追了过来,“您上次不是要请笛师吗,我新请了两位,不知道合不合您的意,您要不要听听?”
脚步一停,尽管我能感觉到他从骨子里隐忍着的怒意,却还是轻吸了口气,“去听听。”回头看看一旁傻愣着的我,“黄离,你也来吧。”
上次请我是琴师,这一次是笛师,难道他真的醉心于音乐不可自拔了?
可是又不像啊。
面前两名男子中规中矩的吹奏着,算不上出神入化,却也是中上的水平,声音轻扬婉转,只是镜池的眉头,越来越紧。
“行了!”他不耐的出声,“我哼一段,你们能吹出来吗?”
两人讷讷,紧张的看着镜池的表情。
清亮的嗓音,在喉间逸出,婉转绕梁,低沉时小河呜咽,流水潺潺,忽如雄鹰展翅,一飞冲天,盘旋着,飞翔
雨打芭蕉,风红樱桃,一幅春风画卷慢慢的铺开,秋雨落,残阳斜,余辉撒尽豪迈。
镜池的歌,本来就是一绝,难得如此大气的曲调竟然被他演绎的淋漓尽致,酣畅痛快。
只是两名笛师的脸,越来越难看。
唯独只有我,不在意的转过身,笑了,得意的笑了。
“平湖少爷,这,这”
两人中的一名,艰难的开口,“这曲子”
镜池的神色仿佛早已经知道了这样的结果,“吹不出是吧,那算了。”
另外一人抬起头,“少爷,这曲子根本不是笛曲吧,音韵落差太大,还要一气呵成,纵然是一流笛师也很难办到。”
镜池一声冷哼,“你自己技艺不行就明说,我若是没听人吹过,又怎么会找笛师?”
“啊!”两人一惊,互望着,不吭声。
还是那教坊的老板,看着镜池,半晌,挤着声音,“平湖少爷,这,这曲子气势磅礴,大气雍容,更有华贵之气,不该是坊间人所作,应该出自宫廷,是宫廷乐师的曲子吗?”
一句话,镜池的脸突然变色,紧绷着,突然转身就走,抛下一干人互相望着,不明所以。
“少爷,少爷”我扯着嗓子,提着蹒跚的脚步,憨厚着跟在后面追着,肚子里,早已经笑开了话。
那曲子,就这两个蹩脚的笛师还能吹出来?
这可是要强大的内力支撑,一气呵成,才能从幽咽突然转为高亢,又渐渐回落而不留痕迹。
别问我为什么知道,因为这曲子,是我曾经做的,曲名——南风戏玉池。
为君再吹南风曲
夜晚,我又一次顺利的潜入了华倾风的房间,将那把钥匙原封不动的放了回去,再次纵上府外梧桐树树梢,成功的在鸟笼里看到一只鸽子,取下鸽子脚上竹筒里的字条,仔细的展开,一排蝇头小楷整齐的写着。
“君之命已着手准备,两日必有消息,转临公子口讯,小心安全,色胚,混蛋。”
我苦笑,这还是机密的传讯么?快成打情骂俏的家书了。
翘脚坐在枝头,被冷风吹着脑袋清醒着,我慢慢的分析着各种可能。
既然我不知道‘沧水’会对哪里出手,不如直接将他们的目标引来‘云梦’,上官楚烨生死未卜,阵前就少了最可怕的一员大将,此时不打更待何时?
也许‘沧水’的准备还需要一个月,为了趁火打劫而特意提前开战,一定会有准备不足之处,以有心算无心,到底是谁有心?谁无心?
如果是这样,即使偷不到军事分布图,我至少知道了他们要攻打的对象,这仗还怕会输吗?
同样,更不会有人猜测到,上官楚烨已到‘沧水’境内。
一石四鸟,我为自己这个盘算有些小小的得意。
我无聊的放眼将军府,漆黑的夜晚,一切都安安静静的,有一点风吹草动的迹象,马上就会被我的眼神捕捉到,尤其是人影的晃动,在平静中太过于明显,而我的警惕感偏偏不让我放过。
于是,我的目光定格在最左上角的院落中,在眼光几次闪过后,我确定那清瘦的人影,是镜池。
他漫步在自己的庭院中,仰首看着墙外高高的大树。
离的太远,我看不清楚他脸上的表情,也无从去判断他的心思,只能从衣衫的飘动中判定,他穿的很少。
脚下点着树枝,我象一只夜枭,从这头飞掠到那头,没有一点声息,悄悄的停留在离他最近的一颗树上。
好痛!
为什么所有的树都是梧桐,只有这一颗是百年老松树?松针又细又长,扎的我全身痒中带痛,痛中带痒。
头一转,头发挂住了松枝,手一动,又是一排扎着我的松针。
手疼,腿疼,腰疼,背疼,屁股——也好疼。
好不容易勉强找了个位置,刚坐下,我整个人弹了起来,屁股,屁股
呜呜,两颗松球挂在屁股的位置,这一屁股下去,松球扁了,我的屁股上也多了好多个洞洞,我惨兮兮的一手捂着屁股疯狂的揉着,一边龇牙咧嘴不敢发出半点声响。
耳边,听到了犹如叹息般的哼调,他仰望着无尽的黑色夜空,紫色的衣袍在夜色中看上去仿佛和黑色融为一体,显得那张脸更加的苍白。
我看到,他的手中轻抚着一管玉笛,通体雪白,在那指尖流转着莹透的光,低头见,他的眼中流露出淡淡的忧伤,不知是不是被夜风吹凉了,我依稀觉得那手指有些颤抖。
他轻轻的凑上唇,似乎想要吹响它,只是无论他怎么用力,只能听到几声嘶哑的残破声音勉强从笛孔中挤出。
他无奈的垂下眼皮,长睫毛遮掩了全部的神色,只有那身上透出的落寞还能猜测到一点点心思。
那笛子我认识,当日在游湖时,他雇杀手行刺子衿流波时,我为了救他,直接射出手中的笛子当了暗器,之后根本没想着要收回,如今却在他的手中看到。
镜池啊镜池,既然放不下,为什么要逃离?
他咬着下唇,默默的盯着手中的笛子,捏了捏,拢入袖中。
他的神情,写满了追忆,有喜有忧,有悲有欢,层层叠叠的堆积着,眉头紧锁,拥着轻愁。
我呼吸着,每一下都浅浅的抽着心疼的感觉,吸入的空气里,仿佛也是那薰衣草的味道,扎在心间如一根刺,每一次跳动都触碰着那疼更深入。
手,伸到腰间,我抽出一管玉笛,悄悄的递到唇边,看着那双紫色的忧郁双瞳,幽幽的送出笛声。
一点理智尚存,在声音飘出的瞬间,我凝音成丝,以传音的功法送到他的耳中,柔柔的。
南风吹,玉池水皱。
他爱那曲子,却无人能再为他吹响,上官楚烨既得他心,又毁他爱,为他吹一曲又有何妨?
他猛的一抬头,脸上瞬间露初不可思议的神情,手中的笛子滑落在地他也毫无察觉,手指盖着唇,身体一晃,扶着墙勉强站稳。
他的眼,不住的四下搜寻着,院中,墙头,树梢
我隐藏在最高的枝头,看着他张皇的神情,看着他的失态,心头幽幽的一叹,手指按着笛孔,音乐旋转在他的身边,耳畔,萦绕着。
他看不到我,我却能将他所有的表情尽入眼中,看他不断的摇着头,看他颤抖着的唇,看他眼中惊讶逐渐被恨意取代,看他如梦醒般逐渐冰冷的脸色。
“出来,你在哪,出来!”
突然一声轻喝,他的脸朝着夜空,没有方向的叫嚷着,愠怒的嗓音在寂静的夜空中远扬飘散。
“出来,我知道你在,出来!”
我心头一惊,完全没想到他会如此失态的叫喊,发丝散乱,形若癫狂。
我停下手,声音消散了,可他的动作却没有停歇,“你又想来骗我吗?为什么不正大光明的出来?出来!”
人声逐渐的靠近,慌慌张张的下人敲打着他的门,“平湖少爷,平湖少爷,怎么了,您开门,快开门”
各种嘈杂的声音在门前汇聚成一团,我垂下眼,心头有些不是滋味。
我又自作多情了,又冲动了,这么多局辛苦的布下,却因为他的愁容而让我暴露了身在‘沧水’的可能。
他只要一句话,就有可能将我置之死地,就有可能毁了我的满盘计划。
上官楚烨啊上官楚烨,多少次因为男人而起的教训,你还没吃够吗?
院中的他,用力的呼吸着,深深的吸了几口气后,伸手拉开了院子的门。
“平湖少爷,您,您怎么了?”
“是不是有贼?”
“有没有惊吓到您?”
七嘴八舌中,他有些茫然,疑惑的看着眼前衣衫不整赶来的人群,嗫嚅了下唇,“你,你们有没有听到什么声音?”
“什么声音?”几人面面相觑,同时摇了摇头,“没有啊。”
他不自觉的倒退了两步,颤抖着声音,“笛音,笛子的声音,你们有没有听到?”
几人再次不约而同的摇了摇头,“没有。”
他扶着门,单薄的身子似在寻找什么依靠,“是不是太远了,你们没听见?”
“少爷,不可能啊,我一直在巡视,就在您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