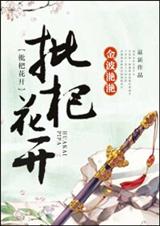石门开-第10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地钻进了他的胸膛。被子弹溅起的泥浪,劈头盖脸地压住了他的身躯。他挣 扎着,手向前伸,仿佛要推开那凶恶的死神,声音窒息在喉咙里,终于,眼
前变成了一片黑暗,痉挛的身子陡然躬起,随即又软瘫在地上,殷红的血慢 慢地浸进泥土。蒋军开始进攻。
耀武扬威的坦克“轰轰”地震颤。 叠成梯形的士兵猥集在坦克后面,一步一趋地朝前拱。钢铁在流动。似
不可抗拒的庞然大物。履带下的一切都被碾得变了形。 于弹飞过去,打在坦克身上,火花迸飞,一阵“滋滋”乱响。坦克毫不
理会,照旧一往无前。 手榴弹飞过去,像一群翻着跟头的黑鸽子,腾起一团团烟雾。坦克轻松
地甩甩脑壳,没事一样。
武器是战争的重要因素。 拿破仑不否认。 希特勒不否认。 斯大林和毛泽东也不否认。
倘若将历史的时针拨回几圈,当著名的西方记者斯特朗在延安枣园发出 “中国共产党最需要的是小米、步枪和盐??”的感叹时,美国墨西哥州的 荒漠上,正聚集起一支以 20 亿美元做后盾的向核高地冲击的劲旅。
不管人们是否承认原子弹的出现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起了促进作用,
广岛、长崎的残酷事实,却使人们充分认识了武器的威力——这凝聚着人类 智慧、又能使人类毁灭的魔鬼。
眼瞅着开在最前面的坦克已抵近战壕,趁坦克跨越壕堑履带松弛的瞬 间,战士王海眼疾手快,将一捆 10 多斤重的炸药,塞进了坦克履带里。
“轰”的一声,神气十足的乌龟壳被炸瘫了。
王海攀上炮塔,打开仓盖,扒拉丁一下那颗低垂在胸前的脑袋,只见耳 道里溢出一股血。敌人被震死了。
后面的坦克见此情景,都不约而同地调转方向。步兵也无心恋战,争先
恐后地挤到坦克前头,寻求坦克的庇护。 机枪手刘志豪看时机到了,索性把重机枪从掩体里扛出来,架在战壕上,
泼泻的子弹如风扫残云。往枪膛里送子弹的小鬼兴奋地低声数着数,数了一
会儿,竟数不清了,阵地前布满了零乱不堪的草黄的色块。
武器是战争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 毛泽东把这颠扑不破的真理阐述得更加完整,更加精辟。就在广岛遭受 袭击的第二天,重庆的一家报纸对此作出评价,认为这是“一次战争艺术的
革命”。 毛泽东不同意这个观点。
几天后,在延安窑洞前的石桌旁,他对来自内布拉斯加的记者安娜·路 易斯·斯特朗发表了那番震惊世界的谈话,“原子弹是美国反动派用来吓人 的一只纸老虎,看样子可怕,实际上并不可怕。”9 年后,在中南海游泳池 边,毛泽东又重新把这番话讲给了来自克里姆林宫的赫鲁晓夫,使这位身材 矮胖的俄国人惊得目瞪口呆。在赫鲁晓夫事后撰写的书中曾这样回忆:
“我试图向他解释,一两枚导弹就能使中国所有的部队化为灰土。毛泽 东只是微微一笑。那笑里藏着只有中国人才有的自信。”
“轰!”
乘胜追击的战士刚刚返回阵地,敌人的炮弹撵着脚跟又砸过来。比上一 次时间更长、更猛烈。
半边天宇都变成了烧红的炉膛。 “敌人搞什么把戏,两次进攻问隔还不到半小时。”郑维山望着硝烟涂
抹的天空,自言自语。 “打钢铁呗,还不是仗着他的美国大鼻子。”胡耀邦在一旁搭话。 “徐水方面情况怎么样?”郑维山问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文年生。文年生
正举着望远镜观察阵地。他也是纵队干部调整时到的 3 纵。他为人忠厚,沉 稳缄言,知识才华含而不露。但有一点与众不同,三伏天,人们躲在树荫底 下,扇着蒲扇还嫌热,他却躺在被阳光晒得滚烫的屋顶上,任凭太阳蒸烤; 到了“腊七腊八,冻掉下巴”的日子。人们都恨不得把炭火揣在怀里,他却 迎着寒风在井台上冲凉水澡,连帮他提水的小鬼都冻得浑身打哆嗦,他却没 事一样。听到邓维山的问话,他放下望远镜:“刚才接到野司电报,2 纵仍 在攻城。”
“敌人肯定是打红眼了,急于突破这道防线,和徐水的守敌会合。部队 还撑得住劲吧?”
“第一梯队伤亡不小,第二梯队还没展开。”
“告诉部队,把正面兵力撤下来一些,加强两翼,敌人冲锋时,两翼部 队多搞点阵前反击。既要注意保存阵地,又要力求杀伤敌人。”
战火仿佛把时间拉长了。 每一分钟都倾泻着钢铁,每一分钟都流淌着鲜血,每一分钟都充满着生
存与死亡、胜利与失败的角逐。
这一天,敌人先后组织了八次进攻。教科书上最规范的陆空步坦协同进 攻搞过;小群多路、无重点渗透性进攻搞过;利用炮火优势、密集型集团式 进攻搞过;人海战术、涌浪式轮番进攻也搞过。惨淡的夕阳终于溅落在地平 线上,那迸射的红光犹如浸漫的鲜血,冒着腾腾的热气,红得令人震撼。尚 未散尽的浓烟在微风中袅袅飘动,好似战神黑色的斗篷,呈现出一种悲壮惨 烈而又神秘莫测的气氛。
被蒋军称为“死亡高墙”的防线,依旧握在晋察冀野战军手中。
困 惑
奔泻的河水,一旦遇到急转弯,常常会出现漩涡。只有冲破这“圆”的 困惑,才能继续向前。
杨得志背对着窗口,目光怔怔地盯着屋角那只正在结网的蜘蛛。他的脑 子里仿佛也有一张网,一张由纷乱思绪结成的网。作战室里电话不断。人们 打电话的呼喊声,走动的脚步声,以及窗外那闷雷般的炮声,他好像全都没 听到。他的思绪也像那奔涌的河水,当河道突然出现转弯时,便不由得陷入 了“圆”的漩涡,“圆”的困惑。
眼前的这场战斗还要不要打下去?如何打下去? 按照围点打援的设计,敌人的援兵确实被引出来了。但一两天内援兵整
整聚集了五个师,却是始料不及的。敌人吸取了以往孤军冒进的教训,仰仗 其制空权和炮火优势,紧紧猥集在一起,齐头并进。切不开,割不断,出现
了本不希望出现的对峙局面。几天来,虽然给敌人以惨重的杀伤,我们自己 的损失也不小。
杨得志走到屋子正中那张方桌前,作战参谋正把前线刚刚报来的情况标 在作战图上。
情况比他想象的还要严峻。狭小的徐(水)、固(城)、容(城)三角 区域,竟集结了双方数万人马,参差交错,进退维谷。
撤出战斗,容易,但并未达到预期效果;继续顶牛,已经顶了四天,还 要顶多少天?那将意味着让战士付出更多的鲜血。
战略决策,有时简单得令人一挥而就,有时又复杂得令人举棋不定。眼 下手里的这颗棋子,究竟落与不落?究竟落在哪里?这种对局势的利弊权 衡,对敌我态势的判断,在军事家的作战活动中,占有特殊的地位。
战争,不仅是双方力量的较量,更是指挥员智慧的较量。杨得志懂得, 轻视对手等于轻视自己。在两军对垒的棋盘上,因为对方失误而使自己得手 的情况并不罕见。但是,他不允许产生这种侥幸心理,这种完全建立在敌人 失误上的胜利,常常是靠不住的。
他的目光在纵横交织的红蓝箭头间巡睃。看来,只有向西挺进,迫敌分 散,诱敌深入,才可能创造出运动中歼敌的战机。在大部队行动之前,能不 能再搞一点出其不备的动作?
“司令员,野司电报!” 郑维山接过来看了一眼,没说话,将抽得已经捏不住的烟屁股狠狠碾在
鞋底子上。
郑维山每逢思考问题时,总喜欢在屋里默默地踱步,总喜欢一根接一根 地抽烟。他虽然身为纵队司令,但他观察问题的眼光却常常逾越纵队的界限, 对整个战斗发展、战役全局,都有着一种内在的洞察力和感知力。根据前几 天交战的情况,他已隐隐感觉到,再这样打下去不行,心里浮荡起一种暗暗 的潜忧,但是,下一步的态势究竟如何发展,眼前又似乎罩着一层雾霜,令 人难以看透。“上级有什么指示?”胡耀邦靠过来。
“你自己看!”
“什么,让我们打涞水?为什么要打涞水?”胡耀邦抑制不住地喊出声 来。
涞水位于啄县与固城之间,一旦打响,难免不受腹背夹击。况且,从部
队目前的集结地到涞水,要经过敌人的防区,孤军深入,在军事上也属大忌。 再退一步,部队经过几天窿战,各方面损耗已经不小,再打滦水,能下能攻 得下?既便攻下,要付出多少代价?郑维山、胡耀邦、文年生,三个人相互 交换了一下眼色,下级服从上级,这是每个军人最起码的常识,特别是在战 场上,更容不得任何人去讲价钱,讲条件。可是??
郑维山挠了挠理得短短的板刷头,“我们是不是给野司回个电报,谈谈 看法。”
“你就不怕人家说你抗旨不遵?”文年生半开玩笑半认真地把电报在手 里抖了抖。
郑维山沉默了。凭心而论,他对野司几位领导是信赖和尊重的。野司组 建不久,第一仗就打得不顺,应该维护他们的威信。可是,一个合格的下级 指挥员,并不仅仅是首长的传声筒,而应当成为首长的耳目、大脑和神经。
“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古人早有明训。何况我们可以把理由向野司 首长陈述清楚,征得野司同意,再决定下一步行动。”胡耀邦快人快语。
“这么说,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了。”文年生指指郑维山、胡 耀邦,又指指自己。
“政委,你耍笔杆子出身,能者多劳,电文还是你来起草。”胡耀邦也 不推辞,“刷刷”几笔,一份电文跃然纸上。
野司: 来电收悉。关于打涞水,我们认为目前条件不大成熟,我们意见就地坚持,争取情况
转机。
胡耀邦把电报交给郑维山。郑维山看了看,递给文年生。“措辞是不是 太生硬了?”文年生不无顾虑地看了胡耀邦一眼。“我们主要是讲情况,措 辞怎么样,野司首长不会介意的。”“既然这样,我没意见,不过,丑话说 在前头,如果挨板子,咱们谁也跑不了。”郑维山往电报稿上拍了一巴掌。
第 5 章 罗历戎北上
灾祸与幸福,像没有预料到的客人那样来来去去。幸运本身就是一
种
骗人的伪装。
安乐椅轻轻地摇动着。
狗咬狗一嘴毛
罗历戎双臂十分舒适地搭在紫檀木扶手上。 迷离的目光随着椅子摇摆的幅度,在空中划着一个又一个弧状曲线。 他在想心事。 自从北平军事会议老头子应允了他率军北上的请求,心里好一阵窃喜。
但他不是那种喜形于色的人,脸上故意装出一副为党国事业万死不辞的庄重 和深沉。
谨慎小心的孙连仲对此举却始终放心不下。罗历戎离开北平前,孙连仲 特地把他叫到自己的房间。
“老弟孤军北上,勇气堪嘉,只是??”孙连仲顿了一下,见罗历戎没 有什么反应,故作关心地把头凑过去,“届时,要不要让刘化南部从保定向 南扫荡一下,策应你们,以防有失。”
罗历戎淡淡一笑:“孙司令长官过虑了。且不说保定以南无共军主力,
不可能遭到大的截击,即便遇到情况,鄙人所率五个团的兵力,也完全有把 握将其击退,勿需派兵保障。”
孙连仲看着罗历戎那目空一切的神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