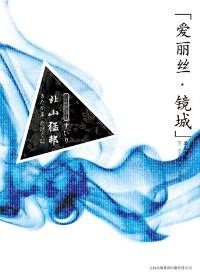雾越邸杀人事件-第32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要论“憎恨”,最恨兰的应该不是名望奈志而是彩夏吧(前天在温室时,她说过那么尖酸刻薄的话,眼中还冒出暗红色的火舌。昨天的“审问会”上,她反驳兰的语气也充满了憎恨!)如果她现在天真烂漫的表情、语气、台词,全都是在她的盘算下装出来的呢?
“的场很可疑。”彩夏根本不管我在想什么,突然这么说。
“为什么?”
“昨天开始,她突然变得很亲切,吃饭时一定会为我们服务,但在那之前简直是超级冷淡,现在这样子,八成是在监视我们——啊,这个耶稣好帅啊。”
她抬头看着十字架上的耶稣,突然很兴奋地提高了声调。
我看着她的侧面问“怎么说呢”,催她继续说下去。
刚才我也怀疑过的场,但是,我这么做并不是因为还眷恋那个已经被我否定掉的假设,而是被她这么一说,我也觉得的场昨天以来的态度软化大有文章。
“嗯——我觉得说不定跟四年前的火灾有关。”彩夏用一成不变的语气说,“她说不是纵火,可是说不定就是纵火,那么,凶手就是没有被抓到,而那个凶手说不定就在这里。”这倒是一种新的说法。“四年前的火灾”这几个字,又强烈触动了我心中的疙瘩,但我还是应了一声“原来如此”,继续跟她搭腔。
“你是说榊可能是纵火的凶手,白须贺家的人知道了就杀他复仇?”
彩夏猛然大叫一声“不是啦”,声音响彻整个礼拜堂。
“我说的不是这样啦,我是说,”她指着自己的太阳穴,“他们之中可能有一个‘这里’不太对劲的人把以前的那个房子烧了,现在又一副没事的样子在这里工作。可能是的场,也可能是鸣濑或井关。我们来了之后,可能这个人的病又突然发作了。”
“突然发作,杀了榊?”
“嗯,”彩夏很认真地点着头,“也有可能是那个留胡子的末永,的场不是说他老婆自杀了吗?可能是因为这个打击,‘这里’出了问题。”
“突然发作?”
“没错,榊跟兰都是特别醒目的人,他很可能从最醒目的人下手。”
我无法判断她说这些话究竟有几分是认真的,把视线从她脸色移开,若无其事地转向右前方的彩色玻璃图案。
“关于火灾的事,”我说,“不管是不是放火,你不觉得有什么疙瘩吗?”
“咦?”彩夏不解地问,“什么疙瘩?”
“事情发生在四年前,原因是显像管在深夜起火燃烧,这当然是厂商的责任。”说到这里,我突然了解到我的“疙瘩”是什么了——我想起来了。
“原来如此!”我不由得大叫一声。
彩夏满脸不解地看着我说:“到底怎么了啊,铃藤?”
“你大概不记得了,四年前你还只是个初中或高中生。”我面向彩夏说:“当时相继发生了好几件大型电视机起火的意外事故。造成很大的问题;有几件意外还演变成大火灾。”
“我不记得了,不过,听你这么说,好像有点印象。”
“那些有问题的大型电视机,都是同一个厂商生产的,也就是李家产业。”
彩夏马上领悟到我话中的含意,“啊”地张大了嘴巴。
榊由高——李家充是李家产业社长的儿子:
对在火灾中失去妻子的白须贺而言,是让他恨之入骨的“凶手”的共犯。
不管火灾后的赔偿、刑事责任等如何处理,当白须贺知道偶然进入自己家里的榊的身份时,很难说他不会萌生为妻子复仇的念头。
在火灾中失去丈夫的井关悦子,也有同样的动机。
的场小姐也脱不了干系,因为她好像非常仰慕已故的夫人。
问题是——我慎重地往前思考。
刚才在“的场=凶手”的假设中,我也曾经碰过相同的问题。
那就是他们如何在事前得知,来访的客人当中有这么一个人?
不,还是有可能知道。
撇开榊由高这个艺名不谈,在我们到达的第一个晚上,他们就在电视新闻报导8月那个案子时,知道了李家充这个名字。
的场说第一次看到榊被列为案件嫌犯遭到通缉的电视报导,是在15日晚上。
如果当时电视登出了他的本名跟照片(第二天的新闻报导也行),那么,鸣濑、的场或井关悦子就会注意到那个男人就在访客之中……
“难道凶手真的是这个家里的人吗?”彩夏突然东张西望了一下,压低声音说,“不过,如果动机真如你刚才所说的,那么,我跟你应该都不会有事吧?因为凶手没有理由恨我们啊。”
“可是也没有理由杀了希美崎啊。”
“因为她是榊的女朋友啊。”
她好像说给自己听似的喃喃自语,两手抵在椅子上,开始晃起脚来。
就这样沉默了一会,又突然用很开朗的语气说:
“下次的公演要演什么?”
“还不知道。”
“那天晚上你不是跟枪中讨论过吗?”
“嗯,可是那时候还没发生这些事。”
“因为你们是以榊为主角策划的?”
“没错。”
“别人就不行吗?”
“我无法发表意见。”
“总不会因为死了两个人,剧团就瓦解了吧?”
“这就要看枪中了。”
“那就不必担心了,枪中很有钱。”彩夏安心地放松脸颊,说,“兰已经死了,不知道我会不会拿到比较好的角色。”
她说这种话时,口气一点都不带刺,一幅天真无邪的模样。
看我都不回话,她啪啦站起身来,说:“我要上去了。”
说完,走出礼拜堂。
走到门前时,她临时想到什么似的,对坐在椅子上目送她的我说:
“深月的事,你还是很有希望,因为她看着你的眼光非常温柔。”
10
下午快2点时——彩夏离开好一阵子后——我也离开了礼拜堂。
我关上门,从中间夹层回廊下面走到一楼大厅时,惊讶地停下了脚步。
因为芦野深月正独自站在壁炉前,跟那幅肖像画面对面互望着。
听到我的脚步声,她转过头来,惊讶地“啊”了一声。
我瞥了一眼礼拜堂,表示我是从那里出来的。
“你很在意这幅画吗?”
我边说边走向她。
深月没有回答我,只是微微点了点头。
“一个人待在这里不好吧,很危险呢。”
这回她对我摇了摇头,不知道是代表什么意思。
然后,又继续抬头看着墙壁上的肖像画。
她今天的打扮也是黑色长裙、黑色毛衣,站在肖像画面前,让镶在金边框里的画,看起来像一面大镜子,而不是画。
“她是多少岁时过世的呢?”
深月的声音充满了感叹,可能是因为长得太像了,实在无法不感同身受吧。
“‘死’真的是一种很悲哀的事,尤其是深信自己还有无限未来的人突然死了。”
她喃喃述说的声音实在太悲戚了,我不忍再听下去,更进一步靠近她,拼命找话题想跟她说,于是,我想起了那件事——
“芦野,”
我想到昨天黎明时,在图书室听枪中说的事,还有,那之后在梦中见到的玻璃墙另一面的脸庞。
“我想问你一件事。”
听到我一本正经的语调,深月浮现出有点疑惑的笑容,拢拢乌黑的长发。
“今天早上的场说过‘对未来失去兴趣’这么一句话,昨天,枪中也对我说过类似的话。”
“枪中?他说了什么?”
“他说,”我决定说出来,“他说你舍弃了未来。”
“咦?”抚弄着长发的她,骤然呈静止状态,疑惑转变成惊讶。
“他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他说你舍弃了未来,所以才会这么美。我不懂他这句话的意思,他说最好不要知道;最好是充满了神秘感,可是,我……”
无法克制的冲动,让我说出一长串的话,可是,看到深月的反应,我突然说不下去了。
她避开我的视线,默默一次又一次地摇着头。
“我是不是不该问?”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唯唯诺诺地任视线在黑花岗岩地板上游移。“那是我不该知道的事吗?”
冗长的沉默,笼罩着宽敞的挑高大厅。
跟她相距两米、面对面站着的我。
像断了发条的小丑娃娃般伫立着:
既无法更接近她,也无法再开口说什么。
同样无言伫立着的深月,仿佛就要被吸入后面的肖像画里消失了。
如果真发生这种事的话,我一定会就这样一辈子站在这里。
“我——”
听到深月的声音,我立刻严阵以待。
“我活不长了,所以……”
我一时无法了解她这句话的意思,不,是我大约已经猜到会是这种答案的大脑,拒绝去了解这句话的意思。
接着,又是一阵沉默,片刻,深深的叹息飘落在紧绷的空气中。
“这是什么意思?”我好不容易才挤出话来,“我实在不懂……”
“我跟一般人不一样,”她平静地说着,把右手轻轻贴在胸前,“心脏不一样。”
“心脏?怎么了……”
“我的心脏先天就很虚弱,应该算是某种先天畸形吧,在此我也不便详细解说。从小,我只要做一点剧烈的运动就会很痛苦,甚至昏倒。中学时,因为症状太严重,就去看专科医生,才知道是心脏方面的疾病。”
她细长的眼睛看着我的脚下,淡淡说着——没有一点自艾自怜的感觉。
“医生告诉我父亲,我很难活过30岁。父亲烦恼了很久,才决定告诉我这件事。”
“不,”我发出呻吟般的声音,“怎么会这样。”
“我刚听到这件事时,非常震惊,不停地哭,也变得很绝望。可是,奇怪的是,过一年后就一点都不觉得怎么样了。不过,既不是自暴自弃,也不是对人生绝望。该怎么说呢?”
枪中的话在我心中一一浮现。
——她现在的心态是平静的“谛”观。
——对,她舍弃了一切,但不是绝望或老年人的了悟。
“总之,我觉得心情很平静,连我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她说。
——她舍弃了没有希望的将来,平静地过着现在的生活。
“枪中本来就知道这件事吗?”
“嗯,很久以前就知道了。”
“他明知道,还让你站在舞台上吗?你这样的身体,怎么可以演戏……”
“他也说不好,可是,我喜欢演戏。”
“即使会缩短你的生命吗?”
“是的。”
——简直就像个奇迹,所以她才会……
枪中是说,因为这样,她才如此美丽吧?
我没有比这一刻更憎恨这个十年的朋友,他明知我对深月的感情,却从来没有对我提过这件事。
不,我不该这样指责他,没有当事人的同意,他也不能随便把这个秘密说出来——对,一定是因为这样。
可是,作为一个喜欢她的人,枪中为什么不把她的心引导到另一个方向?
为什么认同她的“舍弃”,还用那些话来赞美她?
或许,这就是枪中对美的诠释吧,可是——不是有生命才美吗?
“还可以动手术或想其他办法呀,怎么可以现在就放弃了。”
“好像需要移植,可是,我的血型比较特殊,很难找到合适的心脏。即使找到了,成功率也很小。”
“可是……”
“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