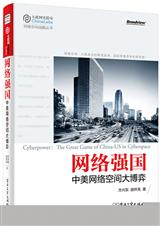网络与现实之门-第37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业敏感性太强了,我竟然一点都没察觉到比赛的时候就在自己眼皮底下发生了这些事情,我只知道当场上出现技术故障的时候,姜昆在做自己额外的工作——救场、维持正常的比赛气氛。
再接下去,所有的焦点开始集中在我身上,
“不公平。题目的难易程度相差太大,比赛规则又没办法实施,这样选出来的网姐能令人信服吗?”
“无意中又听到了一则新闻。记者的一位在外地电视台工作的老同学,跟踪拍摄某位网姐一月有余,当我们众口一词表示对这位网姐的好感时,她语出惊人:”别看她在台上很有分寸,可在台下,刻薄得不得了。那天,好几家媒体一起采访她,都下午两点多了,她只邀请中央一家媒体的记者去她家吃饭。这次来上海,我们没舍得住那么贵的国际饭店,你知道她说什么?她说‘你看人家(指那家中央级媒体),早上来看我一次,晚上来看我一次,你们呢?’“”对啊!“另一家上海媒体的记者”补充控诉“:”那天安排专访时,一位记者就因为说错了一句话,她吵着闹着要和人家打官司……“
“你看评委多偏爱浙江的陈帆红,每次都是她的分数最高。”
我很幸运地成了整篇报道的中心人物,尽管有些描述是虚构的情节和对白,这位记者可能是怕“打官司”,没敢把我的名字和事情对上号,我还是根据蛛丝马迹认出了自己。而最终帮助我看懂这篇报道的却是很多人羞于出口的一些原因:
“残疾也是优势嘛,惹人同情。”
“冠亚军决赛在浙江的陈帆红和黑龙江的柳菁之间展开,柳菁的那段演讲机智、自信、条理清晰,但陈帆红的发言有些牵强。对陈帆红的偏爱会影响最终的结果吗?有记者说,不会吧。听说,‘爱立信’要请最后获胜的网络小姐做形象大使的。”
在一次又一次的提醒下,我不得不再次面对残疾这两个字,我也不得不重新去思索在普通人的心里,“残疾”到底是什么含义。残——不完美的,疾——不健康的,合起来就是——惹人同情的弱者。我不在乎“残疾”这种称呼,但是我不愿意接受“残疾”背后隐藏着的深层意思。有的人就是不愿意面对现实,不愿意承认,一个在他们眼中比谁都弱、比谁都差、只应该让人同情的女性,战胜了所有在他们看来是健康的、美丽的女性,最后获得了“中国网络小姐”的称号。更让他们难以接受的是,就是这样的一个“残疾”的形象,将作为中国女性网民的形象,这个结果让他们觉得难堪、被侮辱了。我不知道评委是否一直都偏爱着我,如果说每轮分数的领先只说明了“评委的偏爱”的话,那未免把评委和其他的选手看得太低了。我只是很清楚地知道自己为了获得和人平等地站在一个舞台上,平等地参加一个比赛,付出了多少代价,我从来都没有奢望过有谁会对我偏爱,当我坐着轮椅在台上向着全场观众绽放出自信的笑容时,我心中想到的却是究竟有多少人能看懂我的笑容,有多少人能够看到一个站着、自由行走的我,又有多少人能够理解到网络对人的意义。
我一直在分析着与这位记者类似的人的心理,想要知道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种被扭曲的心态。直到看到了互联网周刊上刊登出的一篇文章——中国著名新经济学者姜奇平写的“陈帆红,二十世纪最后的童话”的时候,我才明白这其中的缘由。社会是由不同层次的人构成的,每个人都能在社会中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位置,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存方式。当一个人想要描述另外一个人的时候,有三种方式——仰视、俯视、平视,要想描述得准确又贴切的话,只有采用一种方式——平视,否则描述者就无法了解被描述者的真实心理,更不用说从被描述者身上获得什么有价值的观点。
不一样的人生
赛后,大赛组委会给了我充分的自由,让自己选择可以推动网络发展的公益活动,我完全可以自己决定是否要去参加一些公益或非公益的活动。也许是关于比赛的种种报道,使人们误以为只要是公益活动,我就必须得参加,为此,我很被动,很多时候连选择的余地都没有,仿佛自己变成了一个公益性人物。我很愿意做公益活动,但是我也有自己的生活、工作,我也要生存,我不可能整日忙于东奔西走地参加公益活动,却拿着病假工资不去单位上班,我也不可能分文不取地到处义务服务,最后却不得不为自己今后的手术费、生活费发愁。也许年少的我很浪漫,做着各种梦,但我的经历使我不得不成为一个现实的人,也只有我知道自己将面对什么,自己要面对什么。很多人觉得我出名了,和我的爷爷陈歌辛,和我的伯父陈钢一样,出名了,但是,又有几个人知道,我每天在做些什么,我在过着一种什么样的生活。
我曾经天真地以为公众人物只是一个阶段的事,却没有料到,一旦成为公众人物后,就得安于这个位置,想要再回到过去,是不可能的了,很多事情不可逆转,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尽快适应自己新的生活方式。
为了不让所有有着善良愿望的人们失望,我很累,我每天要回几百封的信,要面对众多的媒体,要接待各种来表达善良愿望的人,我还要做自己的事情——维护菜青虫之家这个快乐的源泉、学习新的知识、创建网上医院……所有的这一切,都只有我一个人在做,没有人帮我,有时候我自己都很佩服自己,一个人能做这么多的事。同时,我也在想一些问题,如果我仅仅是付出,没有任何的回报,那么我很难真正地融入这个社会,如果我永远过着传统的生活,无法将自己所拥有的知识转化成经济的话,那就说明我还不适应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
在这样一种生活中,我努力地寻找着快乐,哪怕只有一点点,我也很满足。忙碌的生活中总有些新鲜的感觉时不时地刺激着自己,世纪末的时候,中国青年政治学院邀请我去与学生谈网络与人生,这是我赛后第一次到高校与学生交流,尽管后来我还去了其它的高校,但在我的记忆中,这次是气氛最好的一次。整个过程中,阶梯教室中的笑声不断,我也终于从前一个阶段的严肃中走了出来,轻松地面对人群,用真实的思想和大家交流。我坐在讲台上,面对着台下几百位大学生,回答了大学生们的所有问题后,我也向他们提了一个问题:“你们认为中国网络小姐应该是什么样的?”有的说应该是电脑及网络高手,有的说应该是无所不知的百科全书,有的说应该是智慧与美丽共存的女性,有的说应该是有亲和力的女性,有一个学生特别有意思:“中国网络小姐应该是很漂亮的!”我笑着问他:“你觉得我怎么样呢?”他不好意思地说:“离得远,我看不清……”我请他走上前来看,他的脸立刻红透了,支支吾吾不肯上前来看个清楚。我觉得这样的交流很有意思,也非常喜欢这种形式。显然,大学生们也很喜欢这种轻松的形式,不断会有学生走进教室,没有座位了,就站在教室后面看,后来我才知道,在对面的一个教室里有位教授在作报告,有很多学生是从那个教室“转移”到我这个教室来的。看到这么多年轻的面孔,泛着青春的光彩,我想起了自己的大学生活,一切仿佛都离得很遥远。在北回归线的银色月光下,王以培的一首诗涌上了我的心头:
这一夜所有的音乐从梦中传来
这一夜所有的树木纷纷落叶
这一夜所有的村庄都在下雪
这一夜所有的老人回忆从前
这一夜所有的眼睛注视着窗外
这一夜所有的泪水向我涌来
所有的感觉都凝结在北京冬天的夜色中,所有的酸甜苦辣都烟消云散了,轻松过后,我还是无法改变现实,更无法逃避。网络改变了我的生活,也改变了我的人生。
新世纪的第一天晚上,我参加了面向全球直播的中央电视台制作的“世纪风”元旦晚会。大赛组委会认为,参加这种影响面广的大型活动也是一种公益活动,我的形象、我的经历将和“网络”这两个字一起通过电视传播,间接地推动着网络的发展。我和表演艺术家奚美娟作为“生命”这一主题的嘉宾主持人,用我们自己的语言向观众传达着我们所感悟到的生命,奚美娟没有任何异议地推着我的轮椅,她的神情平和安宁,打消了我所有的疑虑。也许是在此之前遭遇了太多的冷漠,奚美娟简单的行动,简单的眼神,却让我感到了无限暖意。人与人之间的交融,胜过言语,胜过春天。
镁光灯下的生活
当我终于能够坐在自己家里的电脑前重新更新自己主页的时候,却再也无法像以前一样心无旁鹜了。电话铃时不时地响起来,要求采访我的,邀请我参加各种活动的,要求我提供帮助的,最初我都欣然接受,过了一段时间,发现同类的事情越来越多,我几乎无法掌握自己的时间,而自己越是轻易地答应,对方越是不珍惜我的劳动和付出。我不得不停下手头在做的一切,开始思考究竟该怎么去面对这些以前根本不会遇到的情况。
采访我的媒体来自全国各地——从中央级的媒体到地方媒体,同时也有很多国外的媒体——英国路透社、日本NHK、日本朝日新闻、美国之音、美国芝加哥论坛报、澳大利亚ABC、美国新闻周刊,转载、刊登有关我的媒体范围更广——从国内一些中学的内部校刊到法国、德国、匈牙利、英国、南非、澳大利亚、新西兰、马来西亚、新加坡的媒体、亚洲周刊……我对每个来采访的媒体都很友好,没有任何要求,只有一个简单的要求,希望采访过我的媒体能够给我一份有关我自己的采访节目的拷贝,每个媒体向我要求采访的时候都表示这是件应该做的事情,并且信誓旦旦地保证一定会做到,而最后真正能够做到的却没几家,大部分都是雁过不留痕。我不能随便拒绝任何一家媒体,因为即使没有采访过我,有些不负责任的记者一样可以东拼西凑地写出关于我的长篇报道,其内容的真实性必然是大打折扣。我开始有选择地接受采访,尽管这些采访占用了我大量的休息时间、工作时间,我还是很友善地对待每个来采访的媒体,还是那一点小小的要求。我一厢情愿地认为,只要自己真诚地对待别人,别人也一定会真诚地对待我。
可是,无数事实证明我错了,来采访的媒体还是一如既往,要采访我的时候爽快地许诺,采访结束后便轻易地忘了许诺过的事情。有少数的一些媒体,也许是因为太容易便采访到了我,一点也不珍惜我的时间和劳动,直到来我家采访的时候,还不知道自己究竟要采访些什么,更有甚者,占用了我大量的时间,最后却轻描淡写地一句“节目不满意,不播出了。”也许在很多人的眼里,我仍然只是一个残疾人,给我一个上镜头上报纸的机会就已经是给了我天大的面子,我怎么还有资格去要求更多呢?
我一直充当着这么一种被施予者的角色,经常会收到一些网友来信问:“你现在经常接受采访,是不是都收费的?”我无言以对,如果真的每个采访都是付费的,我想采访者也会比较珍惜被采访者的劳动一些,也会更尊重被采访者一些。我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