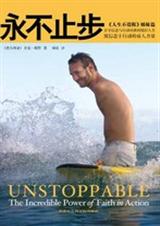永不瞑目-第35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庆春固执地说:“对他不合适。”
李春强笑了,有点搞不懂地说:“你立场出问题了吧?”
庆春沉闷不答。
李春强想找点幽默来挑起她的情绪,胡乱说道:“你是不是和他接触长了,有感情了,真把他当成你弟弟啦?”
庆春不但没笑,反而被此话激怒,一推门走出屋子。李春强在后边几乎来不及解释:“咳,我开玩笑!”
但是李春强还是认为这个机会绝不能错过,他决定下午亲自去一趟分局的拘留所找一下肖童,趁热打铁,迫其就范。他既然犯了事,肯定也需要得到一个将功折罪的机会。
下午临走的时候,他犹豫了一下,还是征求了庆春的意见,问她愿不愿意同去。
庆春想了一下,居然答应了。
他们一同到了分局,先找分局的同志问了问“帝都”夜总会伤害案的大致案情。
然后就叫分局的同志领着,到后面的看守所来了。
看守所分为前后两个套院。前院是分局预审科办公的地方,后院是看守所的监房。前后院间隔了一排预审室,围墙电网、警卫塔楼,一应俱全。地方虽然不大,布局却正规。
李春强和欧庆春进到后院,在一个四面用房子围起来的口字形的天井里,预审科的民警正在给新进来的嫌疑犯拍档案照片。
因此让他们稍等一等。相机支在三角架上,每次从房子里叫出一个“嫌疑犯”让他们双手把写有自己名字的纸牌端在胸前,正面一张,侧面两张,照完后再换下一个人。拍的速度倒是挺快。李春强和庆春没等一会儿便轮到了肖童。他从屋子里被带出来时面容呆板,无精打采如行尸走内一样。忽见李春强和欧庆春在侧,眼睛便直了,死死地盯住欧庆春不动。欧庆春冲他笑了一下,他激动得全身发抖。预审干部把一张纸牌给他叫他端在胸前,上面白纸黑字笔画难看地写着肖童二字。他动作机械地端着自己的名字,看着庆春,脸上的肌肉僵着,目光里什么都有。拍照的预审干部喝令:“看镜头!”他像没听见一样,仍对着庆春毫无遮掩地逼视。预审干部喝道:“嘿,看什么哪你,眼睛规矩点好不好,这是什么地方,嘿?看这边!”肖童把头正了。咋喳一张照完,又照左右两个侧相。全照完了,又让他在一张专门的纸上留了指纹和掌印,然后押他回屋。他没有再看庆春,低头进去了。
预审干部对李春强和庆春笑笑,摇头无奈地说:“这种人,你算没辙,这才刚刚进来没几个小时,见来个女的眼就直了。这要是关的时间长了,咳,那就不知道怎么着了。这些人关键是一点廉耻心也没有,跟个动物差不多了……”
李春强随声笑了笑,庆春低头不语。他们被预审干部领进了一间预审室。不多时,肖童被带来了,手上还带着铐子,庆春对预审干部说:“铐子摘了吧。”李春强也说:“摘了吧,没事。”
铐子摘了,预审民警让肖童在一只方凳上坐好,便出去了。
李春强点上根烟,故意做出很随便的样子,问肖童:“抽吗,来一支?”
肖童说不抽。
李春强笑着问:“怎么回事,好好的怎么折这儿来了。”
肖童歪着头不说话。
李春强说:“就为一个女的,值得吗。你一个大学生,本来前途无量。这下好了,故意伤害,你知道刑法规定犯故意伤害罪要判多少年吗?”
肖童一动不动,眼睛不看他。
李春强对肖童的态度有些反感,但还是忍耐着,说:“你说不想给公安局干了,是不是?这下不是还得跟公安局打交道吗。
这下想通了没有?想通了我们可以给你个将功赎罪的机会,啊!“
肖童梗着脖子看了李春强一眼,开口说:“我没犯罪!”
“你没犯罪,没犯罪你到这儿干吗来了?”李春强把嗓门放粗。“是参观学习呀还是你们法律系组织你在这儿体验生活呀?
没犯罪你把人家脑袋打开花了,人家缝了多少针有没有后遗症你知道吗?我还是奉劝你嘴别那么硬了,到了这儿只有一条路,认罪服法,配合政府,将功补过,这是唯一的路!“
肖童同样声气不让地说:“只有法院才能判我有罪,你没有权利说我有罪!”
李春强倒给他说得哑了一下,他忽略了这小子是学法律的,所以在谈话的用词上让他抓了漏洞。他吸着气说:“哟,那是我们抓错你了,你来这儿是冤假错案,是吗!”
肖童倒显得十分理直气壮:“我打的是一个流氓,他玩弄妇女,我是见义勇为!”
“你见义勇为?我真是长了见识了。你喝得醉熏熏地跑到夜总会去见义勇为?可惜的是目前还没有一个证人跳出来证明你是见义勇为呢。”
他的这番话把肖童的强词夺理给扪回去了。李春强乘胜追击道:“你清醒一点吧,别一误再误卖弄你那点法律知识了。”
肖童低头无话。
李春强又卖了卖老,说:“其实你这种打架伤人的案子我经手的多了。这种案子,说大可以大,判个几年没什么稀奇。说小也可以小,也可以按一般治安案件处理。拘几天,罚点款,就放了你。你们学校也顶多给你个处分,你还可以接茬上大学。毕了业还可以当法官当律师,高高在上审别人的案子,什么都不影响。但如果判了刑,哪怕只有几年,你这学是上不成了,档案里有这么个污点,将来找工作都是个麻烦,弄不好你这辈子就这么完了。何去何从,你自己想想吧。”
李春强长篇大论完了,肖童抬起头,简短一句:“你想要我怎么办?”
“我路已经给你指明了,将功补过,犹未为晚。我们可以把你接治安处罚处理,但你出去了,要为我们工作。你应该为国家做的贡献,你必须做!”
肖童说:“我要是不答应你呢?”
李春强故意冷淡地说:“对我们没什么损失,你别以为我们是来求你的,说白了我们是来救你的,念着你过去为人民做过点贡献,我们不想看着你就这么毁了!”
肖童看一眼庆春,庆春从一开始就一言未发。肖童说:“我想和她单独谈谈。”
李春强断然拒绝:“不行,现在你没有资格提条件!”
肖童目光再看庆春,他大概以为庆春能够同意和他单独谈谈。但庆春仍然一言未发。肖童看了半天,绝望地自语道:“那好,那就让我毁了吧。”
李春强口干舌燥,以为成功,未想到这小子竟是如此朽木不堪雕琢。他无计可施,怒目而视了半天,才按响了警卫的呼叫铃。
从分局回来,李春强仍然余怒未消,他干刑警七八年了,处理过的案子已不可计数,什么嘎杂蔫横的人都见过,像肖童这样软硬不吃的家伙,还是头回遭遇。他苦笑着对庆春唠叨:“咱们也算是仁至义尽了吧,你今天可都听见了,我是上至国家利益,下至个人前途,大道理小道理都讲全了,可你看他那态度。人长得满机灵,脑子可是一根筋加一盆浆糊。我今天也算是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了吧。”
庆春却摇头:“你今天晓之以理了,我没见你动之以情。”
李春强语塞,一想,妈的也是。
庆春勿谓言之不预地批评道:“我早说过,你这套威胁利诱的方法,对他效果不会好。他的性格我比你了解。”
李春强一时不服,但又找不出道理来否定庆春的想法,抬杠地说:“你既然了解他,今天为什么一句话不说?”
庆春道:“他要和我单独谈,就是有松动。你硬不同意,那他的性格,当然就堵上这口气了。”
李春强说:“我就反对你这样,当时不说,事后又诸葛亮了。”
庆春说:“你当时那么气愤,你和他的情绪又那么顶牛,我能要求和他单谈吗,我总还得维护你的权威吧。”
李春强说:“不是要维护我的权威,我们和这种耳目的关系,必须要有一定权威。他想怎么着就怎么着,一味地哄着他顺着他,迟早会有麻烦。”
李春强的这个观点,从是非原则上是无懈可击的。但欧庆春回避了和他进行一场观念上的讨论,只是务实地问道:“我想我应该再去和他谈谈,好不好?”
虽然庆春用的是一种商量的口吻,但这口吻过于郑重和急迫,这种无意间流露出来的心情,让李春强感到疑惑和不快,但他还是同意了。他也不愿轻易放弃这个现成的情报来源,那两千一百万元的海洛因毕竟说明了肖童的价值。于是他说:“好啊,你再去谈谈也好,咱们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打个战术配合!”
李春强嘴上固然同意,心里对庆春再去谈话能收到多大成效,却有很大保留。
不料庆春第二天上午单独去了分局看守所,竟是马到成功,肖童居然无条件地答应了继续为他们工作。他不禁有点摸不着头脑了。问庆春有何法宝,庆春平淡地说:“你昨天不是把利害关系都讲清了吗,我无非唱个白脸说几句软话,让他下这个台阶罢了。”
这确是一个不容轻描淡写的成功,而庆春的神态,却并没有像李春强想象的那般兴奋,她的少言寡语,甚至使人感到几分暧昧难解。李春强始终想不出她和肖童究竟都说了些什么“软话”,她又是怎样地对他“动之以情”。
二十五
在肖童的问题上,欧阳兰兰彻底佩服了父亲的谋略和远见,她相信他既可以让肖童带上镣铐,也可以把他从缥绁中解放出来。
一切都是为她。
自从母亲死于车祸,她就是父亲的唯一亲人了。父亲始终不让她介入那些地下的生意,不让她参与任何违法的事情,不让她冒一点点风险。他殚精竭虑地为她筹划着另一种生活,一种富足,平安,合法的生活,也作为他自己未来的寄托和终老的归宿。
但她很清楚父亲的一切美好打算都是依靠贩毒。如果说,当她最初明了这内幕时还曾有过一丝恐怖和罪恶感的话,那么现在,在她知道父亲冒着生命危险所做的一切,都是在为她垒造幸福的时候,她除了在感情上体会到父爱的温暖之外,再也不去想别的什么了。
父亲说你应该好好学习英语,以后到了国外可以自己生活。但她对英语没有一点耐心和兴趣。
父亲说那你就找个懂英语又有才能又谦让厚道成熟持重的人结婚吧,然后让他带你出去照顾你保护你。而她对父亲找来的那些老气横秋的学究,也没有一点耐心和兴趣。
父亲说你什么本事也不学什么人都不爱,对什么都没兴趣,这世上还有什么能让你动心?
是的,她应有尽有,百无聊赖。她告诉父亲她不想出国,不想背英语,不想结婚生孩子。她对这一切都不会有兴趣。但这时出现了肖童。
是肖童使她在旷日持久的无聊和麻木中感受到那么纯洁的美,感受到清新,感受到健康。朝气和一种未被修饰的倔犟,一种毫不做作的浪荡和粗野。他的完美给了她从未体验过的激动和向往,她在见他的第一面就在内心里决定以身相许。她惊喜地意识到当自己一直冷藏在无意识中的那种激情一旦被发掘和释放,它所焕发出来的能量,无人可以阻挡,包括父亲,也包括肖童自己。
在一番阻挠和规劝无效之后,父亲务实地表示了无奈的宽容。肖童也在一阵明确的敌意和抵抗之后,松动了立场。至少他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