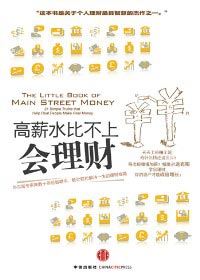不如安心做鸳鸯-第47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事,也只当作一番传闻来听,其中事事非非,江湖早有公论。如今闻蝶谷死灰复燃,但凡正道人士,怎不心生疑虑?
岂料她听得他这番话,不由冷冷一笑,嘲讽道:“无辜之人?今日这些双手染血之人,不知哪一位算得上无辜之人?二十多年前的那桩旧事小弟早有耳闻,不过是东海门垂诞闻蝶谷财物,找了个借口想侵占,岂料闻蝶谷中人不肯束手就擒,两方交手,各有损伤。东海门不甘罢休,摇唇鼓舌,鼓动江湖中人参战,这才有了后来那些战事,追根究底,不过是利益之争罢了,休得拿道义来作幌子,也不怕羞煞了道义二字!”
她这些日子追随叶初尘四处奔走查帐,自是见识了闻蝶谷的财势力量,兼且她又出身商贾之家,凡事皆以利益为先考量,自然说出了这番话来。倒不曾料到此言一出,竟教秦渠眉愣了一晌,将她这番话放在心中思量一番,不禁有些动摇。
二人缓缓而行,到得岛内所居之地,但见大门前开阔之地中间已是架起了木柴,堆了许多人头在一旁,海烈正端了一坛酒立定在柴堆之前,口中念念有词,一边祭酒一边红了眼眶,教在场诸人不无感慨,只道他兄弟情深,其兄与兄长之子过世二十多年,到如今他还不能忘怀,血债血偿,誓要将闻蝶谷诛杀干净,更有人佩服他节烈之义,交口称赞。
秦渠眉与谢描描立定在人后,她二人身旁正立着今日前往得云楼诛杀闻蝶谷的这一干人。这些人在江湖中不过是小门小派,大多年轻,是以对二十一年前江湖之中腥风血雨并无多大愤慨之心,反倒是前往得云楼诛杀哄抢,所获不菲。此时各自将怀中所揣首饰拿出来端详,这一位悄声道:“岑兄你瞧,得云楼所造钗子果真精致,无怪乎客似云来,也亏得此楼是闻蝶谷的产业,否则你我兄弟哪能平白得了这么许多精致的首饰,过几日回去哄哄家中那婆娘,她瞧着定然开心。
另一人将怀中古玉拿了出来,也瞧来瞧去,道:“我瞧着这块蟠螭佩饰也值个一二百两银子,玉质透澈莹润,我当时去拿之时,得云楼伙计死抓着不放,被我一刀便砍了首级下来。海少门主也说了,不过是些不义之财罢了,自然容得我们自取……”
谢描描握紧了双拳,只觉这些人身上血腥之气刺鼻难闻,手上青筋暴起,目中似要喷出火来。她自开始在各地查帐,一圈巡视下来自然明白,闻蝶谷门下作生意,最是规矩踏实不过。各地店铺无不是诚信待客,童叟无欺,是以生意自然兴隆。岂料今日却做了他人口中一块肥肉,任人宰割,当真令人痛心疾道,愤而难忍。
秦渠眉见得她的身躯微微摇晃,听得身旁这些人兴奋的低低议论,再思量一番谢描描先前之言,只觉不无道理。
场中冲天大火而起,空气之中弥漫着一股毛发与皮肉的焦臭之味,立在圈内的叶初尘与关斐皆是面沉似铁,眼看海烈滴下几滴泪来,也只冷眼瞧着。
七月十五,闻蝶谷门下东海镇得云楼被毁,楼中掌柜伙计共厨娘家眷,无一人生还,楼中财物尽被抢掠一空。
那一夜东海门大摆宴席,庆贺剿枭首战告捷,座中江湖豪客今日前往得云楼者皆满心欢喜,不曾去者尝有遗憾,也只拼命喝酒。
谢描描静坐在秦渠眉身旁,只将杯中之物一口口喝下去。倒是叶初尘与身旁太极门的掌门商无隐谈性正浓,将近三十年的江湖奇闻前辈轶事讲了个遍。商无隐初时只当他不过是地鼠门下,小门小派,自然见识颇浅。几句话谈下来,见得他年纪不大,但江湖掌故颇熟,各门各派武功也能点评一二,谈话又极是风趣,不由对他另眼看看,直拉着他拼酒,关斐试图将他拦下,但未曾奏效,见得自己左右手二人皆是一意灌酒,只恨不得自己也灌下去几十杯,醉他个昏天黑地,人事不知。
只是他向来便知,这位谷主虽年纪轻轻,但颇有几分前任谷主叶西池的狂狷洒脱,纵情任性之态,世上没有不敢做之事。此情此境,他面上虽带了三分笑意与商无隐攀谈,但眼底冰冷之色暗凝,这却是叶初尘大怒的前兆,若搁在往日闻蝶谷中,他早溜的不见踪影,此地却是逃不过,也不知道今晚谷主会作出什么难以收拾的事体来,唯有暗暗叫苦。
这头谢描描已是有了三分醉意,强自忍着不肯示弱。她的师尊无尘道长与玉真子恰也同席。她幼时多蒙无尘道长教导,她门下十余位弟子,对这位最小的弟子也算得上疼爱。谢描描又向来视师命为尊,但有今日这番聚会,眼瞧着闻蝶谷众人无故丧命,师傅虽然在座,却不肯多言,倒教她想起自己当初学武之时,师尊曾耳提面命:救人于厄,振人不赡;其言必信,其行必果; 不矜其能,羞伐其德。这些让她奉行为圭臬之语者,如今瞧来,不过是几句空话,师尊自己又何尝做得到?
反倒是江湖传闻,无尘道长与玉真子两位道长在江湖上也颇有侠名,一位剑术超绝,扶危济困,一位慈悲心肠,仁心仁术。二人难得齐聚东海门,自然多多亲近了一番。玉真子曾与谢描描有半师之恩,去年尤听得谢描描在镇江斧头帮失踪,早先时候与秦渠眉不曾同席,倒也不好特意前来询问,此时恰逢同席,自然将谢描描近况问询一遍,且与无尘道长微笑:“秦庄主可是道友徒弟的夫君,今日相识,正该相互好好亲近一番。”
秦渠眉虽不能确认谢描描底细,也曾瞧过她的武功路数,倒也知道她师从丹霞山,此时不免在桌上执礼相见,令无尘道长嘴角弯弯,极是慈蔼道:“秦庄主不必多礼,描描向来是个糊涂透顶的孩子,凡事参不透,还要请秦庄主多多容让。”
谢描描正将一口酒喂进口中,昏头涨脑,此时听得这话,只觉心内咸甜苦辣熬成了一锅粥,真正滋味难辨。无尘道长这番话,倒教她想起过去在丹霞山的旧日时光,那曾是她最为留恋的平静岁月,到如今回忆起来,亦是难忘。但她又确是个少根筋的主儿,执拗的心气儿一上来,更无半点相认的心思,自伤身世,又怜惜今日无故丧命之人,恨不得将自己溺毙在酒缸里才好。
秦渠眉见得她一杯接着一杯,并无停下来的意思,与无尘和玉真子两位道长告了罪,拖着谢描描回住处。
一年多前,叶初尘想尽了办法将这二人拆开,今日瞧着秦渠眉盯着谢描描的眼神,似乎瞧出了几分端倪。但今日闻蝶谷众人鲜血染就了东海镇,谢描描那点心思倒瞒不过他,若再教她回到紫竹山庄,他笃定不能。是以他倒是极为放心被秦渠眉带走的谢描描。
至少,安全无虞。
谢描描仰头去看,半空中玉轮高悬,周围草木的清香带着湿润之气扑鼻而来,她的心思似糊涂又似清醒,酒劲全上了头,脚下虽高低不分,磕磕绊绊,但紧搂着自己身子的这人,有强壮的臂弯,几乎算得上挟裹着自己而行。
她颤微微伸出手臂,喃喃叫道:“秦大哥……”
秦渠眉停了下来,只觉心神俱驰,难以控制,脑中一热,将她半扶半抱进了旁边的树丛,再也忍不住心中酸痛,重重吻了下去……口中是馥郁的酒香,柔软的丁香小舌,几乎令他几疑是梦。
他渐渐沉缅了下去,梦境是这样甜,现实是这样的苦。
洪波涌
ˇ洪波涌ˇ
谢描描已是大醉,只感觉一阵燥热,全身被困进一个不知名的地方,挣扎不开,不由嘟嚷:“叶初尘……”
秦渠眉似被这三个字惊醒,似兜头一盆凉水,从一个绮丽的迷梦里惊醒,紧盯着怀中那张酒意醺然的小脸。心中刹时有惊雷滚过——她失踪的这段日子里,果真与闻蝶谷大有关系……
仰头去看时,天上玉盘飞渡,人间清辉遍洒,照耀在他不曾看见的地方,那人软软靠在他的怀中,嘟着樱唇轻声呢喃:……你个王八蛋……走开……”
他再次俯下身来,瞧着她双目紧敛,黛眉微蹙,断断续续的叫:“……水……喝水……”
游目四顾,皆是山石林木,只得再抱起她来,脚步沉滞,缓缓向着自已的居处而去。
谢描描第二日醒来,见得自己平摊在一张大床之上,身旁再无旁人。她奇怪的爬起来,细细想来,昨夜自己似乎喝得酩酊大醉,被秦渠眉带走,那这间陌生的出奇的房间,定然便是秦渠眉在东海门的住处了。
低下头去,见自己睡得皱巴巴的衣服,她长呼了一口气,拍着胸口叹:“好险!幸好没有脱衣服!”
只听得房门轻响,便见秦渠眉推门而入,手中端着一碗汤,递了过来,笑容浅淡无痕,道:“小兄弟,你喝醉了还真是憨态可掬啊!”
谢描描接过那碗汤来,一仰脖喝干,见得他这幅似笑非笑的样子,不由猛然打了个激淋,呆道:“难道我昨晚出丑了?说错话了?”心中急跳,莫非自己说了什么话让他认了出来?
秦渠眉心里发苦,面上却但笑不语,只急得她团团乱转,好话说了一箩筐,就差抱着他,将整个身子都要贴上来:“秦大哥,快说说,我昨天究竟做了什么丢脸的事情?……你若是不肯说,我可真没脸呆在这里了……”颓然朝后坐去,双手掩面,似要哭出来一般,语声中尽是懊恼之意。
这房内三明两暗,布置极尽奢丽,她坐在凌乱的锦被之上,紧咬着双唇,小心的抬起头来,窥探着他的眼色,那般的小心翼翼。秦渠眉将心中涩意深深掩埋,顺势在她头顶敲了一下,笑叹道:“小兄弟,你这番模样,跟个刚断了奶的毛娃娃可没甚区别!”
谢描描恼羞成怒,顺手从床上拖了鸳枕扔了过去,怒道:“秦大哥休得胡说!”秀巧的耳珠已经通红,与面上肤色大异。
那锦心鸳鸯枕颇长,正是昨晚二人共枕过的,上面还留着两个亲密相连的陷下去的印子。秦渠眉昨晚已知她醉后也念念不忘闻蝶谷主叶初尘,他虽不曾见过那少年,也知他定然清隽俊逸,狂介任性……将鸳枕接在手中,恍惚似昨夜抱着沉醉过去的她一般,明知前面是悬崖也要忍不住凭着一腔孤勇而一意往前……
“小兄弟,莫非你有什么事瞒着为兄?”
将鸳枕放在床上,他揽了那人的颈子,感觉到手下的肌肤腻如凝脂,禁不住心中一荡,又夹杂着难以言喻的涩意,另一手在她头顶轻抚,顿见她目光躲闪,左顾右盼,似恍然大悟,叹道:“原来昨夜我竟是昏了头,睡在大哥房里了。也不知我帮中那两位哥哥怎么样了?容小弟先去看看!”小心推开了他,将鞋子套在脚上,一溜烟的跑了。
秦渠眉自斧头帮丢了谢描描,似被人强摘了心肺一般,日夜不宁。调了庄中大半人手,亲绘了四张谢描描的画像,令他们大江南北的去寻而未果。其后秦母病逝,守孝在家,方才将寻她之事耽搁了下来。
令他再想不到的是,不过是前来东海门参加喜宴,居然就教他碰见了她,只是如今虽然怜惜之心如旧,却不敢贸贸然捧了上去。唯有强捺着喜意,悄悄跟在她身后,亦出了房门,静静立在院中树影里。
谢描描一脚踢开房门,忍着面上作烧,冲了进去。见那二人睡得昏天黑地,恰被这声震天巨响惊醒,勉强睁开了眼睛,见得是她,复又闭上了眼睛,睡了过去。
她见得这二人这幅模样,走近床去,掐着关斐的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