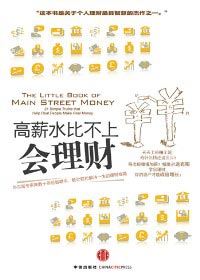不如安心做鸳鸯-第45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他手中鞭子松开,那施琳琅想也不想便挥出了第二鞭子,左手背在身后。谢描描瞧的真切,她的身后正背着三把幽蓝的飞刀,趁着秦渠眉分神与海非川说话,一边躲她的鞭子,那三把飞刀便冲着他而去,树上的谢描描一颗心顿时揪了上来,忍不住惊道:“小心飞刀!”
秦渠眉打落那三把飞刀,与海非川仰头向着树上看来, 只见树桠间缓缓走下来肤色微蜜的少年,再跃下两枝,正正坐在最下面的一截树桠之上,晃荡着双腿,笑嘻嘻道:“喂,新娘子,你这胡乱迁怒他人的作法可不地道啊!施家在江湖之上也是有名有姓的,你这般行事,不怕传出去惹人笑话?”
树下三人万料不到树上竟然藏着这样一个少年,秦渠眉见这少年笑得极是眼熟,笑嘻嘻正看着自己,不由抱拳道:“多谢小兄弟提醒!”
那少年摆摆手,“秦庄主大名,在下早有耳闻,不必客气!”从怀中摸出一声帕子来,径自跳下树去,自说自话将施琳琅刚发的那三把飞刀捡了回来,啧啧叹道:“够狠啊!居然是见血封喉的毒药。施家乃是江湖之中的名门正派,教出的女儿却是狠辣无比,随便对付一个不相干的人,居然也肯用这么下三滥的招数!少门主,你可真是所娶非人呐!”摇头晃脑,感慨不尽。
海非川似乎听进去了最后一句话,脸色变的很不好看,但也还是努力压抑,朝身后的房门去看,那紧闭的一扇门忽的打开,一盆盆的血水被人端了出来。那些嬷嬷早就听闻这位苏姨奶奶的受宠程度,更何况今夜海非川为了她生产不惜与刚进门的大奶奶发生冲突,哪里还敢怠慢?
施琳琅手中的鞭子想也不想,便向着谢描描而去,所幸谢描描近几个月来在闻蝶谷中被姬无凤追杀,那逃命的招数是练的溜熟,根本用不着别人提醒,已滑的像条泥鳅,在她的鞭影之中左躲右闪。不懂门道的人看着她险象环生,懂武的人看着,施琳琅居然连他的半片衣角都没沾到,还不断被他出言戏弄。
“我说大嫂,新妇要讲妇容妇德,敢问大嫂你做到了哪一点?新婚第一夜就被休回娘家,你父母面上也不大好看吧?”
唰的一声,施琳琅的鞭子再度抡了过来,秦渠眉只觉得
一股大力朝着自己撞了过来,那少年嗖一下便缩在了自己身后,从身后探出半个脑袋来,道:“秦庄主,方才在下出言提醒,这女子实在凶悍,在下抵挡不住,你可得还了这份情啊!”
秦渠眉见状只觉好笑,叹道:“随你!”将他往身后藏了藏,抓住了施琳琅挥过来的鞭子,冷冷道:“你这女人,忒也不识好歹!”
谢描描暗笑。
桃叶碎
ˇ桃叶碎ˇ
却说当时谢描描惊呼出声,叶初尘想要捂着她的嘴,已然来不及,只得在她耳边俯耳说了几句,关斐眼瞧着她从树上跃了下去,偷偷去窥叶初尘的脸,细碎浓密的树叶将他的脸掩在暗处,却是看不清他的表情。
再见她藏身在秦渠眉的背后,双后紧紧揪着他的衣角,可怜巴巴道:“秦庄主救救我,这海少夫人莫不是要在下的命不成?”
黑暗中,许是他听错了,竟疑似叶初尘冷哼了一声。
树下的秦渠眉许是真的恼了,手下再不留情,几招就将施琳琅的鞭子夺了过来。藏在他身后的谢描描劈手接了过来,啧啧赞叹:“真是把好鞭子,海夫人,容在下借来把玩几日再还,如何?”
施琳琅气得无计可施,恨恨瞪了海非川一眼,却是产房门哐啷一声打开,一个接生嬷嬷跌跌撞撞冲了出来,衣襟上全是血,扑到海非川面前就跪了下来,大呼:“少门主,姨奶奶生了一个小少爷下来……只是……只是……”
逢新生儿降世,必有啼哭之声,这嬷嬷既说生下了一个小少爷,却听不到幼儿啼哭之声,海非川面色巨变,磕磕绊绊道:“小少爷……”
“小少爷生下来便没有气息。”
那嬷嬷许是怕担责任,一早死命的磕下头去,几乎要哭出来,“少门主,姨奶奶近几日无心饮食,心气郁结,这才有了早产之症。”事到如今年也顾不得得罪施琳琅这位未来的当家奶奶,万一这位爷见得孩子早夭,怪罪下来,也不知道自己能不能见到明天的太阳也是个问题。
海非川闻言,一脚踢开那嬷嬷便向着产房冲了进去,他进去之后只听得房内惊呼连连,那些嬷嬷们哀求之声不断,只求他尽快离了血房,却不见他出来。
施琳琅许是被这早夭的孩子给吓住了,竟然忘了要鞭子,只呆呆的立在院中,面沉似铁,大红锦衣在夜风中飘扬,无端显出几分凄凉之意来。
谢描描见她这番景像,自己也略略明白了几分。若搁在从前的她身上,必然是懵懂无知的,可自家中遭逢巨变,再到与秦渠眉分离,这几个月以来她心中牵挂良多,自然对这位新娘子有了几分怜悯之意。轻手轻脚走过去,将鞭子递了给她:“喏,我不要你的鞭子了,你不必太过伤心!”
施琳琅从呆怔之中醒来,接过了这鞭子,长长呼出了一口气,强颜欢笑道:“我有什么可伤心的?伤心的应该是死了孩子的人吧?”
谢描描奇怪道:“既然你不伤心,流什么泪?”
“我哪里流泪了?”
她骇然去摸脸,触手一片凉意。
房内忽尔便传来了一声凄凄切切的哭声,似被人摁住了喉咙或者全无力气,只能发出一阵阵单薄悲伤的痛哭声,教人听得心都要碎了,更有男子温柔低语之声。又过得一刻,便见得产房之内的嬷嬷们鱼贯而出,其中一人手中抱着个红色的包裹,谢描描伸头去瞧,不明所以,摇摇秦渠眉的手臂:“秦庄主,那老嬷嬷手里拿着什么东西?”
秦渠眉眉头紧皱,轻声道:“死婴。”连他自己也说不清楚,心里是什么滋味。
谢描描长大了嘴巴,说不出话来。呆站了片刻,耳边听得秦渠眉小声道:“你我待在此间无益,不如去前厅饮酒如何?”
谢描描连连笑着摇头:“秦庄主与在下岂能并桌而坐?在下一介无名小卒,坐在前厅怕是会被轰出来的。”
秦渠眉向来是个冷淡寡言之人,只是今夜瞧着这少年的笑容似曾相识,在他的笑脸里不由有了片刻的失神,也不再勉强他,道:“不知小兄弟可否留下名姓,以后但有用得着秦某之处,秦某定当尽力。”
谢描描闻得他不再勉强自己,心下一阵黯然,道:“在下名冷风,秦庄主客气了,能与庄主相识,自是有缘,庄主还请自便。”
眼瞧着那人谢过她的提点之恩,越过施琳琅的陪侍,玄色衣衫渐渐消失在夜的另一头,她也垂头丧气,出了苏宁的院子,只觉鼻息间还有血腥味缭绕,一时挥之不去。
不过堪堪转过了两座院落,身后便搭上来了一只手,在她肩上重重拍了一下,道:“小兄弟,想什么呢?”
不出她所料,正是随后偷偷潜出来的叶初尘与关斐。
“想我的夫君。”
谢描描淡淡答他。
关斐一呆,终究忍不住笑出了声,指着她这一身的打扮,“少年郎想少年郎,莫非冷兄有分桃断袖之僻?”明知道她那句话说出来,身旁的谷主面色已经沉了下来,他还得打圆场。
谢描描忍无可忍,扬手掷出一把飞刀去,正是今晚施琳琅掷出的那把带毒的飞刀,一边躲闪一边哎哟叹息:“冷小兄弟,你怎可一言不合便做出这等下三流的事情来?那飞刀可是见血封喉,莫非真想置为兄于死地?”
这一夜谢描描在东海门喝的大醉,被关斐与叶初尘架着回房。此日早晨她揉着疼得快裂开的脑袋睁开了眼睛,愈加怀念过去那些酒醉的日子,秦渠眉的温柔体贴。
——那时候,他何尝让她有过这种死不如死的滋味?
她试着要爬起来,这才发现睡的正是张大床,脚底下横着关斐,身侧睡着叶初尘,惊得她猛然起身,简直疑似幻境,一脚踹在关斐胫骨之上,那人在恬梦之中惨呼一声,抱着胫骨便跳了起来。
头顶的叶初尘漫不经心睁开眼睛,极是不耐烦道:“关斐,你既然不想睡大床,昨夜就该守在门外一夜,大清早的嚎什么嚎?”
关斐五官都痛得扭到了一起,指着谢描描气得说不出话来:“昨夜要不是我厚着脸皮挤上床来,谢描描,你早成了谷主盘中的菜了,别不领情!”
谢描描纵起身来,眼瞧着又要照着关斐的胫骨下去一脚,只惊得那孩子大叫着要躲,岂料她只是虚晃一招,迅速转了个身,一脚踢在叶初尘胫骨之上,怒骂道:“无耻之徒!”
跳下床去梳洗打扮。
关斐见得叶初尘闭着的眼睛猛然一睁,也是“哎哟”一声惨呼,抱着胫骨也如自己一般狂跳了起来,这才将苦皱在一起的五官松散开来。
三人梳洗完毕,推门出来之时,竟然发现此处是个极为僻静雅洁的院落,院内花木葱笼,只听得隔壁房门吱哑一声,从里面迈出一人来,身形挺拔如青松玉竹,目光幽暗似寒潭漆盲,转头朝这边一眼瞧过来,叶初尘与关斐皆是一愣,却见得谢描描已经笑开了花,跑了过去甜甜道:“秦大哥早!”
二人面面相窥。
昨夜二人见得谢描描酩酊大醉,便向庄中仆役讨要了一间房,回来歇息。夜半之时只听得隔壁也住了人进来,却不知正是秦渠眉。
秦渠眉唇角微扬,淡淡道:“小兄弟早,不如一同去前厅用饭?”
谢描描难得灵慧一次,奇道:“秦大哥,这东海门的门主莫非昨晚昏了头,竟然会将我这小小的帮派与你放在一个院内?”
“我见得昨夜住房紧张,同海门主说了,将你们安顿在我住的院内。——这两位,是你帮中的兄弟?”
谢描描见得那二人瘸着条腿缓缓而来,连连点头,道:“这两位皆是我帮中兄弟,只是腿有旧疾,走起路来……有点小小的问题,功夫却是顶好的,心眼也是顶了的……若非这旧疾,两位哥哥也不至于打了这么些年的光棍……”她一派天真烂漫,说起来竟似为了这二人无限惋惜一般,连秦渠眉也不禁为她这忧心忡忡的神色给逗得笑了起来,小声道:“你的两位哥哥过来了。”
叶初尘与关斐早已闻得他二人的窃窃私语,面色不禁黑了几分,还要上前与秦渠眉见礼。一行几人去了前厅用餐。
沿途众人见得这少年与这两个汉子昨日不过坐在院里喝酒,今日居然与秦渠眉前排而行,瞧那少年的神色,分明与秦渠眉极熟,都不禁想要探察这三个的来路,可惜这次海家宴客的贴子不论江湖大小门派,一律有份。一时半刻,又哪里问得清楚这少年的来历。
到得前厅之时,谢描描极与秦渠眉客气几句,便向着昨日那一干小门派聚集地而去,正走了两步,却被秦渠眉伸手拉住,她只觉拉着自己的那手干燥温暖,似乎昨天还拉着自己的手,神情不由恍惚,是以并未察觉到,秦渠眉不过是无心的一拉,只觉入手绵软秀气,连她手心里的两处茧子也是极为熟悉的,神色一僵,唇角绽出一抹浅笑来,更紧的拉住了那手,再三确认,只觉一年以来心中所压的那块巨石缓缓下落,连那声音也少了几分不自觉的冷意来:“小兄弟,你还是随为兄去前厅用餐吧!”
谢描描恍惚之间,便被他牵着手,一步步进了大厅,被他按坐在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