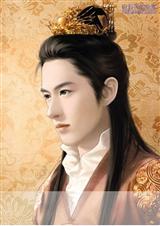������ͥ��-��12����
�������Ϸ���� �� �� �� �ɿ������·�ҳ���������ϵ� Enter ���ɻص�����Ŀ¼ҳ���������Ϸ���� �� �ɻص���ҳ������
��������δ�Ķ��ꣿ������ǩ�ѱ��´μ����Ķ���
����������δ���ˣ��ؽ�Ү��ѧ�ţ���������������Զ�������ҹ���ˣ����е�Ҳ�r������������������Կ��ξ��������Ÿ봫�ص���Ϣ������������Բ��������渶�������ɳ����ɱ�ж��˼������֮�⡣��
�������������ɹ��þݵ�����ʮ���ݣ������������������ˡ�������ʾ�����齫�������٣�������֮�ƣ��־ñغϣ�˭����������������������
������ҹ��Ѭ�����ϴ����룬�����з�������֮��������������������ϣ���ѩͰ�еij��������ǡ���ô��ˣ�ȡ����ϸϸһ�У���Ƥ��ȿ����ô��������ɫ��������������
���������ϣ�����ָ�Թ��������˳�����֮�ˣ�����
��������Ҳ������˶��ԡ�ֻ�Ǿ��ã��ⳡ���������ˡ�ս��ʤ��̫˳���ˡ���ʱ������̫��˳���ˣ�����������忻��������������ν�ġ���������������⸣���С��ա�����
�������º�ս��������Ϣ��������
����������ʽ������ȴ�ǿڶ��ഫ��˽�顣������֮���䣬�����������ݣ��������գ���������һƬ���Ļ̵̻ķ�����ড���
����һ��֮���Թ��壬�����ɽ�Ү���ݸ�ĸ�����֮ս�в�֪���٣�����δ������
���������д��Ե���ʥ�������ѣ����������ı��̫�����书��������Ϊ�ۡ���
�������ͬʱ�����и��������̽������������Ŀ�ʼ������������
�����������ǰ���ӿ�������Ʋ��ꡣ��
������ҹ����
�����������������һ���綹��ӳ�ô�ֽ��֦��Ҷӿ����Ӱ�S�ʡ���
�����������շת���࣬�������ߣ��ɴ��������������ڰ���ҹ������
�������顱��һ����������Ȼ���ƿ���������ҹ��������¡¡�����ļ���ӭ����������
�����������Ϩ���ˡ���
����һ����Ӱ�����ŷ磬�����꣬�����һ�ѽ��ҽ���ס����
������˭�����Ҵ�֮�£�ֻ��һ�ɳ�ʪ�������Ϣ���ڼ����ϣ����ж�ʱ�������ֻ̿֡���
������Ī�£����ҡ�������
�����İ��У���է����ϲ�������ѣ�����
������������§��һ�£����ɿ��ֱۣ���ڵ�������һ�������ĵ�������ڷ�������̫�����ҳɹ��ˣ�����
�������������˿��������ߵ��ű߽������ؽ������������ƻ������ɫ�ʵ�������������ô���£�����
������������ϲɫ��ѹ����������������ʱ���������˺ͣ���ת˲���ŵ�ʱ��������
����������˵����ϸЩ������
�������ڰ������£����˿���������������˵������������Χ�����ݣ��ۿ�����ָ�տɴ�����Ȼ��̽���뱨������Ү��ɳ�������ݣ�ǰ���ѵ��������ˡ�������������Ԯ�ѵ�������ô���Ҿ�����ǰȥӭս��ɱ���������ٶ�˳�δ�١���������Ӫ����ͳ������ӽ����������ӱߣ������ɱ�Խ�Ӷ���������������ˣ�������Ծ������ִ��е��ɱ��ǰȥ��Ү��ɳ������־ܣ��������������������裬��ɱ�����ذ���������š�Լ��������ʱ�����ɱ��������ڣ������IJ���֧�֣������ȥ������
������������ɱ���ȴ����ִ���죬����ǰ�����������������죬�����ɱ�����������ɱ�����������ɽ�Ү��б�����������ɽ�Ү���ݸ硣��Ү���ݸ�ϵ�ɰ����������¼�ȫ�������º��Ǿ�������һ��ʮ����ʮ���٣����Ҿ���ս��ƣ������������֧�������������ʱ�ֵ���ס����ɢ�ҡ�Ү���ݸ������ᣬ�����мᣬ��ȡ����������Զ��̣�һʱ�˲������ݣ����Ǹ�����������ǰ�ں�����������ɥ�ڴ��ˣ�����
�����������أ�������֪�������ģ��ּ������û�����ɫ������˵��Ļ��������̲�ס�ߴٵ�����
���������������������ݣ�����ʿ��½���ӻأ�����ʿ��ɥ���������ˡ�ʱ����ĺ�����������Ϣ������Ү���ݸ磬�����ɱ����ָ�ɱ�����Ҿ���Ϣδ�������к��ij��У�һ���ɾ���������Ҹ�Ѱ��·��ͳ���˿�ȥ�����ǻ�������ӣ�Ҳ�౼ɢ����һ����������֮������ٲ����ټ��ˡ�����
����˵���˴�������Ȼ�͵������һ���������˲�֪����ȴ�����������������ֻ��ƥ�����ӱ��ߣ���������ȥ�ˡ���ɫ���裬��ãĪ�棬·�����߸߰˵ͣ��������У���Ҫ�����ǣ��ϱ�����̽��·�飬��Ƭ������Ԩ�������ȣ�����
�������㡭���������˸�������ɵ�������֣�̽�����֪̽�ɱ���Ԯ��Ү��б����Ү���ݸ�����������׳����˽�Ҫ�ľ���������©̽������
������Ц�ˣ���������ҷ������Եġ�ת˲���ŵ�ʱ���������������룬�ұ����죬�кβ��ɣ�����
�����Ҷ�ʱ�����ˡ���
��������֣�ίʵ��������
�������һ��������ʧ�٣����Ĵ��ң�����֮˵�ս���ʢ��ӵ���¾���Ҳ��������Ȼ�ˡ����ο�����Ѫͳ�մ��������������������Ȼ�������IJ�����ѡ����
������������ǰ��Ϥ��ȴ�ַ·�İ�������գ������̾�˿����������ѣ������ȷ�Ϲ�����������������������
����������Ȼ����ȥ̽�����һƬ�������ף�����һ�ˡ����������û����ʬ�����ˣ�����Ȼ�������أ�����Ŀ���еij������⣬ȴ�����˳���������ʵ�����ҿ�ʼ���ɸ�������������ʱ������ͨ�������µĹ��ˣ�����DZ����δ��Ѩ�Ļ����С�̫������֪��ô�����ʵ�������ɫ���ϣ��촽�ںڣ��������Ƕ�ҩ���£�ʲô�������㣬��ȫ��һ�ɺ��ԣ��ѵ��㲻��������ô�����ڸ��������ټ��������һҹ��������
�������ѵ���һ�����죡��
����������꽻�ӵ���ҹ����һ�����죬����ʵ��������������ľ�����
�����ҽ������ű��Լ������ڵصIJ�����촽���ɶ��Ƶز�������������
������������ġ���֮��ȥ��һĻ���ָ���������ǰ����
��������棬�ϵĴ������ȴ������Ŀ�⣬ѩ��������ij�������ӡ����������ԶԶ�ĵط�һ��һ���û��ţ����Ļ����������ɭ�ϵ���ĵ��ӻز�Ϣ������
�����Թ���һ�����Ǹ�ҹ�����������ܣ���ǧ���غ�������ѹ�壬����ȴֻ���ң�Ҳֻ�����Ҷ��Գ�����һ�С��κ��ˣ��κ��˶�����Ϊ�ҵ�����������ϸ����м�����ѣ������ܡ���
����ͷʹ���ѡ��ұ���ͷ���������ӣ�����һ��ģ����ʹ�����������
������̫��������
������������������æ���ҵؽ��ұ�����ϣ��������岻��ô�������ȥ��̫ҽ������
�����Ұ����亹�乵Ķ�ǣ���һ�ֽ����������������ˡ���ֻ�Ǿɼ�������������ЪϢ��á������밲����Ъһ�ᡭ������
���������浣�ǣ�ȴ�ֲ��̷���֮�⣬ֻ��ץ�����ҵ��֣�����齱ߣ�����š����ü����̫��������ÿ�����£��ǵúú�ҽ�ε������ɡ������������յǻ�����һҪ�±��Ǽ���������ҽ�����Ҫ���㼰�翵����������
�������ڽ���δ�����ޫ�䣬���á����յǻ������֣�һƬ�հ����ӣ���֪Ϊ��ȴ����Ī���Ŀ־��벻����ֱ���ӻ�ã�����ѣ���������������䣡��
�����վ��в������ʣ���־���������ǣ�����ģ������
���ġ���ʮ���¡���ˮ����
�������ƺ����˸��ܳ����Ρ���
�����ξ����Ҷ��Ե���Σ¥�������̿������պ��ס�������ȥ������ɽĨ�ƣ���ճ˥�ݣ�б���⣬��ѻ��㣬��ˮ�ƹ´壬�ƻ��ѻƻ衣��
����¥�߿նϻ꣬������¥��ȴ������Ѱ�������ڡ���
����ɲʱ����ҡ�ض���¥һ��һ�ڲ��ϵ����ߣ�ֱ���������һֽ̿��ƣ���������ȣ�ȴ�����������������
���������Ȼ�Ždz�����������������
���������װ�ķ��죬ʹ���Ի�˯�о��ѡ������������Լ���ŵ����ִӶ��Ϸ���������æ�ʣ���ʲôʱ�̣�����
�����������ϣ���îʱ���̡�����ˮ���б�Ӧ�ţ��߽�������Ƚ������Ҷ��ϡ���
������һ�Ѳ������������𣬴�æ��������
������ˮ�����������ϣ���Ҫȥ�ģ�����
�������ʹ���������һ������Ļش�����������������ֱ���ʹ�����
������ʮ��������֮���»ʵǻ���ʽ��ʽ��ʼ����
��������ȴƾ�ż��������������Ķ����������У�������ׯ�����µ������У����ص�ɱ������
�������ѡ����Ҵ�δ��˾��̼��е������ϲ�����ƽ������֪��ʱ�����ѳ�Ϊ������Ī��İ�ο����ů���������������һ����һ�ε�ӵ����ʧȥ������������������Ϊ�������飬��˼������ˮ��ȴ�վ����ǷŲ��¡�������һ�����顱�֡���
��������ͬʱҲ���ѵط������ҶԵ��ѵ��飬�ȷǰ��飬�ַ����飬������������ʦ�ุ������Ҳ��ȥ��Զ�������������е����⣬ֻ����ֱ���������������顢��������������֮������һ��ǣ������
�����Ҿ���Ը��ʧȥ������
������ʯ���̳ɵ�ƽ����·�ϣ����ַɿ�����������¡¡���졣�����еIJ�����������֮������ǿ�ң����ϵش߲������������Ž�ˮ�����϶�ȥ��������ٳ����Ľֵ�¥�����ڳ������ǿ���������첨�ţ�ֱ��ʹ�����ɱ���ȥ����
����̤�Ϻ��������ɵ��ϵ�ʯ�ݣ��Ҵ�δ�������㽹�Ƶظо�������һ��㲽�����ϵ��ذ��������ô������ô�ߣ��·�һ������ͷ�����ݣ�ֱ����������
�������������ݵĶ��ˣ����Ǵ�ǧ����ܿܿ���������۵ġ���η�ġ�����Ȼ�����������ŵģ��������ϵľ���Ȩ������
����û�����ܰ��Ѷ����Ŀ�����������Ϊ���ָ�����Ը���������������ȴ����������ĥ����Ը�Գ�֮�����������������ԭ��
�����������������ˣ��������������ʮ�������ˣ�������ȡ����֮��������һ��һ�����ܶ���ʼ����
�����ġ��̡��ܡ��ء��������Թ���ˡ������ֻصĴ桢�ˡ�˥������ֱ����������������ֱ���������ڳ�������һ��Ϊֹ����
�������˵�����ҿ������ŵ�������ʲô�أ��Կ�ط�����������µ�һ��������ʲô�أ��Թ�����Ļ��Ǵ۶ᵽ�ֵ����Ͻ�ɽ����ʲô�أ���������ˮ�µ�һ�����ΰ��ˣ���
���������Ҷ��ԣ��⸡��һ����λȨ�ơ��ٻ���������ѵİ�Σ��ȼ�ֱ����������������ݽ棬��ֵһ�ӡ���
�����ҵ�һ������������ᶨ�ؿ���������ʵ��Ը����������������ٹ̵�����Ѷϣ������أ������˵أ����������ʯ��֮�ϣ����������յ�ѡ��
����ׯ�ϵ�����֮��ֹͣ�ˡ���
���������������Ȼ������ţ��������ˡ���
������ʯ�ݵ���ߴ���һ�����ֿ������Ӱ���Ƹ������ң���������������Ц�⣺���ع⣬�������ˣ�����
����������������Ŀ����Ц�������������书�����Ե���ͨ���ѹ�����ı���棬�����������أ��м���¶֮������ƫ��η�������ˡ�����
���������ޱ����һ��һ��̤����ܯ��������̧���ĵ��Ѿ͵����������ؾ���ʯ���ϣ�������Ѫ��һ��Ƭ������Ⱦ�����浤ϼ�����е����������Ȼ�������ݺ��⡣��
�������أ�������һ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