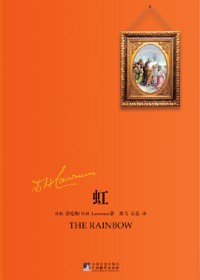花边文学-第20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运命
电影“《姊妹花》(2)中的穷老太婆对她的穷女儿说:‘穷人终是穷人,你要忍耐些!’”宗汉(3)先生慨然指出,名之曰“穷人哲学”(见《大晚报》)。
自然,这是教人安贫的,那根据是“运命”。古今圣贤的主张此说者已经不在少数了,但是不安贫的穷人也“终是”很不少。“智者千虑,必有一失”,这里的“失”,是在非到盖棺之后,一个人的运命“终是”不可知。
豫言运命者也未尝没有人,看相的,排八字的,到处都是。然而他们对于主顾,肯断定他穷到底的是很少的,即使有,大家的学说又不能相一致,甲说当穷,乙却说当富,这就使穷人不能确信他将来的一定的运命。
不信运命,就不能“安分”,穷人买奖券,便是一种“非分之想”。但这于国家,现在是不能说没有益处的。不过“有一利必有一弊”,运命既然不可知,穷人又何妨想做皇帝,这就使中国出现了《推背图》(4)。据宋人说,五代时候,许多人都看了这图给自己的儿子取名字,希望应着将来的吉兆,直到宋太宗(?)抽乱了一百本,与别本一同流通,读者见次序多不相同,莫衷一是,这才不再珍藏了。然而九一八那时,上海却还大卖着《推背图》的新印本。
“安贫”诚然是天下太平的要道,但倘使无法指定究竟的运命,总不能令人死心塌地。现在的优生学(5),本可以说是科学的了,中国也正有人提倡着,冀以济运命说之穷,而历史又偏偏不挣气,汉高祖(6)的父亲并非皇帝,李白的儿子也不是诗人;还有立志传,絮絮叨叨的在对人讲西洋的谁以冒险成功,谁又以空手致富。
运命说之毫不足以治国平天下,是有明明白白的履历的。倘若还要用它来做工具,那中国的运命可真要“穷”极无聊了。二月二十三日。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二月二十六日《申报·自由谈》。
(2)《姊妹花》郑正秋根据自己编写的舞台剧《贵人与犯人》改编和导演的电影,一九三三年由上海明星影片公司摄制。影片以一九二四年军阀内战为背景,描写了一对自幼离散的孪生姊妹,因处境不同,妹妹成了军阀的姨太太,姊姊成了囚犯。结局是姊妹相认,与父母阖家团圆。
(3)宗汉即邵宗汉,江苏武进人。他的《穷人哲学》一文发表在一九三四年二月二十日《大晚报》“日日谈”。
(4)《推背图》参看本卷第93页注(6)。(5)优生学英国哥尔登创立的学说,他认为人或人种在生理和智力上的差别由遗传所决定,研究如何改进人类的遗传性。(6)汉高祖即刘邦(前247—前195),字季,沛县(今属江苏)人,汉王朝的建立者。
再论重译
看到穆木天先生的《论重译及其他》下篇(2)的末尾,才知道是在释我的误会。我却觉得并无什么误会,不同之点,只在倒过了一个轻重,我主张首先要看成绩的好坏,而不管译文是直接或间接,以及译者是怎样的动机。
木天先生要译者“自知”,用自己的长处,译成“一劳永逸”的书。要不然,还是不动手的好。这就是说,与其来种荆棘,不如留下一片白地,让别的好园丁来种可以永久观赏的佳花。但是,“一劳永逸”的话,有是有的,而“一劳永逸”的事却极少,就文字而论,中国的这方块字便决非“一劳永逸”的符号。况且白地也决不能永久的保留,既有空地,便会生长荆棘或雀麦。最要紧的是有人来处理,或者培植,或者删除,使翻译界略免于芜杂。这就是批评。
然而我们向来看轻着翻译,尤其是重译。对于创作,批评家是总算时时开口的,一到翻译,则前几年还偶有专指误译的文章,近来就极其少见;对于重译的更其少。但在工作上,批评翻译却比批评创作难,不但看原文须有译者以上的工力,对作品也须有译者以上的理解。如木天先生所说,重译有数种译本作参考,这在译者是极为便利的,因为甲译本可疑时,能够参看乙译本。直接译就不然了,一有不懂的地方,便无法可想,因为世界上是没有用了不同的文章,来写两部意义句句相同的作品的作者的。重译的书之多,这也许是一种原因,说偷懒也行,但大约也还是语学的力量不足的缘故。遇到这种参酌各本而成的译本,批评就更为难了,至少也得能看各种原译本。如陈源译的《父与子》(3),鲁迅译的《毁灭》(4),就都属于这一类的。
我以为翻译的路要放宽,批评的工作要着重。倘只是立论极严,想使译者自己慎重,倒会得到相反的结果,要好的慎重了,乱译者却还是乱译,这时恶译本就会比稍好的译本多。
临末还有几句不大紧要的话。木天先生因为怀疑重译,见了德译本之后,连他自己所译的《塔什干》,也定为法文原译是删节本了。(5)其实是不然的。德译本虽然厚,但那是两部小说合订在一起的,后面的大半,就是绥拉菲摩维支的《铁流》(6)。所以我们所有的汉译《塔什干》,也并不是节本。七月三日。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七月七日《申报·自由谈》。(2)穆木天的《论重译及其它(下)》载一九三四年七月二日《申报·自由谈》,其中说:“我们作翻译时,须有权变的办法,但是,一劳永逸的办法,也是不能忽视的。我们在不得已的条件下自然是要容许,甚至要求间接翻译,但是,我们也要防止那些阻碍真实的直接翻译本的间接译出的劣货。而对作品之了解,是翻译时的先决条件。作品中的表现方式也是要注意的。能‘一劳永逸’时,最好是想‘一劳永逸’的办法。无深解的买办式的翻译是不得许可的。”又说:“关于翻译文学可讨论的问题甚多,希望忠实的文学者多多发表些意见。看见史贲先生的《论重译》,使我不得不发表出来以上的意见,以释其误会。”
(3)陈源译的俄国屠格涅夫《父与子》,是根据英文译本和法文译本转译的,一九三○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4)鲁迅译的《毁灭》,根据日文译本,并参看德、英文译本。(5)穆木天在一九三四年六月三十日《申报·自由谈》发表的《论重译及其他(上)》一文中说:“我是从法文本译过涅维洛夫的《塔什干》的,可是去年看见该书的德译本,比法译本分量多过几乎有一倍。”《塔什干》,原名《丰饶的城塔什干》,穆木天的译本一九三○年由上海北新书局出版。
(6)绥拉菲摩维支(A.C._J^GYJg,1863—1949)苏联准摇!短鳌肥*他所著的长篇小说。
正是时候
张承禄
“山梁雌雉,时哉时哉!”(2)东西是自有其时候的。
圣经,佛典,受一部分人们的奚落已经十多年了,“觉今是而昨非”(3),现在就是复兴的时候。关岳(4),是清朝屡经封赠的神明,被民元革命所闲却;从新记得,是袁世凯的晚年,但又和袁世凯一同盖了棺;而第二次从新记得,则是在现在。这时候,当然要重文言,掉文袋(5),标雅致,看古书。
如果是小家子弟,则纵使外面怎样大风雨,也还要勇往直前,拚命挣扎的,因为他没有安稳的老巢可归,只得向前干。虽然成家立业之后,他也许修家谱,造祠堂,俨然以旧家子弟自居,但这究竟是后话。倘是旧家子弟呢,为了逞雄,好奇,趋时,吃饭,固然也未必不出门,然而只因为一点小成功,或者一点小挫折,都能够使他立刻退缩。这一缩而且缩得不小,简直退回家,更坏的是他的家乃是一所古老破烂的大宅子。
这大宅子里有仓中的旧货,有壁角的灰尘,一时实在搬不尽。倘有坐食的余闲,还可以东寻西觅,那就修破书,擦古瓶,读家谱,怀祖德,来消磨他若干岁月。如果是穷极无聊了,那就更要修破书,擦古瓶,读家谱,怀祖德,甚而至于翻肮脏的墙根,开空虚的抽屉,想发见连他自己也莫名其妙的宝贝,来救这无法可想的贫穷。这两种人,小康和穷乏,是不同的,悠闲和急迫,是不同的,因而收场的缓促,也不同的,但当这时候,却都正在古董中讨生活,所以那主张和行为,便无不同,而声势也好像见得浩大了。
于是就又影响了一部分的青年们,以为在古董中真可以寻出自己的救星。他看看小康者,是这么闲适,看看急迫者,是这么专精,这,就总应该有些道理。会有仿效的人,是当然的。然而,时光也绝不留情,他将终于得到一个空虚,急迫者是妄想,小康者是玩笑。主张者倘无特操,无灼见,则说古董应该供在香案上或掷在茅厕里,其实,都不过在尽一时的自欺欺人的任务,要寻前例,是随处皆是的。六月二十三日。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六月二十六日《申报·自由谈》。
(2)“山梁雌雉,时哉时哉!”语见《论语·乡党》。(3)“觉今是而昨非”语见晋代陶渊明《归去来兮辞》。(4)关岳指关羽和岳飞。万历四十二年(1614),明朝政府封关羽为“三界伏魔大帝”,并在宫中设庙奉祀。清朝对关羽累加封号,称“忠义、神武、灵佑、仁勇、威显、护国、保民、精诚、绥靖、翊赞、宣德关圣大帝”。清末民初祭祀渐废。一九一四年袁世凯在称帝前重新下令合祀关岳。一九三四年广东军阀陈济棠又向国民党政府提议恢复孔丘及关岳祀典,并于该年三月二十八日举行“仲春上戊祀关岳典礼”。
(5)掉文袋又叫掉书袋。《南唐书·彭利用传》:“言必据书史,断章破句,以代常谈,俗谓之掉书袋。”
知了世界
中国的学者们,多以为各种智识,一定出于圣贤,或者至少是学者之口;连火和草药的发明应用,也和民众无缘,全由古圣王一手包办:燧人氏,神农氏(2)。所以,有人(3)以为“一若各种智识,必出诸动物之口,斯亦奇矣”,是毫不足奇的。
况且,“出诸动物之口”的智识,在我们中国,也常常不是真智识。天气热得要命,窗门都打开了,装着无线电播音机的人家,便都把音波放到街头,“与民同乐”(4)。咿咿唉唉,唱呀唱呀。外国我不知道,中国的播音,竟是从早到夜,都有戏唱的,它一会儿尖,一会儿沙,只要你愿意,简直能够使你耳根没有一刻清净。同时开了风扇,吃着冰淇淋,不但和“水位大涨”“旱象已成”之处毫不相干,就是和窗外流着油汗,整天在挣扎过活的人们的地方,也完全是两个世界。
我在咿咿唉唉的曼声高唱中,忽然记得了法国诗人拉芳丁(5)的有名的寓言:《知了和蚂蚁》。也是这样的火一般的太阳的夏天,蚂蚁在地面上辛辛苦苦地作工,知了却在枝头高吟,一面还笑蚂蚁俗。然而秋风来了,凉森森的一天比一天凉,这时知了无衣无食,变了小瘪三,却给早有准备的蚂蚁教训了一顿。这是我在小学校“受教育”的时候,先生讲给我听的。我那时好像很感动,至今有时还记得。
但是,虽然记得,却又因了“毕业即失业”的教训,意见和蚂蚁已经很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