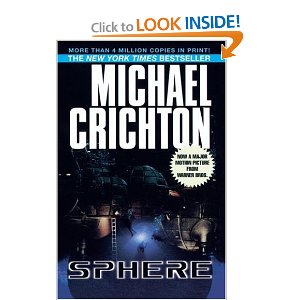深海·人鱼的信物-第95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有个孩子也不错啊,”餐桌那边的阿寻冲着路明远甜甜一笑,习芸也不由自主地随着他笑了起来,“不像我,一天到晚忙得要死还不知道自己到底在为什么拼命……”
习芸毕业之后就进了一家合资公司做起了小白领,平时在世界各地飞来飞去,见面的机会也非常少。她先后谈了几个男朋友,不过好像都没到谈婚论嫁的程度。
习芸看了看路明远怀里的阿寻,很突然地问我,“你还记不记得大二那年我跟你去了沙湾过暑假的事?”
我的心咚地一跳。抬眼看时,习芸脸上却是一副微带懊恼的戏谑神色,“那时候邻居家里就有一个蓝色眼睛的帅哥,不知怎么搞的,我追着追着就放弃了……”她脑海中的那一段记忆曾被深海做过手脚,她不应该记得的。难道说因为深海被封印的缘故,他所施展的禁术也开始慢慢失去效果?
“你大概追到一半又发现什么新目标了吧?”我勉强笑了笑,心里却很想知道关于那个夏天她到底还记得些什么。
“大概是吧,记得不大清了。”习芸长长地叹了口气,“后来出了溺水的事,送我回来的就是另外一个男生了,也不知当时我是怎么想的……”
当时被抹去了一部分记忆的还有那群出来做调研的大学生。如果习芸的记忆已经恢复.他们也应该也同样恢复了有关那个夏天的部分记忆,很有可能他们都会记起那个长着蓝色眼睛的神秘青年……这会不会惹来什么麻烦呢?深海不在,迦南也不在。米娅夫妇是我不想去招惹的,而夜族人却是我不能去招惹的。这个问题我应该问谁?往好的方面想,也许时过境迁,他们纵然想起深海的样子,也不过是一个不记得名字的陌生人。我们每个人的记忆里都有很多这样的人。对于深海,他们应该已经失去了刨根问底的兴趣吧。
现在,我也只能这样希望了。
因为约好了由路一带路去市郊那个废弃的工厂实地考察,所以头天晚上我把闹铃定在了凌晨五点钟。
路一说那个地方看地图虽然不远,但是因为附近正在修高速公路的缘故,要沿着小路绕一个圈子,所以时间上就有些说不准了。他还要搭乘当晚的航班回广州去见老陈,所以有事只能尽量往前赶。最初的计划是我自己跟着他去了解一下路线的,因为我不想让路一知道蔡庸那些人的存在。但是蔡庸认为我对
他需要什么样的场地完全没有概念——实际上,我对他到底需要什么样的场地也确实没有概念,‘照我最初的想法,把蔡庸持有部分股份的那家俱乐部租下来不是也很方便吗?可是蔡庸却列举了一系列的原因:私密性啦、场馆的限制啦、普通的训练场无法支撑特殊要求的训练啦等等,因此思来想去也只能把蔡庸带着一起去。
我一直对蔡庸的底细充满了好奇心。他的年纪虽然不大,但是世界各地的风土人情他都能说个头头是道,让人觉得他似乎去过很多地方。他的拳脚很厉害,枪法也好,对于如何训练我们找来的高手们他也是一副成竹在胸的架势,怎么看这些技巧都不应该是一个酒吧老板应该精通的。
而且他还有那么一位比他自己还要神秘的弟弟。
不过好奇归好奇,我也知道在我和蔡庸之间有一道坎是我不能去触碰的。他并不是我的雇员,但也不是我的朋友,关于身份,我不知道该如何给他定位,我甚至不知道他是否能算作深海的朋友。可是深海相信他,我又确实找不到比他更合适的帮手了。在这整件事情上,看到那些琐碎然而却又关键的细节都被他大包大揽地兜到了自己身上,我的感觉也变得越来越复杂。
看来,古人所说的疑人不用,用人不疑,这种气度我果然没有,于是,我只能把希望寄托在时间上。也许随着时间的流逝,在我和他,包括我们找来的那些本领高强的男人们之间能够磨合出一种类似于战友一般的感情来。佣兵听起来太冰冷,而我们之间的合作关系又明显还没有到达朋友的程度。还是战友这个定位比较合适,不冷不热,不远不近。不需要相亲相爱,只需要彼此间毫无嫌隙的信任。
这样的感情,应该是最最合适的吧。
当然这一切路一是不知道的。他只知道我有个朋友要跟着我们一起去看看这个废弃的食品加工厂,至于别的情况,我不说他也不会问。
路一向来不是好奇心泛滥的人。
脑海里翻来覆去想着这些事,不知道过了多久才迷迷糊糊有了睡意。电话铃突兀地响起来时,我还以为到了该起床的时间,谁知抓过手机一看,却是一个陌生号码打进来的电话。抬头瞥一眼床头柜上的小座钟,指针的位置还不到凌晨四点,睡眠不好的人,夜里一旦被触动就很难再睡得着了。我也是这样,从床上坐起来的时候,我已经完全清醒了过来。
“喂?哪位?”
电话的另一端十分安静,我甚至听不到呼吸的声音。正疑惑时,话筒里传来嘀的一声轻响,像是某种电子仪器发出的声音,电子仪器、检测设备、医院、研究所……我的思路飞快地将这几个名词串在了一起,一时间毛骨悚然。
“殷茉,是我。”女人的声音,低沉而疲倦,带着浓重的鼻音, “好久不见了。”
这是我不曾期望过的声音。那些我不愿意去回想的过往,在这一刻,都随着她的声音在这暗夜里苏醒了。我嘴里发苦,一时间竟不知该做出怎样的反应才好,想耍按下挂机按钮的同时又矛盾地想知道她会带来什么样的消息。
在我的心目中,她一直都是温厚的长者,优雅沉静,令人信服。不知何时,这感觉已经变成了犯人家属面对狱卒时的不知所措。
“我打这个电话,是想求你一件事,”也许是见我始终没有要开口说话的意思,米娅叹息着开口了,“我不敢说什么求你原谅的话,不过,对不起你的人始终都是我,严德……他从来没有做过对不起你的事。”
我想起那个船舱里的网筐,那些用在自己身上的神秘药剂,想起上岸之后他们对我的照顾,想起他打着雨伞把我送到车旁时关切的眼神……尽管在我的心目中从来没有把他们看做是分开的两部分,但我仍然不得不承认米娅的说法,严德从来没有做过对不起我的事。
“如果可以的话,我想请你来丁香公寓看看他。”有一些莫名的东西被压抑在她的声音里,像勉强忍耐的呜咽,将我心底里那一丝不祥的预感瞬间放大。
“他……”
“大概就在这两天了。”
我的脑子里嗡的一声响。
“他想见见你。殷茉。”
黄昏时分,就在路一打来电话说他已经带着“我的朋友”考察完毕顺利返回市区的同一时间,我也站在了丁香公寓的大门外。
这个有着很乡土的名字的地方,从外表看,几乎和我第一次看到时一模一样。大门开着,种满了花花草草的院子依然显得生机盎然,沿墙栽种的一溜丁香树已经长到了墙头那么高,茂密的枝叶挨挨挤挤,把树后的砖墙遮挡得严严实实。树丛旁边的秋千在昏黄的光线里轻轻摇曳,像温情的女子不经意间流露出来的寂寞。
客厅的门敞开着,灯还没有亮起来,站在院子里只能看到门厅里的一角矮柜和矮柜上盆景的暗色剪影,硕大的一蓬草状植物,从昔着光的角度看过去活像一个人披头散发地站在那里。即使明知是自己的错觉,我的后背仍然爬上来一阵毛毛的感觉。
迈过院门之后我才注意到楼上卧房的窗户都开着,象牙色的窗纱微微拂动,窗纱后面是阳台苍白的墙壁和几茎细竹,我记得那是严德喜欢的植物,在船舱里的时候我就曾见过。没记错的话,那里应该就是严德和米娅的卧房。
我走上台阶,在大厅门口站了一会儿。
客厅里还是老样子,深色的木质家具搭配着象牙色的地毯,纯粹而又内敛的颜色折射出他们那个年纪的人所特有的优雅。虽然客厅里空无一人,可是空气里仍然残留着一丝温暖的东西,仿佛落霞满天,余晖脉脉,迷醉的感觉里混杂着黯然神伤。
即使我对这里的主人心怀芥蒂,仍然无法否认这里的确是一个令人感觉舒适的地方,就好像相爱的两个人之间那种令人心动的电波正由某个特殊的点均匀地辐射到房间的每一处角落。
我转回身望向楼梯的方向,米娅站在楼梯转弯的地方静静地看着我,也不知站了多久。她应该是在看我,但是视线却又仿佛从我的身上穿了过去,望向了旁人不知道的地方。微微有些出神的样子,眼底一抹掩饰不住的黯然。
“米娅。”她不说话,只好由我主动向她打招呼。
米娅的目光微微一跳,仿佛被惊动了似的将注意力重新集中在了我的脸上。她隔着半个客厅静静地注视着我,目光之中慢慢地浮起一丝纠结的神色。
“你真的来了。”她的声音略显沙哑,“我以为……”
“严德还好吗?”我打断了她的话。
“他一直在等你。”米娅并没有直接回答我的问题,说完这句话就率先朝楼上走去,我望着她的背影,忽然间有些迟疑。我其实并没有做好要见他们的准备,很有可能见了面也不过是听严德说一句对不起罢了。面对一个即将离世的人我又能说什么呢?这种想要求得谅解的情结我能理解,但是一句违心的“没关系”真的可以让他了无遗憾地离去?
一路行来,我的脑子里始终一片空白,可是到了要见面的时刻却反而变得纠结起来。深吸一口气,抬头看时,米娅已经伸手握住了卧房的扶手,正转过头来用一种略微有些担忧的目光看着我。
我想她也许是要叮嘱我一些需要注意的地方,可是等了几秒钟却始终没有听到她说什么。诧异地抬头看她,米娅却微微有些不自然地转过头,避开了我的视线。与此同时,她的手向下一压,象牙色的木门无声无息地在我面前推开了。
卧房给我的第一眼印象竟然是满目苍绿。门边、窗下、屋角……我数不过来这间卧房里到底摆放了多少细竹。仿佛不论身处房间的哪一个角落,随便一眼瞥过去都能看到一莲蓬醉人的绿。那个苍白桔槁的男人正闭着眼静静地躺在这一片绿色当中。几年不见,他的头发已经全白了,稀稀疏疏地铺散在浅色的枕头上,衬着他毫无血色的皮肤,看上去宛如茂密盆景中一块浅色的点缀,消瘦得几乎要被那大把大把的绿色吞没了。
几年前深海就说过他的年纪可能已有八十或九十岁了,可是看到他那张原本优雅而沧桑的脸如今消瘦得只剩下一层干枯褶皱的皮肤,要说他有八百岁我也会信。我从来都不知道人可以衰老得让旁人完全认不出他本来的样子。
“他每天这个时候都会睡一会儿,大概要再过几分钟才会醒来。”说完这句话房门便在我身后关上了。也许她只是不想参与我和严德的谈话,但是随着房门带起的那一缕微风拂过,我的后背却止不住有些发凉。我忽然有点怀疑床上的那个人是不是还在继续呼吸?那么苍白的样子,让人看了完全感觉不到一丝一毫的生命力。我甚至开始怀疑这个人真的是严德吗?
窗外传来一阵拍翅膀的声音,一只鸽子落在窗台上,歪着头朝房间里看了两眼又拍打着翅膀飞走了,洁白的双翼在夕阳下泛起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