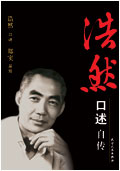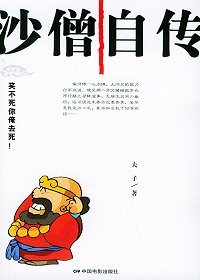甘地自传-第45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就不应当半途而废。
我写自传不是为了讨取批评家的欢心,写自传本身就是对于真理的一种体验。目的之一当然是给我的同事们提供一点安慰和回忆的材料。真的,我就是根据他们的愿望着手写作的。要不是捷朗达斯和史华密·阿难德坚持他们的意见,这本书也许就写不成了。所以假如我写这本自传是错误的,那他们也应当分担责难。
现在还是谈谈题目以内的事情吧。正如有很多印度人同我住在一起,象我的家人一样,我在杜尔班的时候,也有英国朋友同我住在一起。并不是所有同我住过的人都喜欢这样,但是我坚持要留他们住。我并不是在每件事情上都是聪明的,我也有一些痛苦的经验,包括印度人和欧洲人。我并不为这些经验感到遗憾。尽管我有过那些经验,尽管我时常引起朋友们的不便和不安,我却一直没有改变我的行为,而朋友们也很客气地同我相处。当我同陌生人来往而朋友们感到不快时,我就毫不犹豫地责备朋友们。我认为信奉上帝的人要想在别人身上也看见体现在他们身上的同一个上帝,必须有足够的超然之情去和别人共同生活。同别人一起生活的能力是可以培养的,不是回避这种交往的难得的机会,而是用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来欢迎这种交往,这样才能使自己不受到有无机会的影响。
所以波耳战争爆发的时候,我的屋子虽然已经住满了人,我还是接待了两个来自约翰内斯堡的英国人。他们都是通神学者,其中有一位就是吉特庆先生,关于他以后我们还有机会多谈一些。这些朋友们常常弄得我的妻子眼泪纵横。不幸的是,因为我的缘故,她经受过很多这样的考验。英国朋友象家人一样亲密地同我住在一起,这还是第一次。我留学英国的时候虽然是住在英国人的家里,但是那时我是按照他们的生活方式生活的,多少有点象住在公寓里。现在情形颇为相反,这两位英国朋友成为我们家里的人,他们在许多方面都采用了印度人的生活方式,屋里的设备虽然都是西式的,内部的生活可以说主要是印度化的。我记得把他们当作家人看待确有过一些困难,但是我可以肯定地说,他们在我家里做到完全象住在自己家里一样,是不太为难的,这样的交往在约翰内斯堡就比在杜尔班多得多了。
第十二章 同欧洲人的亲密往来(下)
我在约翰内斯堡的时候,一度雇用过四人之多的印度职员,与其说他们是职员,倒不如说更象是我的儿子。然而即使这么多人,还不能满足我的工作需要,譬如说打字吧,没有它就不行,而我们当中,只有我一个人会打字。我教两个职员,但他们一直不合要求,因为他们的英文太差。其后有一个职员我想训练他当会计。我不能到纳塔耳去找人,因为没有入境证谁也不能到德兰士瓦来,而就我个人的方便来说,我是不愿意去求负责发证的官员的。
我简直是没有办法了。事情越堆越多,不管我怎样勤奋,似乎很难把业务上的和公众工作上的事务都应付过去。我很想延聘一个欧洲人来当职员,但是否有白种男女愿意给一个象我这样的有色人种做事,我没有把握。不过我决定试一试。我去找一个我所认识的打字机经纪人,请他帮我物色一个速记员。当时女速记员倒是有的,他答应给我找一个试试看。他遇到一个苏格兰女子,名叫狄克小姐,是刚刚从苏格兰来的。她并不反对自谋一种正当的生活,随便到哪里工作都可以,而且她需要工作。于是那个经纪人便叫她来见我。她当时就给我一个很好的印象。
“在印度人手下做事,你不嫌弃吗?”我问她。
“我不在乎,”这是她坚定的答复。
“你希望要多少薪水?”
“十七镑十先令是不是太多了?”
“不多,如果你能做我所需要的工作。你什么时候可以来?”
“现在也行,如果你愿意的话。”
我很高兴,马上口授信件让她打字。
不久,她同我的关系,就象一个女儿或妹妹一样,而不只是一个速记员。我对于她的工作,可以说找不到什么错处,我常常叫她经管数达几千英镑的巨款,还把账目交给她管理。她得到我完全的信任,但是事情也许不单单是这样,她甚至把自己内心的思想感情都告诉我。她把最后选定丈夫的事也拿来征求我的意见,我甚至还享有为她主婚的荣幸。狄克小姐成为麦克唐纳夫人以后,便不得不离开我的事务所,但是就在婚后,当我工作上实在搞不过来了,只要找她帮忙,她无不应命而来。
然而现在我需要找一个固定的速记员来代替他的工作,幸而我又找到了另一个女子。她就是史丽新小姐,是卡伦巴赤先生介绍给我的。关于卡伦巴赤先生,我们以后还要谈到。她现在是德兰士瓦一个中学的教员。她到我这里来的时候,大约只有十七岁。她有一点古怪的脾气,有时卡伦巴赤先生和我都受不了。要说她是来当速记员,倒不如说她是来找经验的。她禀性中缺乏那种对于有色人种的歧视。她对于年龄和经验似乎都满不在乎。甚至当面侮辱一个人,当面斥责人,她也毫不犹豫。她的粗暴常常陷我于困境,但是她的坦白率真的性情往往就把因此而引起的问题消除了。她打的信,我常常是不加核对就签发了,因为我觉得她的英文比我的好,而且对她的忠诚有最充分的信任。
她富有牺牲精神,有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她所得不过六英镑,从来不肯接受一个月多于十英镑的薪水。每逢我劝她多拿一些工资的时候,她总是怪我说:“我不是到这里来向你要薪水的。我来这里是因为我喜欢同你一起做事,我喜欢你的理想。”
有一次她向我支取四十英镑,可是她一定要算是借款,而且去年把这笔钱全部清还了。她的勇气也和她的牺牲精神一样大。我生平有幸遇见过几个这样的妇女,其品格象水晶一般的莹洁,其胆识可以使战士失色;她便是其中的一个。她现在已经长大成人了。她现在是怎样一个人,我已不象从前那么清楚了,但是我同这位青年女子的接触,却永远是我的一个神圣的回忆。因此我如果不把我所了解的关于她的为人说出来,那就对不起真理了。
她白天黑夜为运动操劳。她在黑夜的时候,独自一个人外出工作,若有人提议派人送她,她便生气地加以拒绝。成千上万的有胆量的印度人向她求教。在进行非暴力抵抗运动的那个期间,差不多所有的领导人都被抓进监牢里了,就亏她一个人领导这个运动。她经管着几千个人,处理无数的信件,手头还要管《印度舆论》周刊,但是她永不倦怠。
关于史丽新小姐的这类事情,我可以写个不完。不过我想引用戈克利对她的评价来结束这一章。戈克利认得我所有的同事。有很多人他是喜欢的,也常常夸奖他们。在所有的印度人和欧洲人的同事之中,他最推崇史丽新小姐。他说:“我很少遇见象史丽新小姐那样勇于牺牲、为人纯洁和无所恐惧的人。
在所有你的同事当中,在我看来她应当位居第一。“
第十三章 《印度舆论》
在我继续谈到同其他的欧洲人的亲密交往以前,我得先提两三件重要的事情。不过,我同其中一个人的接触,应该在这里马上谈一谈。狄克小姐的任命还不能满足我的工作上的需要,我需要更多的帮助,我在前几章提起过李琪先生,我同他很熟。他是一家商行的经理,他赞成我的建议,离开了那家商行到我这里来做事,因而大大地减轻了我的负担。
大约就在这个时候,马丹吉特先生来找我,提议创办《印度舆论》,征求我的意见。他已经开办了一所印刷厂,我赞成他的建议。这个刊物就在1904年创刊了,曼苏克拉尔·纳扎先生是第一任编辑,但是经营这个刊物的工作却必须由我来担负,事实上我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这个刊物上了。这倒不是因为曼苏克拉尔搞不了,他在印度办过许多报刊,但是只要我在那里,他便不肯为那错综复杂的南非问题写文章。他对于我的见解极其信任,因此便把社论一栏推给我担任。这个刊物一直到今天还是一个周刊,开头有古遮拉特文、印地文、泰米尔文和英文四种版本。不过我觉得泰米尔文和印地文版没有什么实际意义,它们并没有起应有的作用,因此我就把它们停了,免得给人一种欺诈的印象。
我原来并没有想到我自己会在这个刊物上花什么钱,但是不久我就发现,如果没有我的经济上的接济,继续出版是有困难的。印度人和欧洲人全都明白,我虽然不是《印度舆论》的正式编辑,实际上,经营管理是由我负责的。如果还没有创刊倒也不算什么,可是一旦已经出版,如果中途把它停下来,那就不但是一种损失,而且是一种耻辱。于是我不断地给予资助,一直到后来我的存款差不多花光了,我记得有一个时候,我每个月要汇出75英镑。
然而经过这几年以后,我觉得这个刊物对印度侨团是很有好处的。它从来就不是被当作一种商业性的事业。由于它一直是在我的管理之下,这个刊物的变迁就可以说明我自己生活的变迁。当年的《印度舆论》就象今天的《青年印度》和《新生活》一样,都是我的一部分生活的反映。一个星期接着一个星期,我把我的心灵都灌注到这个刊物的篇幅上去,就我的理解所及,宣扬非暴力抵抗运动的原理和实践。有它出版的十年之间,即到1914年,除了我在监牢中被迫休息曾有所间断以外,几乎每一期的《印度舆论》都有我的文章。这些文章,就我所记得的,没有一个字不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没有故意夸大,或专门讨好的东西。诚然,这个刊物已成为我锻炼自制的好园地,对于朋友们来说,即它是保持同我思想接触的一个媒介。
爱好吹毛求疵的批评家在里面也找不到什么可以非议的地方。事实上《印度舆论》的论调已迫使批评家们不得不抑制其笔锋。如果没有《印度舆论》,非暴力抵抗运动说不定就发动不起来。读者希望从这个刊物得悉非暴力抵抗运动的可靠情况,也想从那里知道南非印度人的真实情况。对我来说,这是我研究人类天性的各方面的一种手段,因为我一直想要在编者和读者之间建立一种亲密而正当的关系。我经常沉浸在读者许多真情流露的信件中。由于写信人的性情不同,来信有的是亲切的关怀,有的是严正的批评,也有的是痛诋。研究、消化和答复所有这些信件,对我是一种很好的教育。通过这些信件,我仿佛听见了侨团的声音。它使我完全懂得作为一个新闻工作者的责任,也因为我通过这个刊物抓住了侨团,使未来的运动能够见诸实行,而且具有那么尊严和无可抗拒的气概。
《印度舆论》出版的头一个月内,我便认识到新闻事业的唯一目的应该是服务。新闻报纸是一种伟大的力量,但是正如奔放的狂流能把田庐和庄稼荡然摧毁一样,一支不加控制的笔也能起毁坏作用。如果控制是来自外界的,那比没有控制更加有害。只有内在的监督,才能有益。如果这个说法是对的,那么世界上有多少报刊经得起这种考验?然而谁能制止那些没有用处的报刊呢?而且谁来当裁判?有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