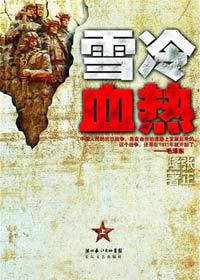雪冷血热-第148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李桂顺被皮鞭抽打得遍体鳞伤,仍然撬不开她的嘴。敌人把两颗人头扔在她面前,那是同时被俘的司务长老王和六十多岁的老战士老崔头,李桂顺昏了过去。敌人以为得计了,用凉水把她泼醒,这回她开口了,破口大骂这帮畜生。
无论敌人怎样用刑,崔姬淑只是冷笑,敌人受不了她那轻蔑的目光,把她的双眼抠了出来。她吐着嘴里的鲜血,说我心里亮堂,看得见你们的灭亡。敌人号叫着,又把她的心剜了出来。
1942年2月初,5军3师师长张镇华率领的一支小部队,在宝清炭窑山被敌包围。战至弹尽粮绝,官兵大都牺牲,身负重伤的师长和或枪伤或冻伤的6名女兵被俘。
从张镇华口中什么都没得到,敌人就把希望寄托在6个女兵身上。
首先被带上来的,是二十岁出头、长得挺结实的朱新玉。伪县长姓郭,亲自审讯,挺和气地让她坐下,问道:姑娘,你叫什么名字呀?朱新玉不理,一个汉奸大声道:你哑巴了?你们的队伍在哪里?
朱新玉道:有你们的地方,就有我们的队伍。
一顿皮鞭抡过,一个叫浅野的鬼子把战刀架在她的脖子上,一个汉奸又拿来一把烧得通红的烙铁。
无计可施后,又开始审讯刘英。刘英的丈夫,是3师8团团长费广兆,正在宝清活动,不久前设伏打死十几个日伪军。
伪县长问:你乐不乐意跟你的丈夫过好日子呀?
刘英道:那是在把你们这些东西消灭了以后。
浅野又把战刀架在刘英的脖子上:快快地说,费的在哪里?
刘英怒视着鬼子:他在俺的眼睛里,就在你眼前!
浅野号叫着:把她的眼睛挖出来!
民众的旗,血红的旗,
覆盖着战友的遗体,
遗体还没有僵硬,
鲜血已染透了旗帜。
唱着赵一曼就义时唱着的《红旗歌》,6个女兵走上刑场。
一个有别于八女投江的英雄群体。
“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
1938年4月初,由于出了叛徒,6军帽儿山四块石密营被偷袭。
这天是李敏的“饭班”,就是轮到她做饭。哨卡上枪声骤响时,这位6军最小的女兵,正在锅台前朝桶里舀饭。她愣了一下,随即更快地舀起来,直到快舀干了,才明白自己提不动那桶。那是只笨重的木桶,加上大半桶包米子粥,能有五十来斤。这时裴成春裴大姐赶过来,一手提桶,一手抓她,两个人爬过后窗,钻进林子里。
11月底,她们从四块石转移到张家窑附近,与敌遭遇。1师政治部主任徐光海,指挥10多个伤员向东山转移,裴成春带人阻击敌人。迫击炮弹在山坡上爆炸,李敏趴在雪地上,用支小马枪向敌人射击。打了半个来小时,东山方向突然枪声大作,显然那边也上去敌人了,而且火力更猛。这边子弹也快打光了,只得撤退。
5个女兵,裴成春在后边掩护,一个身强力壮的在前面开路。这年雪大,山沟里积雪没裆、齐胸。大个子女兵大张嘴巴,累得上气不接下气,李敏上前替她。手扒头拱,拼命向前,突然脚下一滑,那人就像坐了滑车似的飞了出去。
待她明白怎么回事,天色已经暗了下来。
这是山沟里一条河沟的河道,雪挺厚,这时的积雪还松软。冰面坡度不算大,沾点雪特别滑,一扒拱到冰面上,那人就下去了。石头、树棵子什么的,撞上几下,那人就昏过去了。
她不知道是怎么从雪堆里拱出来的,恍若梦境。风在林间呼叫,雪粒子一阵阵扑打在脸上,她感到一种透心的寒冷,意识就开始苏醒,想起刚才的战斗。她挣扎着爬出河道,向上走去。首先看到大个子女兵,最后是裴成春,横躺竖卧的,都牺牲了。还有两个人没了,后来得知是被俘了。她抱着裴大姐哭了个一塌糊涂,就向山顶爬去。
她想鸣枪,没子弹了,就开始“叫树”。人在山里迷路,或与同伴走散了,拿根腕口粗细的木棒,梆梆梆敲击树干,能传出很远,有人听见,就会以同样方式回应,叫“叫树”。叫了好一阵子,胳膊都震麻了,除了风吼没别的,就又燃起一堆火。她希望有人看到这火光,更希望哪儿也燃起这样的火光。她朝东山方向可着嗓子叫着,她不相信那么多人都牺牲了。风把她的声音和希望劫走了,隐约传来狼的嗥叫。
她把枪背好,拄根棍子,开始下山。
她知道,不论多大山,有条河,沿着河道就能走出大山。
上山容易下山难。不知跌了多少跟头,胳膊腿和身上都可用“鼻青脸肿”形容了。
太阳出来了,雪地上一个毛茸茸的东西一动不动,是只死老鼠。她踢了一下,冻得像块石头,就伸手捡起来——这是块肉呀!
狐狸、狍子、鹿、狼、羽毛艳丽的野鸡,两天里见得太多了。狍子有的离她就10多步远,傻呆呆地望着她。帽儿山密营被袭,牺牲几个人,李桂兰和夏军长的女儿负伤被俘,可还有很多人,有裴大姐。两年了,无论她怎样想在别人的眼里变成大人,身边的每个人都是她的依靠,只需跟着他们就行了。而现在,这个世界就剩她自己了,她感到从未有过的恐怖、无助、绝望。十四岁的女兵,觉得自己就像离开大海的一滴水,眼看就要蒸发了、消失了。
把死老鼠烧了吃了,腿脚有点儿劲了。
第一天晚上“行军”,第二天晚上在篝火边“宿营”,天亮了继续“行军”。肚子咕咕叫着,捡些榛柴叶子嚼着。看到脚印,就仔细端详一阵子,也留意树棵子上是否挂着棉絮、布条、布丝。不过这时已经很难辨认了,因为抗联官兵许多人穿的都是缴获的日伪军服装。
天黑了,她想找个背风的地方“宿营”,突然觉得有些异样,赶紧趴下。前面林子里传来踏雪声,一个山东口音挺重的人说:“同志们,起队。”
六十一年后,李敏老人说,改革开放后播香港电视剧,警匪片中警察都说“收队”、“起队”。我们那时就是“收队”、“起队”,不叫集合。想想这辈子,没有比那一声“同志们,起队”,再使我热血沸腾的了。
李敏、李在德这辈子最难忘怀的人之一,就是6军被服厂厂长裴成春了。
她是朝鲜庆尚北道人,1919年十二岁时随家人来到中国东北,“九一八”事变不久入党,1933年参加汤原游击队。中等个头,圆脸,大眼睛,脸上总是红扑扑的。姐姐漂亮,弟弟英俊,都是党员、老游击队员。大弟裴锡哲,1932年春到鹤岗煤矿组织工人暴动,夺矿警的枪,赶上瓦斯爆炸牺牲。二弟裴锡九,同年春打入一支山林队,准备将其改造成党的武装,被坏人杀害。三弟裴敬天——前面已经说过了。
一口流利的汉话,爽朗、热诚、稳重、干练,不知疲倦,没有能难倒她的事情。
或者被袭击,或者主动转移,6军被服厂几次搬迁,选址、建密营都是她张罗。从锯树开始的一整套建房程序,不但懂行,干起活来一般男人也没她利索。被服厂常为其他军做服装,因为6军被服厂的效率是有名的。她手脚不闲,却没有手忙脚乱的时候,总能把工作安排得井然有序。洗衣染布料,一双手皴裂开的口子,有的就像小孩嘴似的。送来一批伤员,被服厂随即转型为医院,她这位厂长就成了院长,还是护士、护理员。给重伤员擦屎擦尿,任何女性开头都难免迟疑,她上手就干。敌人来了,指挥战斗,她就是这支人员参差不齐的队伍的队长兼政委。
1938年4月,在帽儿山四块石,敌人来袭,裴成春把伤员转移隐蔽后,带个队员迎敌而去,两支枪把敌人引开了。
1938年后,更多的是履行医院职能、照料伤病员的被服厂,到处迁移、游动。露营“打火堆”,大家都睡了,她坐在火堆旁缝这补那。风向变了,或是谁凑得离火堆过近了,就把他往外拽拽。查完“铺”了,再去查哨。
朝鲜族妇女刻苦耐劳的坚忍精神,即便不是举世无双,也世所罕见。曾担任过区、县妇联领导和县委委员,只是在参加革命后学点文化的裴成春,还有一种与生俱来的领袖气度。
当年和今天,李在德和李敏一想起裴大姐,就会想到母亲。
赵尚志也叫她裴大姐,当然不仅是因为她比他大一岁。
张家窑战斗的最后时刻,李敏听见金碧蓉喊“没子弹了”,裴大姐厉声道:“别吵吵。”
母亲去世,一夜间李敏长成大人。裴大姐牺牲,李敏就觉得自己是老兵了。而从战争年代到“文化大革命”,每当她觉得快要挺不住了时,就会想起裴大姐。
1939年初,随3团一个连掩护20多伤病员在宝清县锅盔山活动的李敏,已经是个地地道道的老兵了,实实在在还是个小丫头。
一口大铁锅,劈锯成擀面杖粗细长短的桦木绊子,在沸水中咕嘟着腾腾的热气。春天在山里渴了,用刀在桦树上割道口子,汁水就流淌下来,清沁可口。或许就是这个原因,断粮了,就煮桦树绊子,叫“熬树胶”。苦涩不说,还有股说不出的味道。可人饿急眼了,望着那棕色的渐显黏稠的“树胶”,嗓子眼里就恨不能伸出个小巴掌。
不到二十岁的小刘说:今儿个是“几儿”(几号)了?该过年了吧?
四十多岁、和李敏同一天入党的苗司务长,扳着指头算来算去,一拍大腿:可不是咋的,今儿个是年三十呀。
有人就说,那得弄点儿“好嚼裹儿”呀?哪来的“好嚼裹儿”呀?小刘那抿裆裤的屁股上缝块老羊皮,早没毛了,献出来。苗司务长进地窨子里,又拎出只破牛皮乌拉,洗了剁了放锅里,空气中就有了股脚丫子味儿。
大年初一天快亮时,李敏去换岗。星星在天上眨眼,这是一天最冷的时候。哨位在丈把高的石砬子上,身后几棵一人粗细的油松,她将身子靠在树干上。不宜随意走动,走动影响听觉,夜岗主要靠听。真就听到下边有踏雪声,还有树枝折断声。是野兽?不像。谁?口令?就听下边猛跑起来,李敏“吧吧”就是两枪。
一个连就十几个人,还没伤病员多,又没连长。杜指导员说不能撤,地形有利,子弹有的是,打。当即部署战斗,轻伤员也操枪进入阵地。
山陡,老林子里积雪浅处及裆。敌人攻一阵子攻不动,躲在树后一露头,上边就是一枪。
天亮了,敌人少说百十多人,大都是伪军。大家就喊“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唱《劝伪军反正歌》。这帮伪军很顽固,打到中午未觉有冲天放枪的,枪打得也准,冲锋时那股凶悍劲儿甚至不亚于鬼子。开头大家只打鬼子,这下子就不分日伪了,有人甚至专打伪军。
10点多钟,敌人来了援军,炮兵也到了。阳光下,迫击炮弹像一只只老鸹从山下林子后面飞上来,在空中划着抛物线,随即地动山摇。轻重机枪子弹像把无形的扫帚迎面扫来,钻进树干的那种声音,用哪种象声词都难说准确。山陡雪深,攻击动作慢,就成了活靶子。可伪军都带着钢盔,半截身子埋在雪里,再毛着腰,钢盔就像盾牌似的把人都护住了。李敏就侧射,或者瞄准正面敌人钢盔前沿的雪地。
不断有人伤亡。旁边的苗司务长趴在那儿不动了,李敏抱起他的头,满脸是血,牺牲了。许排长是个老伤员,右腿迎面骨又打坏了,倚坐在树下,雪地上通红一片。李敏给他包扎,他说别管了,没用了。边说边举枪瞄准,一枪,又一枪。眼看包扎完了,许排长身子猛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