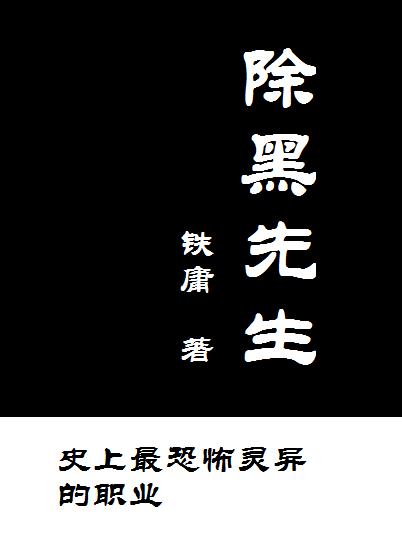灵异四人组-第39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不省心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四人组,万分感谢。。。
。。。。。。
。。。。。。
黎明时分。
东方的天际翻涌着成团灰蒙蒙的云朵,火红色的朝阳在云层中迟钝的穿梭,惨白而又温吞的阳光,一寸一寸照亮内华达州荒凉的戈壁。
这是一片不毛之地。
荒芜,干旱,到处是没有边际的石漠。
空气中偶尔流动起干燥的风,一丝丝气流无孔不入的灼烤着体内仅存的水分。
饥饿,口渴……喉咙如被生生撕裂,吐沫里都是干燥的泥沙……
“哈……哈……”嘶哑的喘息声,胸口剧烈起伏,胸腔里清晰回荡着心脏的震动,“砰——砰——”剧烈而又沉重。
**的脚踩进干涸的沙土里,再也使不出一丝力气。
单薄枯瘦的身体直直倒在沙坡上,脸颊埋进干燥的砂石里,心里发出一声叹息。
原来,自己竟是这样的结局……
风,轻轻吹动,吹动那一头凌乱的金发。
是出现幻觉了吗,风中,竟有一丝清凉的气息。
沉重的双眼缓缓抬起,如湖水般碧绿的眼珠,无神的远望。
就在眼前,跃过身下的沙坡。
在无边荒凉的戈壁之中,一抹生机勃勃的绿色,就像上帝赐予的奇迹,毫无征兆的,降临了……
……
洁白的浓密的睫毛轻轻抖了抖,像灵动的蝶翼,缓缓舒展。
一双墨绿色瑰丽的眼眸,安谧的,在沉寂的黑暗之中缓缓睁开。
黑暗是人为的。
硕大的落地窗,一帘厚重的黑天鹅绒窗帘阻挡了外界的光线。
刺目的阳光,透过窗帘织布微小的缝隙,顽强的钻进黑暗,在红色羊绒地毯上洒下微弱的光斑。
墨绿色的眼眸安静的适应着这种黑寂。
脑海中,梦醒前最后一幕的画面无比清晰的闪现在眼前。
那深深烙进了记忆的画面,无论多少年,好像即使死亡,也无法将它抹去。
这是最初的印象吗?最初的……拉斯维加斯……
身边微微一动,一个均匀的呼吸声响在身侧。
洁白的睫毛轻轻一抖,墨绿的瞳仁看到了身边安睡的像孩子一样的人。
“he/is/the/one?”(就是他?)黑暗中,一个低沉却好听的男性声音响起。
墨绿瞳仁猛地一缩!
视线透过浓密的黑暗,死死盯着暗处的某个身影。
“acacia;you/broke/the/rules。”(阿卡莎,你坏了规矩。)男子的声音透出责备,下一秒,一声布帛撕裂的“嗤啦——”声,黑天鹅绒的窗帘飞扬而起,刺目而温暖的阳光瞬间倾泻涌入房间!
“ah!!!”acacia一声尖叫,速度惊人的躲进房间的阴影里。
光明洒满房间,古欧式装潢的卧室,一桌一椅尽数暴露在明媚的阳光下。
在房间地面,红色的羊绒地毯上,站着一个高高瘦瘦的身影。
一头亚麻色微卷的短发,属于白人的苍白的皮肤。
高挺的鼻梁,英朗的眉骨,一双淡蓝色近乎透明的眼眸,纯净的仿若圣母王冠上举世无双的宝石。
男子手中,是扯下的半条垂地的黑天鹅绒窗帘。
他紧抿着薄薄的淡粉色双唇,高傲冷峻、不可一世的,沐浴在身后圣洁辉煌的阳光之中。
“dwight!”(德怀特!)碧眼女子藏在卧室门后,愤怒尖叫。
金发,碧眼,她正是昨晚赌场中,坐在虹泽对面的性感女郎。
被称作dwight的男子并不在乎acacia近乎警告的怒喊,他扔下窗帘,踱步来到**边。
织满金丝欧式花纹的松软的鹅绒**垫上,熟睡的人甚至没有被光线和尖叫声吵醒。
也许,是因为他不仅仅是熟睡。
dwight俯下身,那双蓝到近乎透明的眼眸,盯着**上那张毫无戒备的睡脸,戏谑而不屑的笑容浮在他薄薄的唇间。
dwight伸出手,指尖抚**上人的脖颈,指腹传来的黏腻感证实了自己的猜想。
“what’s/his/name?”(他叫什么名字?)他收回手,指腹上是刺目的猩红色液体。
“hongse。”acacia没好气的说道。
“i/hope/he/is/the/one/you’re/looking/for…”(我希望他就是你要找的那个人)dwight用系在手腕的白色丝绢擦净指尖的血液。
“care/about/yourself!”(关心你自己吧!)acacia瞥一眼那段丝绢,不服气的撅了撅嘴。
无所谓的笑容浮在脸上,dwight婆娑着手腕冰凉细滑的丝绢,透明的蓝眼睛再次落在**上,落在那张熟睡的安静的脸上……
……
aria酒店。
“你说什么?”**上身的骆安一手撑着**垫,另一只手揉着满脑袋乱蓬蓬的头发,半梦半醒的坐起来。
“虹泽,虹泽又丢了!”kik一脸都是担忧。
“……”骆安从蓬乱的头发间抬起一双极度不耐烦的双眼。
这帮人……早知道这样,当初就不该带他们一起跑。原本以为,躲过关注余家的媒体可以风平浪静,结果这帮人才是最大的麻烦……
“是不是又去赌场了,这小子玩不够啊……”骆安披上睡衣,抬起头冲kik挑挑眉毛,“我要掀被子了,你打算一直这么盯着我看?”
kik白他一眼,背过身继续道,“是晗姐觉察出不对,她说净化时感应到了一些不好的东西,追踪了一晚上,直到早上回酒店时,感觉不到虹泽的气场这才发现……”
“你说什么?”骆安一把掰过kik的肩膀,“那女人一晚上没睡就追那个不好的东西了?”
“是啊,谁像你这么没心没肺还能睡到这时候……”
“该死……”骆安推开kik,穿着睡衣冲出房间。
虹泽的房间,酒店管理人员安静的侯在门外,看样子,自己房间的门也是这帮家伙打开的。骆安撇撇嘴,冲进屋。
贺印那颗曝光过度的头晃得他眼前一亮,接着低头,就看到了跪坐在地板上双眼紧闭的钟姿晗。
**不睡,钟姿晗的气色很差,眼眶下是浓重的黑眼圈。
“di/fa/ro/fantas/lo//fa/e/mu/you/kaa/tee。。。。。。”钟姿晗念着古怪的语言,双手抚摸着地板,指间拂过的地面,几滴黑红色干涸的飞溅状痕迹触目惊心。
“发生什么事了?”骆安意识到,事情似乎有些超出预料。
贺印拧眉抬起头,冷淡的眉宇之间透出阴沉,“这次,恐怕是遇上麻烦的东西了。”
☆、这是哪?
“唔……”头疼……
动一动手指,麻木的四肢几乎不听使唤。
眼珠缓缓转动,混沌的意识飘忽不定,全身的知觉似乎还游离在深沉的梦境之中。
虹泽努力的抬起沉重的眼皮,眼前,是一朵盛开的,美到让人窒息的花朵。
繁复夸张的花瓣,刺目而又张狂的颜色,这是什么花呢?
虹泽搜索着自己二十年的记忆。
……是自己……从没见过的花朵……
难道又是老头带回的古怪东西?这个老不死的,真是……
“臭小子,你敢把我扔下飞机,小王八蛋@#¥%…………”一只炸毛的黄鼠狼蹦进脑海。
对了,这不是在山洞,我已经下山了,老头子也不在这里。骆安说,这里叫……老死、喂噶死?(lasvegas虹泽听不懂英文……)
我已经出国了,还住进一间好大的酒店……还赢了好多钱……还……
一双血红色的眼睛猛然闯进脑海,接着脖子一阵刺痛……是真的痛……
骆安伸手摸了摸脖子,一阵冰凉凉的濡湿,抬起手,掌心是触目惊心的猩红色!
“啊啊啊啊啊!!!”虹泽一个鲤鱼打挺坐起来,全身的意识瞬间归位,“怎么回事,是我的血吗,不是吧,可是脖子好疼……”
咋咋呼呼的虹泽突然噤声,因为他发现自己躺在一张陌生的床上,还是在一间陌生的屋子里,眼前,还有一个陌生的外国男人……
“哈……喽?”虹泽摆摆手,那个男子眼睛一眨不眨的看着自己,不过他的眼睛,好蓝,是瞎子么?
男子眨眨眼,一言不发。
“哈哈哈……”虹泽尴尬的干笑两声,掀开被子下床。
脚接触到地面,头突然一阵眩晕。
怎么回事,昨晚睡太晚了?
“那个……”虹泽晃晃悠悠站稳身子,“这是哪里……”
男子继续沉默,只是薄薄的唇瓣噙出一丝笑意。这笑容虹泽太熟悉了,简直和老头子抓鸡时的表情如出一辙。
强烈的不安感油然而生,虹泽注视着那双几乎能迷惑人心的蓝色眼珠,右手偷偷背在身后,捏起护身诀。
“你到底是……”身体稍稍一动,整个头就翻江倒海般的眩晕,视线开始摇晃。
虹泽大惊失色,心中的不安感强烈。
“三圣法,护!”意识游离前,虹泽一声大吼,接着眼前骤然一暗。
可他还是看到了,看到那双透彻的蓝眼珠在一瞬间,血红狰狞!
虹泽整个人仰天倒地,微弱的视线里,镂刻在屋顶的巨大华美的花朵,像一个漩涡,将他的意识,一点点撕碎,再慢慢吞没……
……
aria酒店,虹泽房间。
贺印三人围在钟姿晗身边,安静的等待,希望她能找到虹泽的下落。
“la/ta/re/nos/tee/fa//ammu/li/ji/ke/xiu……”钟姿晗跪在房间地面,双手快速摩擦着地面干涸的血迹,这样的状态,已经持续了将近半个小时。
“她在说什么?”骆安看着钟姿晗苍白的脸,烦躁的在屋子中走动,时不时停下来问东问西。
“就告诉你这是巫语了,我也听不懂。还有你能不能找个地方坐下来,你的样子很不安……”kik白一眼骆安,扭头不再理他。
“谁不安了?我是想说,这都什么年代了,还靠巫术找人,你看看她……”骆安皱眉看着钟姿晗,那张脸几乎快没有血色了,“半个小时了都没结果,你干脆叫醒她算了……”
房间外的管理人员也时不时的往屋里望一望,贺印只说有人不见了,那需不需要报警呢?几个人面面相觑,只能继续候着等消息。
“a/re/waa/tuli/far/a//mo/si/li/tee/fans/tu/ka……”钟姿晗的声音猛地尖锐,抚摸血迹的手指指腹突然裂开了一道口子,鲜红的血滴落在地板上,贺印三人吓了一跳。
“晗姐!”“姿晗!!!”“快停下!!!”
三人大惊失色,kik摇晃着钟姿晗的肩膀,却不能阻止她分毫,流血的手指在地板上快速移动。
“等一等!”贺印突然大声阻止kik,“你看她在画什么!”
鲜红的血迹在地板上一层层勾勒,骆安突然睁大双眼,“该死,是他们!”
“你认识?”贺印和kik的视线落在骆安紧皱双眉,严肃阴沉的面孔上。
骆安盯着那个图案沉默半晌,终于咬牙,“是鸢尾花,鸢尾家族的人。”
☆、鸢尾家族1
十五年前。
印度达哈维贫民窟。
午后的阳光烦躁而焦灼,如滚烫的油滋滋煎烤着这块贫瘠的土地。
耀眼的阳光,带着仿若上帝的仁慈和平等,将每一缕光线挥洒在达哈维每一寸被垃圾覆盖的土地上。
恶臭随风而来,千千万万种腐烂的气息混合在一起,无数臭蝇迎着这股风翩翩起舞,旋转,腾跃,就好像是世界上最华丽的华尔兹。
垃圾堆成的山,两只浑身长满癞的小狗嬉闹着,从这个山头,追逐到那个山头,然后,突然逃窜。
一个浑身*的小男孩手持着木棍追打着出现在山头,他冲着小狗逃走的方向示威的挥舞着木棍,然后吐了口吐沫,得意洋洋的走下山坡。
跟随着他的身影,在垃圾堆的中央,看到了十七八个年龄不等的孩子。
他们围在一起,商议着,讨论着。
难以置信,这里,正进行着一场交易。
破旧的瓷碗里装满揉成一团的肮脏的纸币和无数枚闪着金属光泽的硬币。
所有的孩子都紧紧盯着那只碗,只除了一个男孩。
男孩约有十二三岁,不是孩子里最年长的,看起来也不是最厉害的。
可是在所有孩子困惑、紧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