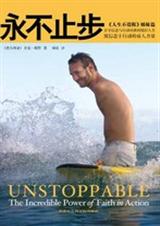天谴行动:以色列针对"慕尼黑惨案"的复仇-第21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在追他们。
“东西都捡到了?”阿弗纳爬进货车时问罗伯特。罗伯特点点头,但表情有点暖昧。他把贝雷塔放起来后不停地拍着衣袋,好像在找什么东西。阿弗纳决定不闻不问。不管罗伯特掉了什么东西,卡尔也许现在正在向袭击现场走去可以随后找回来。这是他的工作。
此后再也没有人说话。那个有些年纪的意大利人驾驶着货车,中速行驶着。他像其他意大利人一样,不知道在给谁开车,为什么开车。在货车的后面,有一些园艺工具在丁当作响。在仪表盘上有一张小小的圣母马利亚雕像。阿弗纳、斯蒂夫和罗伯特跳进货车时,他连看都没有看他们一眼。
大约二十分钟之后,货车开进了罗马南部一个像是石匠的院子里。货车停下来时阿弗纳又感到紧张了。他和罗伯特在绿色“菲亚特”上就把新弹夹装上去了。汉斯和斯蒂夫也武装起来了。他们这时是这次任务中最易受到攻击的时候。命运完全掌握在那些人手里。除了知道那些人不是自己的同胞之外,其他的他们都一无所知。
货车放下他们之后就开走了,他们站在一片松软的沙地上,前面是一些低矮的棚子,里面全是还未完工的墓碑。不远处是一片开阔地,两部小型“菲亚特”停在那里,互成直角。第二辆车里的司机正在抽烟。黑暗中阿弗纳能看见他香烟上的红光。
他们向那两部汽车走去时,本能地呈扇形散开。阿弗纳走得很慢,大约离汉斯十英尺的距离。此时在他大脑里一闪而过的是,“零风险”的概念真的是一个拙劣的笑话。这个概念当然也适合此时此刻的他们。
另一方面,他们的第一个活已经大功告成。
小小的“菲亚特”发动起来。斯蒂夫和罗伯特已经上了第一辆。第二辆车上的司机掐灭烟头,给阿弗纳和汉斯打开车门。无论要发生什么,都不会在这里,或者在这个时候。
出城之后,两部车子向南面那不勒斯的方向开去。阿弗纳看见他们没有走高速干线索尔高速公路而是走了一条较小较不重要的公路。他看了一眼路标。他们在一百四十八号公路上,正向拉提那小镇开去。
无论是汉斯还是阿弗纳都没有说话。阿弗纳在忙着从后视镜里看后面的灯光,确信另一辆“菲亚特”跟在后面。后来,汉斯打破了沉默。
“呃这是第一个,”他用希伯来语说。“你们想知道花了多少钱吗?”
阿弗纳突然觉得,汉斯看起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像一支铅笔。
“大约,”汉斯说。“三十五万。”
第六章 “集团”
拉提那郊外静悄悄的农舍是一个可以坐下来沉思几天的好地方。10月末的天空几乎没有一丝云彩。走在后院里矮矮的杏树之间,阿弗纳闻到了大海的味道。如果他多走几步的话,还可以看到大海。但为了安全,还是不要离开屋子。拉提那不是罗马。在小地方,陌生人也许会招来令人讨厌的关注。
汉斯在车上提到的那个数字他并不感到吃惊。事实证明,杀人是一桩昂贵的生意。阿弗纳试图记住这些钱去了哪里。这是一种将注意力集中到过去三周以来的活动上的练习。
第一个五万很容易想起来,给了安德雷斯。很大的一笔钱,没有交换到什么实质的东西。
在日内瓦的最初几天里,阿弗纳和他的伙伴们没有想过怎样开始执行这项任务。伊弗里姆说他们完全是独立的,这是非常有道理的。他们都同意他们应该独立,自己给自己确定任务,而不是靠特拉维夫的一些人拍脑袋,让他们白费劲。他们不应该被繁文缛节所累,被互相矛盾的指令所累。理论上,这很不错。
在实践中,在最初的两天里,他们在日内瓦的一家咖啡馆里阴沉地一连坐了好几个小时,一边往有坚硬外壳的瑞士卷饼上涂黄油,一边看着雨水从人字形的屋顶上快速落下来。对阿弗纳来说,最糟糕的事情就是他还不知道从哪里下手,而其他人却在等着他发话,因为他是领导。
最后,他从那份目标名单人手。实际上,伊弗里姆的那十一个恶人头子他们到底了解多少呢?这份名单是“穆萨德”按照从重要到不太重要的次序排列的。所以当阿弗纳和卡尔发现瓦地·哈达德博士在名单上处于最不重要的位置时,阿弗纳和卡尔都感到惊讶。他是最为声名狼藉的。当然,他们也不会按照名单上的顺序去寻找目标。浪费几个月时间去追寻一个恐怖分子而错过鼻子底下的三四个,这样做没有意义。
名单也可以按照另外一种方法来分类。一号、二号、六号、七号、八号、十号和十一号,用阿弗纳和他的同伴们更喜欢使用的准军事化的说法,就是“硬”目标。萨拉米、阿布·达乌德、纳塞尔、阿德宛、纳杰尔、阿尔一契尔和哈达德博士是公开的,承认自己是武装革命的领导人和组织者,他们的所作所为众所周知只是不知道他们目前的下落。他们即使微服旅行也随身带着武器,受到贴身保镖的保护。他们处处小心,避免被查出来或者落入别人的圈套。他们不仅要提防以色列敌人,而且还要提防“武装斗争”中不同派系的革命者。他们非常警惕,随时改变行程。有些人如果在同一间房里过两夜就绝对睡不看觉。
三号、四号、五号和九号是软目标。像罗马的威尔·兹威特、汉姆沙里、阿尔一库拜斯,甚至布迪亚也许主要或只有依靠自己掩护自己。他们公开地生活在西欧的一些城市里。在别人眼里,他们只参与跟他们的政治信念相符的教育、文化或外交活动。如果他们于过偷偷摸摸的勾当,那也只是前半生的事。在法国、德国或意大利,只有事后才知道,有些警察曾经是恐怖分子、枪支走私者或弹药走私者要是把他们赶出国门多好在西方国家,写文章支持一项事业或建立一个支持一项事业的信息中心都不是犯罪。
正如伊弗里姆曾对阿弗纳所说,“你不会因为一个人认为巴勒斯坦人应该有个家,就去袭击他。该死,我也认为巴勒斯坦人应该有个家。你袭击他是因为他炸死了孩子或者奥林匹克运动员。”
因此,软目标的安全警惕性就差一些。事实上,有一个目标现在在巴黎的地址里也包含着他全部的生平资料。这并不是说突击队未经任何准备就能暗杀他们。确实,无论计划干掉的那个人有多“软”,正是准备工作,特别是逃离的时候是最难的。后勤方面的工作也很多。
而且,干掉软目标要容易一些。至少容易找到,一旦找到,也不需要杀出一条血路来才能干掉他。
“软”目标被认错的可能性也小一些。跟“硬”目标不一样,长期掩盖得很好的恐怖分子没有理由自找麻烦地去伪装或换身份。他们让人拍照,甚至让别人把自己的名牌挂在门上,如果别人要问的话,他们还会介绍自己。对于这些人不可能搞错。除非“穆萨德”总部搞错,说他们千真万确是自己描述的那些人。
首先选中软目标还有一个原因。慕尼黑惨案是9月初发生的。硬目标也许藏着几个月不会出来。几个月之后等全世界把对奥林匹克队员的杀戮忘了,他们才会出来。如果那时他们干掉了其中一个恐怖分子,找到另一个也许又要几个月时间。到那时,公众的舆论,甚至恐怖头子们自己在情感上都不能把那次杀戮和自己被杀联系起来了。暗杀别人会让人觉得毫无理由。拜伦勋爵的“复仇是一盘菜,最好等冷却下来再吃”的论断阿弗纳并不知道。如果知道的话,他也不敢苟同。
“真该死。”第二天又是个雨天。那天中午,阿弗纳对他们说:“我们忘掉日内瓦吧,太安静了。这里连联络人都没有。把总部设在法兰克福吧。我们首先散开,去银行开账户,收集新闻,各自去自己最熟悉的地方。”
“斯蒂夫,你去阿姆斯特丹。卡尔,你明天去罗马。汉斯去巴黎,罗伯特去布鲁塞尔。五天后我在法兰克福跟你们会合。”
“让我们两周之内干掉第一个恐怖头子。”
这番话听起来有些冲动,但却有道理。很显然,在欧洲的主要城市里,他们需要有银行账户、联络人、加锁的抽屉和安全屋。目标今天可能在这里,明天可能在那里,万一有行动,他们要有逃跑的路线和藏身之所。理想地说,在欧洲不同的城市应该有不同的护照和不同的身份等着他们。当然还要有钱,让他们能够维持一两个星期。绝对不能在一个国家突袭之后用入境时的同一身份离开这个国家。绝对不能带着自己的武器跨越国境。至少,如果他们作了充分准备的话,他们不必这样做。他们甚至不必同时携带两套不同的身份证件。
卡尔过去常常以罗马为家,汉斯以巴黎为家,斯蒂夫以阿姆斯特丹为家。他们以前的线人跟普通警察工作一样,五分之四的情报来自心存不满或者贪婪的线人也许听说过一个目标或其他目标的传闻。至于罗伯特的目的地布鲁塞尔,那里仍然是世界上走私弹药和武器的主要中心之一。阿弗纳对专业术语知之不多这是罗伯特的专业但这也是常识,只要你人用得当,钱用得当,你就能从一个比利时商贩那里搞到相当数量的军火,而且可以把它发往西欧各地,甚至更远的地方。
他的伙伴们离开之后,阿弗纳从日内瓦咖啡吧外面的公用电话亭,花了五万块给安德雷斯打了一个电话。
这个电话是他的第六感觉促使他打的。伊弗里姆说的话已经根植于阿弗纳的脑海之中,就是要打人恐怖组织的网络之中。一箭双雕。毕竟,阿弗纳和他的突击队现在只是一个极小的严密的组织,就像许多地下国际恐怖组织一样。他们跟任何政府都没有官方的联系。他们不受任何提供秘密服务的程序与规则上的约束。他们是独立的。他们是在为一个国家工作但又不是。
伴随着动荡不安的20世纪60年代声势浩大的毒品—文化—反击—越南—战争—环保主义—女权主义一新左翼运动,大批无政府主义武装分子涌现出来。在这方面,他们与那些一伙一伙的自发的无政府主义武装分子并没什么两样。这些恐怖分子也是在为一个国家工作。但是1972年,很少有人作这样的联想。
为什么直到20世纪70年代西方国家的多数自由评论家和政治家才去这样联想,原因很多。首先,在20世纪60年代,在某些情况下,人们对恐怖分子拥护的许多事业和观念给予了巨大的、并不是不应当的同情。尽管绝大多数西方人并不同情恐怖分子采用的方法或“策略”蓄意谋杀、抢劫、劫机和绑架许多人容易把狂热的暴力分子看作是把当代优秀思潮不幸推向极端的一些不太稳定、不太成熟的个体。
第二,某国总是在其政府公告中谴责或者至少是不欢迎多数形式的恐怖主义。该国外交部长在一次大会上说,“某些恐怖行为导致了慕尼黑悲剧的发生,这是不能原谅的。”从事该国政策研究的专家们基于某些理由指出,一直以来,无政府主义者与正统的共产主义者之间存在着一条鸿沟。后者把前者看作是“小资产阶级浪漫主义者”,“客观上”对“无产阶级的胜利”只有阻碍作用。事实上,一些恐怖集团有时候也在公共场合表达他们对“帝国主义”和“西方殖民主义”的反对尽管在情感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