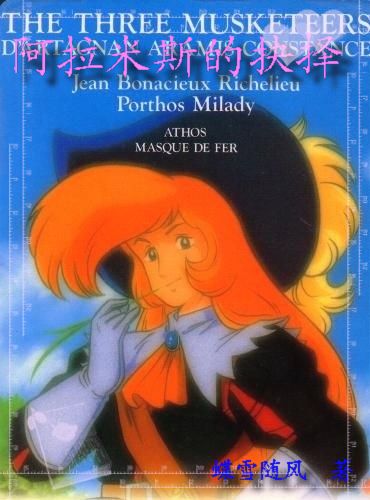阿拉桑雄狮-第42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就谡馐奔淠痰囊凰玻崤岛鋈恢轿椎哪敲锉反骼鲜酵房ド匣姑扛霾杂サ袷巍?
他认得这个标志。所有埃斯普拉纳的战士都认得这顶头盔和戴头盔的人。不敢置信的感觉重重压在尼诺心头,令他四肢麻痹。他只觉天道不公,心中冰冷彻骨。他眼见头顶鹰盔的骑士径直冲向自己,连忙举起手中长剑。尼诺佯攻一招,然后挥剑猛砍敌人肋腹。这次攻击被轻易化解,在他收招之前,就见一柄明亮长剑迎面飞来。尼诺·迪·卡雷拉从此离开人世,坠入黑暗之中。
伊达在父亲身边战斗,一直想鼓起勇气,提出撤退的建议。
明明是一次失败的伏击,父亲居然还坚持了这么久。他们的名声,他们的财富,和他们在亚巴斯特罗的城池,都是建立在—个准则上:知道何时应当作战,何时——比方说现在!——应当撤退,择日再来。
伊达在束手束脚的压迫下挥剑拼杀,他心里明白,肯定是因为兄弟的伤势。阿比尔躺在他们身后的坚硬地面上,只剩下最后一口气。父亲满心悲愤,已经丧失理智。一名匪帮成员守在阿比尔身边,跪在地上抱着他的脑袋,还有另外两人左右侍立,以防有任何该诅咒的贾德人从密集圆阵冲杀出来。
父亲在伊达身边,化作一固狂野骇人的身影,发疯似的攻击敌军阵列,完全不顾眼前局势,也不在乎半数以上的同伴已经牺牲。他们现在只有三十人出头,与那些吃屎的马民几乎数量相当。他们的武器和盔甲不如对方,战斗方式也不适合——从来都不适合这种野蛮的正面交锋。
这次埋伏几乎成功,但毕竟功亏一箦。现在应该脱离战场,向南方撤退,接受苦涩的现实:一场大冒险几乎成功,但到底还是没有成功。他们在返回亚巴斯特罗的家园之前,要走的路长得要命,又是在险恶冬季,顶着冷雨,踩着软泥,还有伤员拖慢速度。现在想全身而退已经晚了,但至少有些人还能活下来。
就好像是为了证明他的想法,伊达突然被迫矮身侧移。一名壮硕的贾德人擎着钉头锤逼上前来,挥手侧击砸向他的面门。贾德人从头顶到小腿都覆盖着铠甲,伊达只戴了一顶皮盔,身穿轻型锁子甲。他们干吗要正面搏杀?
伊达拧身躲过致命锤击,猛地砍向贾德人的脚后跟。他感到长剑穿过靴子,切入血肉。那人惨叫一声,单膝跪倒在地。伊达知道,他们会说这是懦夫的手段。但贾德人有盔甲和利剑。亚巴斯特罗人则有几十年来的丰富经验,熟谙诡诈和诱捕的手段。事关生死,就没有什么规则。父亲打—开始便将这番道理灌输给他们。
伊达在摔倒的巨人脖子上一划,割入头盔和胸甲间的缝隙。他想过是否要捡起钉锤,但又觉得太沉,不适合自己,特别是等到必须逃跑的时候。
他们现茌就必须逃跑,不然迟早要死在隘口里。他看了眼父亲,老人依旧在怒火驱动下疯狂攻击,不断挥剑猛砸一名贾德人的盾牌。那人一步步向后撤去,但持盾的左臂稳稳当当,韧性十足。伊达的目光越过父亲,看到了贾德队长——金发男子又打发了他的一名同伴。他们早晚要死在这里。
正在此时,第二拨贾德人从他们身后冲了进来,马蹄声响彻隘口。
伊达惊得猛一转身。太迟了。他的脑海中出现了栩栩如生的幻象,一名黑发白面的少女朝他扑来,长指甲戳向他血红的心脏。但就在顷刻之间,伊达忽然发现自己根本不明白今天在隘口中发生的—切。
第二拨骑兵的首领越过匪帮阵线,笔直冲向挥舞重剑的金发贾德人。他坐在马鞍上,身子微微前倾,挡住对手的攻击,双腿紧紧夹住坐骑,以大师级的精准动作挥剑下斩,将金发贾洛纳人立毙当场。
伊达发觉自己嘴巴张得老大,赶紧合上。他绝望地看向父亲那充满悲伤和愤怒的血红身影,结果发现老人突然恢复了此刻亟需的理智。
“咱们被利用了。”父亲随后对他说道,在新骑兵带来的腥风血雨和奄奄一息的伤者之中显得异常宁静。他放下手中长剑,“我真是老煳涂了。这把年纪已经不该再带领队伍。我早就应当入土了。”
谁也没料到他突然还剑入鞘,退后两步,似乎超然物外。新来的贾德人把头一批骑兵通通杀死,毫不手软,绝不留情,即便围在金子周围的那些人已经扔掉佩剑,高声叫嚷着愿意赎身,他们的投降都未被接受。伊达这辈子杀过不少人,但面对此情此景,也只能和父亲撤到垂死的兄弟身边,站在原地静静观瞧。
那些贾洛纳人一路南行只为攫取菲巴兹的财富。他们愚蠢地闯进陷阱,却又靠勇气和纪律撑了过来。可到头来,他们还是死在这天上午,所有人都没能走出黑暗隘口。
周围渐渐安静下来,只剩下受伤的匪徒兀自呻吟。伊达发觉新到的贾德弓手正在射杀受伤的马匹,所以才会显得这么安静。畜生的惨叫已然持续很久,他几乎意识不到那种噪音。伊达眼见完好的马匹都被赶到一起。这些都是精壮牡马,阿拉桑的坐骑没法跟埃斯普拉纳牧场的宝马良驹相提并论。
伊达、父亲和其他人早就按照命令扔掉武器。现在没有必要抵抗。他们只剩下二十多人,全都精疲力竭,多数受了伤,而且面对五十名骑兵也无路可逃。阿比尔还躺在他们身边,脑袋枕在一块叠好的布料上,呼吸断断续续,显然在应付疼痛。伊达看到他大腿的伤口很深,尽管腿上扎了止血带,但依旧血流不止。伊达以前也见过这种伤口。他弟弟早晚要死。伊达产生了一种空虚麻木的感觉,无法正常思考。他陡然记起新一拨骑兵出现时看到的那个幻象:化作少女的死神,手指抓挠他的生命。
到头来却不是他的生命。伊达跪下身,碰了碰弟弟的面颊。他发现自己说不出话。阿比尔抬头看眼哥哥,举起一只手来,碰了碰他的指头。弟弟眼中充满恐惧,但什么也没说。伊达使劲咽了口唾沫,现在不是哭的时候,他们还在战场上。他捏了捏弟弟的手,随后站起身来。伊达往回走了两步,来到父亲身边。老人沾满血污的脑袋抬得很高,背挺得笔直,仰头注视着刚来的骑兵。
亚巴斯特罗的塔里夫·伊本·哈桑,在将近四十年后络于被人捉住。
在西尔威尼斯垮台后,这个老匪徒变得比数不清的僭主更像国王,也更像一头雄狮。
伊达的麻木感也延伸至此。他们的世界将在这座峡谷终结。新的传说将同老故事一起,萦绕在艾敏·哈纳扎周围。他父亲没有任何表情。三十多年来,一连串哈里发和半打阿拉桑的小君主,都誓言要将他的手指脚趾一一割掉,然后才会将他处死。
第二拨骑兵的两位首领跨坐在马背上,低头看着老人。他们镇定自若,似乎对这个重大转变毫不在意。他们的武器都已入鞘,其中一个是亚夏人,另一个则跟骑兵一样是贾德人。那个北方人头戴老式铁盔,顶上有个青铜鹰饰。伊达不认识他们。
父亲没等对方发话,便说道:“你们是拉寇萨的佣兵。是金达斯人马祖·本·雅夫兰谋划了这一切。”这话并不是问句。
那两个人对视一眼。伊达发现他们脸上隐隐有些笑意,但他现在心里空落落的,根本发不出火。阿比尔只剩一口气了。他自己浑身酸软,脑袋在惨叫声平息后的寂静中阵阵抽痛,但最疼的还是他的心。
亚夏人操着宫廷腔说道:“一定程度的自尊心,要求我们也分享部分荣誉,但你的主要推论没错:我们来自拉寇萨。”
“你们故意放出风声,让我们知道岁贡的消息,引诱我们北行。”塔里夫平心静气地说。伊达眨了眨眼。
“这点也说对了。”
“还有山坡上的女人 ?'…'”伊达突然问道,“也是你们的人 ?'…'”父亲看了他一眼。
“她随我们一道出征,”面白无须的亚夏人说道,他耳朵上戴了个珍珠耳饰,“是我们的医师,同为金达斯人。这个民族真是聪慧过人,不是吗?”
伊达眉头紧锁,“那不是她的主意。”
贾德人说:“没错,是我们的点子。我想这样做有助于分散迪,卡雷拉的注意力。—些埃斯查卢的流言传到了我们的耳朵里。”
伊达突然想通了,“是你把贾洛纳人赶过来的!他以为你们跟我们是—伙的,要不然绝不可能闯进陷阱。他们派了斥侯,我看见了。他们知道这儿有埋伏!”
贾德人抬起右手,捋了捋胡须,“又猜对了。你们的陷阱设置得不错,但迪·卡雷拉是个——曾经是个——精明强干的战士。他们本想原路返回.绕过峡谷,但我们给出了一个不要那么做的理由。一次犯错的机会。”
“我们本该替你把贾德人都杀了,对吧?”塔里夫苦涩地说,“很抱歉我们没能做到。”
亚夏人笑着摇了摇头,“算不上失败。他们都受过严格训练,而且装备精良。你们差点就成功了,不是吗?自打出发的那一刻起,你就知道这是场赌博。”
所有人都没做声,隘口中一片沉寂。
“你是谁?”塔里夫眯起眼睛盯着那两个人,“你们俩是谁?”风势渐强,峡谷中非常寒冷。
“请原谅,”没留胡须的亚夏人甩镫离鞍下马,“我很荣幸能与您相见。自打我降生以来,塔里夫·伊本·哈桑的威名就一直在半岛传扬。您便是勇气和胆识的代名词。我叫阿马尔·伊本·哈兰,前卡塔达臣属,如今为拉寇萨效力。”
他说完鞠了—躬。
伊达觉得自己的下巴都快掉下来了,连忙把嘴闭上,毫不掩饰地盯着那人。这就是……这就是杀死最后—任哈里发的男人!卡塔达的呵玛力克也刚刚死在他的手里!
“我明白了,”他父亲轻声说道,脸上露出若有所思的表情,“很多问题得到了解答。你知道吗?亚巴斯特罗附近的村镇有很多人因你而死。”
“在阿玛力克四处搜捕我的时候?我的确听说过那件事,还请您宽恕。但卡塔达王这样做不是我出的主意,也许您能体谅。”
“所以你才杀了他,当然。我能问问你的同伴是谁吗?是谁带领这支队伍?”
贾德人已经摘下头盔,夹在胳膊底下,满头浓密棕发蓬乱不堪。他没有下马。
“瓦雷多的罗德里格·贝尔蒙特。”那人说道。
伊达突然觉得脚下坚实的地面有些摇晃,好似发生了地震。这个男人,这个罗德里格,多年来始终被瓦祭们在神庙中诅咒,他被称作阿拉桑之鞭,而且如果这些骑兵是他的部属……
“更多的问题,”伊达的父亲面色凝重地说,“得到了解答。”虽然脑袋和衣袍上沾满血污,但塔里夫·伊本·哈桑此刻显得庄重威严,异常镇定。
“你们随便哪个人就足够对付我了,”他低声说,“倘若我今天难逃失败和死亡的命运,至少日后人们提起塔里夫·伊本·哈桑时,会说是两个国家的最强者联手击败了他。”
“而且他们都不会夸口说自己比你强。”
伊达心想,这个伊本·哈兰很会说话。但婕聪氲娇ㄋ锶耸歉鍪耍以谄渌矶嘤忻嬉捕己苡幸惶住?
“你不会死在此地,”罗德里格·贝尔蒙特接口道,“除非你坚持要死。”伊达盯着贾德人,嘴巴闭得严严实实。
“那是不可能的,”伊达的父亲愤愤不平地说,“我年事已高,身体虚弱,但还没有厌倦生命。我厌倦的是故再玄虚的勾当。既然你们不准备把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