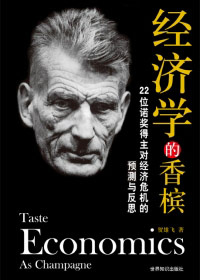遗传学的先驱摩尔根评传-第14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花过多时间去追求技术设备的完善。”
实验室的设备也是廉价品。摩尔根对公用经费之节约简直近于吝啬,这与他用自己的钱那种大手大脚的作风适成对照。不但装果蝇的容器多是代用品,就是研究用的设备也是临时凑合。后来为实验室购置的一些仪器,往往是经历了这位老板的一再反对才买成的。经过多久,手柄放大镜才换成了简易显微镜,而显微镜上面的挡光板是临时用罐头铁皮做成的,遇上屋顶漏雨,就在地板上摆几个水桶。冬天因怕果蝇受冻,才让卡尔文·布里奇斯这位能工巧匠做了一个简易恒温箱。摩尔根的实验使果蝇这小东西驰名远近,四面八方都来索取果蝇原种。摩尔根大大方方地把这些东西送给别人,而且分文不取。但他预计到他对哥伦比亚大学的东西如此慷慨处理必定会得到应有的回报。他在向威斯康星大学的科尔要原种鸽的信中这样写道:“科尔,这些鸽子我不打算付钱,也不会付运费。全世界谁向我要果蝇我都给,而且邮票也没有让人买一张。所以,请你直接把鸽子运来。摩尔根。”
饲养果蝇也花钱不多,头一年每天只花一角钱饲料费。有一天傍晚,谢默霍恩大楼旁边的体育馆失火,摩尔根的果蝇眼看就要完蛋。他冒着冬夜的严寒从家里跑出去。马拉消防车的水龙直冲着谢默霍恩大楼喷水,以免火势蔓延。有些窗户的铁架已开始熔化,而饲养的果蝇就在不远的地方。警察在现场设了警戒线,不许老百姓通过。但摩尔根说服了警察。他一口气冲过六层楼梯,到了顶楼的蝇室。大楼内的温度高得使人透不过气,他不可能把这些小小的容器一个个搬下楼去,但他终于设法把它们搬至大楼内远离火场的一边。这时他才站在人行道上观看,直到体育馆的大火被扑灭为止。谢天谢地,火灾没有扩展开来,果蝇平安无事。
秩序混乱,环境肮脏是这间蝇室的典型特征,但严格而艰苦的研究却在里面静静地进行着。摩尔根站在他那乱七八糟、堆满信札的工作台前通过一个珠宝商用的目镜数着果蝇。信件堆得太高时,他往往把它推到旁边一个学生的工作台上,而一等老板走开,这学生又把它们推回原处——师生大打拉锯战,直到有人代替摩尔根作出主张,把这些信件(有时还没有复信)统统扔进垃圾桶里。
摩尔根的工作台之不成体统还不止于此。同他一道工作的人大多数把死蝇丢进一个大家称之为“停尸房”的油瓶里。而摩尔根干脆用他那瓷计数板把果蝇压烂了事,使这计数板经常长满了霉。有时,研究生的家属(家属常常能找到一份照料果蝇的工作)会提心吊胆地把这位大人物的计数板上已经半干的果蝇给冲洗掉,但他看不惯这干净得发亮的瓷板,于是,第二天更加用劲把果蝇压死在上面。
毫无疑问,摩尔根喜欢的就是这种实验室。他这人天生不爱整洁,也喜欢闹点小淘气,逗着别人玩。他性格古怪,不怕别人非议,有时没找到皮带,就在裤子上扎一根绳子;有时来上班,穿的上衣钮扣全脱光了。还有一次,他发现衬衫上有个大洞,就请办公室里的人拿张白纸给糊上。所以,摩尔根不只一次被别人误认为是勤杂工。不过,即使在他最不修边幅的时候,他仍有一种优雅的气质。
摩尔根和他的合作者在《孟德尔遗传之机制》一书中阐明染色体是遗传的物质基础、基因是染色体的组成部分,在染色体上呈直线排列。也许可以说,该书的第一版(1915年)已经对摩尔根本人为遗传学作出的最重要的贡献作了总结,但在以后的十年中,他继续作为这一集体的核心,推动着哥伦比亚大学许多研究课题的前进。
接着他们又有了许许多多新发现。摩尔根和他的同事认识到反常的性别比例可以解释为伴性致死基因的结果。雄性后代中有一半接受的不是使它们带白眼性状的基因,而是接受了一个致死基因,于是,存活的果蝇中雄、雌比例为1:2。他们还发现,在染色体上的任一位点都可能随机发生互换、但在互换的位点附近却不大可能发生另一次互换。这种现象,他们称之为“干扰”。另外,他们又发现,雄果蝇决无互换发生。布里奇斯证明,互换的频率随母体年龄而有变化。他发现的“不分离现象”是这个集体初期工作中最有影响的成就,对当时还怀疑染色体假说的人很有说服力。所谓“不分离现象”,指的是一对染色体在减数分裂时没有分开,导致子细胞染色体组反常,染色体数目不是多了,就是少了。这一方面的研究为发现具有不同染色体数的果蝇创造了条件。比如有的只有7条染色体(2n…1),有的有9条(2n+1)甚至10条(2n+2)。对于8条染色体的果蝇,用XX和XY未解释雌雄的区别是合适的,但对于染色体数不是8的果蝇,这种解释就得加以修正。布里奇斯于是提出了他的性别平衡论①。按照这个假说,决定雄性的因子并不是Y染色体。设有2对常染色体(即性染色体以外的其它染色体),有一个X,不论有没有一个Y,是雄性;有两个X,不论有无Y,是雌性;有3个X,不论有没有Y,是超雌。没有3对常染色体,有一个X,是超雄,两个X,是中间性;3个X,是雌性;4个X,是超雌。
关于性别的决定,我们目前的看法主要来源于哥伦比亚大学时期的研究。染色体成对的生物中,哺乳动物、线虫、软体动物、棘皮动物、大多数节肢动物以及雌雄异株植物,雄性为异配子性,即XY:而鳞翅目昆虫和蛾类、大多数爬行动物、原始的毛翅目昆虫、某些两栖动物、某些鱼类、某些桡足亚纲动物以及大概所有的鸟类,雌性为异配子性。鱼类中多半无染色体性决定机制。有些物种,至今仍无法确定其性别是如何决定的。事实上,人类性别问题,直到1960年才有了定论:XY是男性,XX是女性,只有一个X而无Y产生出不育女性,只有一个Y而无X则不能成活。
斯特蒂文特也作出了几项重大贡献,染色体图只是其中最早的一项。是他提出了“复等位基因”这一解释,是他推测出有“染色体倒位现象”存在,即染色体的一片断裂开来,颠倒了180度再接回去。既然他在巨型带状唾腺染色体发现之前十五年就预测出倒位现象,他这一成就足可同约翰·库奇·亚当斯对海王星的预测媲美。亚当斯于1843年预测在天王星之外还有一颗行星,三年后人们果然观测到了海王星。
摩尔根在学生们的记忆中永远是个快活的人。他从事的工作,无论是享誉全球的果蝇研究,还是其他人谁也摸不透的实验,都是他自己最为爱好的。比如,他曾经用螃蟹做实验,一只螃蟹不断爬动,背上粘着另一只蟹,而在两蟹之间放上一小片镭。这种实验的目的何在,谁也弄不清楚。
这一段时间,即使他已戏剧性地转变为一名孟德尔的信徒,他仍然经常回过头去搞一些原来的课题。其中之一是环境对生物的遗传有没有可能起决定作用。他不时发表文章,举出一些生物在逆境中违背孟德尔定律的新奇例子,使人不由得感到染色体理论使他联想起先成说,而先成说是他一心想批驳的,他列举过果蝇
①1923年,摩尔根在给一位从前的学生、现在的朋友的信中谈到了平衡论的问题。这封信表现出果蝇实验室中是如何友好争论的,也表现出摩尔根一贯不肯轻易把事实拔高为理论的态度。他在信中说:“我完全赞成批评平衡论论据不充分的意见,而布里奇斯对这个理论是过分喜欢了。如果对那种或那些有关的‘单位’我们不能赋予客观的价值,那么,这个理论无论现在或将来都不过是杜撰。这也许会是真的,也许从一定意义上来讲是真的,但这个‘理论’告诉我们的还仅仅限于事实本身。我从一开始就这样提醒布里奇斯,但一点作甩也没有。”
的变型腹突变是受食物含水量的影响,而下肢增殖和残翅变异是受温度的影响。他还继续搞胚胎学研究,特别是研究玻璃海鞘的自体不孕和招潮的螯为什么一大一小。他又研究科尔送他的扇尾鸽的尾羽数目的遗传以及鸡和招潮第二性征产生的机制。
摩尔根继续在哥伦比亚大学开设研究生课程,不过他对教学工作的态度并没有改变。有一次,他下课回到实验室,打个哈欠说:“对不起,我刚讲完课,便昏昏欲睡了。”他对行政管理工作照样不感兴趣。当L·C·邓恩正在考虑来不来哥伦比亚大学的时候,他对摩尔根说他担心学校里的气氛不大正常。摩尔根用几句话表明了他的态度。他说,真的,在一所较大的高等学府教书必须具备某些生物学特征,“首先你得逆向进化,生出一副外甲来,同时你还得学会离走廊远远的,因为走廊一般都通向会议室。”然后他问邓恩的办公室里是否只有一把椅子,当听说有两把时,他苦笑着摇了摇头,说:“错啦,本来只应有一把椅子,你应该在椅子上牢牢坐住”
摩尔根自己就是个在椅子上坐得住的人。整整十五年,他一直坚持在蝇室里干活,布里奇斯和斯特蒂文特也是如此,虽然蝇室的工作人员常有变动,他们三人始终是这个研究小组的核心。
自然,摩尔根尽量设法使整个小组在一起工作。不过斯特蒂文特经常强调说,“摩尔根没有指导我们的工作。这是我们果蝇实验室的特点,他干他的活,无意于建立一个在他指导下的工作小组。”但这个小组的成就以及它的共同努力的协作精神(这对摩尔根至关重要)是其他研究小组所没有的。1915年以后,摩尔根从卡内基学会得到一大笔资助来继续果蝇研究,这笔经费一直延续到他去世为止。摩尔根把这笔款项的一部分用来支付布里奇斯、斯特蒂文特以及后来的杰克·舒尔茨的薪金,让他们成为专职助理研究员。他们不仅每年夏天伴随着摩尔根一家到伍兹霍尔,而且当摩尔根享受哥伦比亚大学一年休假转到斯坦福大学从事研究时,他也带去了布里奇斯和斯特蒂文特,再加上一大帮研究生——其中也包括伊迪丝·华莱士小姐,她精心绘制了各种变异果蝇的图谱。到摩尔根离开哥伦比亚大学的时候,这两个助手的去从问题也就不言而喻了。
《孟德尔遗传之机制》一书的第四位作者H·J·马勒1920年离开哥伦比亚大学到了得克萨斯大学。他在得克萨斯经常公开批评摩尔根,说他从未给他的学生们(实际上是他的合作者们)个人的发现以应有的承认,而是把这些发现描述成好像是整个小组的集体成果。照马勒的说法,果蝇实验室研究出的那些重要的结论,并非任何时候都是摩尔根先说服了自己的学生,然后又说服了世界;恰相反,有时候是学生说服了这位持怀疑态度、有时甚至表现得冥顽不灵的摩尔根,那时他比他的任何学生更能说服全世界。
摩尔根听了很伤心,但他装出心平气和、泰然处之的样子——这是他特有的做法。1934年他给一位同事的信中写道,“马勒一贯与我们作对,不过他总是想方设法含而不露;因为我们认定他的态度是错误的,不可辩解的。我们也没计较,始终对他十分友好。”作为摩尔根和马勒双方的好朋友,莫尔夫妇认为,马勒的态度固然有错,但是可以理解。
对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