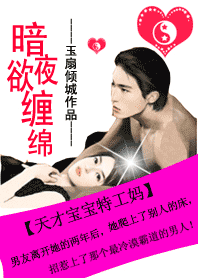零号特工-第9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湖蓝圈马回到桩前:“不是共党就别死撑!知道什么叫熬刑吗?那是要练的!”
肉票死挣,唔唔连声,湖蓝一把拽出他的堵嘴布。
肉票连忙道:“他是延安中情部的!我舅跟他熟!”
湖蓝再也不搭理肉票了,掉头看着那边的小商人:“小舅子?”
烈日炎炎,遍体鳞伤的小商人已经神志昏沉。
湖蓝飞骑而来,甩手抛出一根套马索连人带桩套上,从浮土中扯了出来。他拖着小商人在干涩的黄土上驰行。军统们玩叼羊似的追在身后,有时用长鞭子抽打,有时抬起马蹄踏了下去。跑着跑着,湖蓝冷不丁转身挥刀将套马索砍断。
小商人连着木桩又往前翻滚了一段才停下。
湖蓝下马,踱到小商人身边:“可以说了。能撑到现在,你再说不是共党也没人信了。”
小商人有气无力:“说……没不说呀。”
湖蓝问:“密码本不在你手上,在谁手上?”
小商人假痴:“啥……啥玩意?”
湖蓝皱了皱眉:“你这号人我见多了,翻个花样让我看看行不行?酒。”
果绿将一个酒袋递上。
“这酒烈得很,淋到伤口上都能消毒。”湖蓝威胁着,“杀伤口,真他妈痛。痛到脑仁儿里。”酒袋扔回给果绿。
果绿扯掉小商人的眼罩。
小商人竭力想挣开肿胀的眼睛。
“再不说就着酒给他点上!”湖蓝走开,身后传来小商人的惨叫声。
湖蓝到荫凉处,躺在早就铺好的羊皮褥子上。报务员正将便携电台支在一边收发。
一份电文递了过来,湖蓝看电文。
“鲲鹏这小子又起刺,活撑着了。”湖蓝把电文扔了,报务员捡起来烧毁。
果绿走过来,面无表情地说:“死了。”
湖蓝恼火地坐起来。
果绿连忙说:“也说了。挨烧了才说。”
湖蓝踹了他一脚:“少他妈废话!说的什么?”
“五个字。卅四,三不管。”
湖蓝瞪着果绿那张从不带表情的脸,忽然乐了:“从昨天到今天,你们跟着我跑苦了吧?”
“不苦。”
“全体睡觉,睡到这鬼日头落下去。”他又向果绿招手,“你没得睡。”
果绿过来,湖蓝跟他附耳,然后倒头就睡。
果绿上马而去。
14
油灯的光在晃动,零的嘴被人扳开,粥倒进零的嘴里。那点流食在零的咽喉里咕噜地响了一阵,才慢慢通过他的咽喉。零干裂的嘴唇开始嚅动,于是那个扶着零的人也将他放回铺上。零睁开了眼睛,先茫然地在那一点油灯光上找回了目光的焦点,然后看着救了他的那个人。
阿手那张毫无特点的脸看着他:“你晕在我店门口了。”
零费力地想了想:“谢谢。”
阿手更靠近了一点:“你要住店吗?”
零愕然地看着他。
“住店吗?”
零在愕然中点了点头。
“先交钱。”
零下意识地将手伸进了口袋,然后,又从完全通了底的口袋伸了出来——他的衣服可是每一块都被鲲鹏们拿刀挑过了。
阿手看着那只手,零看着阿手,茫然着。
楼下,阿手的父亲在拉着原始而笨重的风箱,脸上的皱纹如荒原上密布的沟壑,他和阿手看上去有点父子相,都是一贯的爱死不活。风箱嘎嘎地响,火苗嘶嘶地冒。阿手的父亲心不在焉地听着卅四叫嚣:“这叫白日行劫恶丐强化!鸡蛋五角大洋一个?这是公鸡下的蛋?你知道五角大洋在延安可以买到什么?”卅四比出一个至少跟驼鸟差不多大的东西:“这么大的鸡两只!还都是生蛋母鸡!”
阿手父亲不死不活地说:“那是延安嘛。”
“那可是赤匪盘踞的地方!这是国民政府的地方,是乐土!乐土!”
“乐土东西就贵嘛。”
卅四愤愤地说:“我只会给你边币。”
“边币就是纸嘛。”
外边蹄声嘚嘚,正准备大吵大闹的卅四从门缝里看去。街上,刚巡视回来的鲲鹏正和他的手下策马过路,进了对面的店,也就是隔着门板给了卅四一枪的店。
阿手父拉着风箱,这老头除了正在鼓风的火苗几乎从来不看什么。
卅四摸了摸险些被一枪洞穿的额头无奈地说:“好吧,我给你国币。”
老头依然不死不活的德性:“擦屁股纸嘛。”
卅四又惊又怒,又怒又急:“说这种大逆不道的话!我拿你送官法办!”
“没有法的,这里枪就是法嘛。不会办的,自己人嘛。”
卅四深觉受辱:“谁跟你自己人!”
“不是说你嘛。我和官是自己人嘛,每星期三都交太平税嘛。”
卅四愣住,顿失气势地坐下。
“不给银元就不叫给钱嘛,不给钱就不住店嘛,不住店就出去嘛。”
“给我点盐。”卅四怒了,他忽然想明白了似的又问,“盐也要钱?”
“盐比蛋贵嘛。”
“不要了。”卅四剥着他的连壳蛋,比面对全副武装的湖蓝时更为沮丧。
阿手和零在楼上一坐一立地相对,隔着一层楼板,楼下的声音清晰地传来。楼下沉默了,他们也大眼对着小眼。
零说:“我没钱。没银元,没国币,连边币都丢了。”
阿手看着零的手,零的手指上戴着一只古旧的戒指。
“这个不行。我妈就留给我这一件东西。”零自觉地站了起来,捞起自己的破烂,尽管还是在打晃。
“你喝了粥,你睡了客房的床,你花钱了。”
零愤怒而茫然地看着对方。一个利欲熏心的小百姓,贪婪但是气馁,比他扮演的李文鼎更加懦弱。零决定不管不顾地走。
“这地方过日子好难,每粒米每滴水都花钱的,你吃一口,我们就少吃一口。”
零回头看着他。阿手很畏缩,很无助,阿手和李文鼎有一种共同的神情:茫然。零将手上的戒指撸了下来,塞给他,然后掉头就走。将到楼梯口,外边突然一阵枪声。
一个人跛着脚从鲲鹏进去的那家店蹦了出来,几个他的同伴也跟着跑出来,到他身边护卫着。那伤了脚的家伙阴狠地看了鲲鹏一眼,带着同伴掉头走开。
“别说啥军统见天就洗了三不管,叫你们了不起的湖蓝快打来,我拿他死尸当份大礼。”鲲鹏剔着牙出来,趾高气扬地说。他人多势众,而且跟对方的短枪比起来,他这边拿的都是长火。
镇子尽头的中央军岗哨对此熟视无睹。
零蜷在一个角落,阿手熟练地蜷在一个更为保险的角落,并且拿一只枕头护着头。
在长久的静默中,零望向阿手。阿手正拿牙齿在测试那只戒指的成色。零站起身,打算离开。
阿手看也不看地说:“这镇上,露天过夜的外人还没有活过天亮的。”
零看他一眼,继续开步。他没有住店的钱。
“这东西值钱。折去你刚花的钱,还能住到明天。”他看着零讶然的表情说,“我们做生意不骗人。”
零有点感激。
“大车铺一晚,饭钱另算。”阿手又咬了咬戒指,“你还有没有?人总要吃饭的。”
零摇头,然后看着桌上那碗曾用来喂他的粥,还剩一多半:“这个我花钱了?”
“嗯哪。”
零拿起那碗粥一口喝尽,以抵挡往下必然的饥饿。他那点感激迅速被挥发殆尽。
简陋肮脏的大车铺,零蜷在一角,早已睡着。
铺上还睡了其他的几个,鼾声如雷,在这样的光线下根本不见其人。
唯一一个坐卧不宁的是睡在另一角的卅四,一会儿起来抓着虱子,一会儿起来用衣服包上头,以挡铺上熏人的恶臭。
15
三不管小镇尽头的兵营,带刺的铁丝门打开了一条缝,放出一队巡逻兵便立刻关上。三不管的一天开始了。
巡逻队用一种小心翼翼的步子直穿三不管,像是踩在街心一条不存在的钢丝之上,谦卑地迈着步子,尽可能地低垂着眼皮。
一条百业萧条的街,阿手的大车店和对面鲲鹏所居的酒店是全镇唯一存在的商业,巡逻队脚下踩的那条中线似乎把镇子分成了两半。人们从屋里出来,只沿着墙根子行动着,绝对无人横穿街道,那是军统和中统间不可逾越的鸿沟。随着更多的人从屋里出来,中间的街道也更像一个两军对峙的战场。
巡逻队像是镇上人的开工哨,而镇上人一天的业务便是晒太阳和拆枪擦枪。步枪、骑枪,比比皆是的手枪、刀具。这里的人们毫不避讳让人看见这些让正规军也显得逊色的家伙,更不避讳让对街看到这边的横眉冷对,仿佛在相互炫耀武力。
那队可怜的巡逻兵越走越是发毛,强作镇静下小声地嘀咕:“班长,怎么今天就是不对啊?”
“有、有什么不对的?鬼扯!”
“长家伙多了好几倍,往常玩的多是短火呀。”巡逻兵说,“我看是真要打啊。”
班长看了看鲲鹏所拥有的那半条街,正好看见一支在擦拭中指上了他的枪口。他连忙转过头来训斥:“闭嘴!向后转。”向后转,转过来便可走回安全的军营,但班长有些发愣,来时他最后一个是最安全的,去时他第一个可是最不安全的。
卅四正从镇子尽头的阿手店里出来,几乎就在巡逻队的身边。他清了清嗓子往地上咳吐一口,正一步三摇地想迈开步子,却突然愣住。卅四一目到底,两边街上全是林立的枪口,他立刻往店里拧回了小半个身子。
“站住!”班长冲他呵斥。
卅四又拧回小半个身子:“我是国民政府……”
班长小声地威慑:“过来!”
“国民政府教育部……”
班长的枪口已经对准了他,为了不引起那两边街的大惊小怪,是悄悄对准他:“老子是中央军!过来!”
卅四茫然地过去,立刻被班长揪到了身前,现在的班长有了一个肉盾牌:“走。”
“我是……”卅四正想开口,被枪口顶了一下,终于闭嘴,开步。
一支古怪的队伍,前边走着一个中山装、拄着杖一步一蹭的老头,后边跟着几个藏头露脸、枪口向天的中央军。
鲲鹏从他霸居的酒店里哈欠连天地出来,挥了挥手,手下拖过来一张桌子迎门放了。鲲鹏弯腰,拿起一个大家伙往桌上轰然一放。一挺捷克造ZB26,轻机关枪,现在的鲲鹏算是抢尽满街华彩。
卅四突然站住,看着鲲鹏。
鲲鹏看着卅四,拿牙签捣着牙龈。
一个笸箩往桌上一倒,满桌黄澄澄的子弹,中统们开始往弹匣里压弹。
对街的开始回屋,关门,上板,他们的家伙在那挺机枪面前是没得比的。
赢了这一回合的鲲鹏敲上一个弹匣,端起机枪,走到店门口,“哒哒哒哒哒……”他向对街虚扫了一阵,赢来了半条街手下的喝彩声。
卅四在身后又被枪捅了一下,终于犹犹豫豫再次开步,脚步也自然偏向了没枪的那边。门后清晰地传来拉栓上弹声,卅四和他古怪的尾巴们立刻偏回了中线。
军营线的铁丝门又开了条缝,放进终于成功走了个来回的巡逻队。
队伍立刻乱了,卅四被推到一边,丘八们劫后余生地钻回自己的军营。卅四拼命扒着即将关上的铁丝门缝隙:“我是国民政府教育部!国民政府……”他把一只手塞到门里,另一只手慌忙在口袋里掏着东西,掏出的不是证件而是钱。
钱塞到把门兵手上,门缝总算开大了一点,卅四忙把自己挤了进去。
卅四被带到营长面前。
卅四忙不迭地把证件、名片、延安开的路条,连同刚摘下的表一起送了上去,其卑贱与平时的嚣张完全是两个极端:“营座戎马辛苦,在下……”
“想走是吧?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