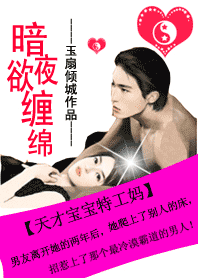零号特工-第34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卅四闭着眼睛在想什么。坐得最靠近他的是湖蓝和靛青。湖蓝忽然轻轻地咳嗽了一声,他不吸烟。在靛青的一个眼色中,所有的烟都掐掉了。也就在这时,卅四抬头开始说话:“鬼子想杀我。”
湖蓝一脸鄙夷:“闷半天就说这么句?不是新闻了。”
“你们实力强悍,刺客全军尽没,我想冰室成政要有好一阵的心痛。是的,湖蓝,一赔十的买卖,你觉得赚了。你就不想为什么?日本特工没多大本钱,凭你们上海站的实力就能清他出局,他怕你们,一直就怕,怎么忽然就甘冒奇险了?”
“为了你。”
“我又有什么价值?我只是个但望天下无事,好在西北埋骨的老头子。”
“过谦了。从你出山的第一天,就比修远还要危险。”
“只是因为劫先生习惯把任何不顺从他的人当做死敌。你们说是也不是?”
沉默。在座都是劫谋的得力手下,但正因如此他们很清楚劫谋处世为人的风格。只有湖蓝对此是毫不犹豫的:“先生说你是敌人,那你便烧成灰也还是敌人。”
“跑题了。我对日本人有什么价值?”
“密码。”
“和他们对抗的共产党武装绝大部分连电台也没有。一份可以与延安直接通话的高级密码,对他们并不如对你们来得有价值。”
“这只是你说的。”
“这不是我说的,是他们做的。”卅四开始解去一直裹在伤口上的那条围巾,然后是解开他的衣服,向面前的所有这些人袒露他的伤口。
湖蓝没说话,也没去阻止,他一直也想看看卅四到底伤得怎样。
“好吧,密码本是蛋,我就是鸡,杀了我就是鸡飞蛋打,因此你对我一路照拂,可鬼子怎么就那么急着鸡飞蛋打?”卅四袒露了他的伤口,“水银弹打的。湖蓝说这东西贵得很,也费事得很,你们也只对必杀的紧要人物才用。来杀我的人全部用的这种子弹,什么时候我老头子变得这么值钱了?”
连靛青在内的军统都把视线转开了,只有湖蓝还直视着,直视一个不忍卒视的东西,他会把这当做对自我的一种挑战。但终于连他眼里也流露出了某种恻隐之心:“盖上吧。”
卅四盖上了伤口,他看着所有人,依靠自己的痛苦,他目的的一小部分终于达到:“现在你们不觉得我在玩笑了吧?”
沉默。是的,没人会把这样重伤者的话当成玩笑,谁也不会拿自己的命这样玩笑。
卅四的脸色已经是彻底的灰败,一个伤成那样的人不可能经得起这样通宵的折腾,可现在的状况是他舍了命在折腾别人:“靛青站长,事发的当天是你在带队吧?”
“什么叫做事发呢?最近没少出事,你说的是哪次事发?”靛青是全然在抵触。
“就是袭击我们的上海联络总站,这次打响的第一枪。”卅四好脾气地提醒。
“第一枪是中统放的,也许是共党。这个问死人才知道。”
一旁的湖蓝开了口:“靛青,这种时候说话用不着负气,弄清事情对我们也没有坏处。”
靛青因此而稍改了一下态度:“我们合围的时候卢戡和北冥的人马已经打成了一团,我们进去的时候地上已经不少尸体。”
“北冥已经全军覆没了。”卅四说。
“你那意思是我说什么也死无对证?”靛青瞪着卅四,板着脸,为了一桩必须掩饰的错误,“你们共党也是一样,双方下手都够狠吧?”
“那天活下来的人就全在你们的上海站了,所以我亡命地赶过来。谁参与了那天的行动又觉得有什么不对,能否说出来?”卅四叹了口气,看着这一屋的军统,苦笑,“列位,你们在场的知道什么却又不说,我这千里外赶来的再怎么演绎也是个瞎子。”
回应他的是大大的哈欠,却因为湖蓝的面子而尽可能地无声。
“湖蓝站长,可不可以让他们抽烟醒醒神?”卅四说。
湖蓝因为这忽然公事化的称谓而愣了一下:“抽吧抽吧。”
一屋除了卅四和湖蓝外都是烟枪,顿时开始了打火声和在空中抛扔的烟卷。
卅四继续说:“列位,如果有什么阴谋,未必就是针对我们共产党,再怎么说,在上海,你们才是日本人真正忌惮的实力。换句话说,如果跟一个身在上海的日本特工说起眼中钉、肉中刺,他第一个会想到的就是你们。”
靛青点燃嘴上的香烟,一口气吸掉了小半支。每一个人都用烟塞住了嘴,沉默而用力地吸着。没人去看摇摇欲坠的卅四,尽管他说话和吐血差不多。
沉默。这是有意识的冷场。屋里的烟逐渐厚重得如要凝固。
卅四无奈地看着眼前如同固态的烟幕,军统们也许很高兴有这么道雾障可以藏起更多不想说的东西。困是不困了,但麻木和私心绝不是几支烟就能去掉的东西。
湖蓝厌恶地把烟幕扇开。沉默。
“靛青站长。”只有卅四开口,“这次来也颇有要向贵站道谢的意思。您以往向我方提供的几次情报,对我方的敌后抗战实在是帮了大忙。不论眼前这事如何,我们是一定要向重庆申谢站长的鼎助了。”
好话人人爱听,何况那意味着实在的功劳,靛青脸上也露出了难得的笑容:“好说好说。”
“我方提供的那些情报也还用得过吧?”卅四又说。
“用得过用得过。南边的几个胜仗,我方将士若是知情就该对贵党说个谢字。只是……嘿嘿。”
“胜了就好,其他都是小事。而且当前时局,站长能这样说话,实在难能可贵。”
“人敬一尺,我还一丈。在上海混了这么久,这点起码还是懂的。”
“我就想站长绝无斩尽杀绝之心。曾经的误会,也许是我方处理不当,也许是中统贪功心切。”
靛青倒摇头不迭了,反正嘴巴上的好人人人会做:“人死了我倒要嘴上积德了。你们上海卢站长,那人是不错的,要说他处理不当我是第一个不信,多少次我要跟中统的家伙白进红出都是他在说和。倒是中统的北冥,那家伙就……哈哈,嘴上积德啊……他跟老卢处得不错,可我就亲眼看着老卢死在他的手上,我是想救没救得上。”
“谢谢。”卅四看着总算开了话匣子的靛青。
靛青倒有些心虚了:“什么意思?你不信。”
“我信。谢谢是因为你也觉得应该救下卢站长,你觉得不该互相残杀,我就该说谢谢。”
湖蓝嘴角现出些不屑的笑意。
靛青挠挠头,他不习惯这样说话:“互相残杀自然是不对,可是……反正该死的不该死的都一股脑死了。”
“靛青站长说得很对,所以我来也绝不是追究责任。说句实话,我们也没有向贵方追究责任的能力。”
“那这从晚上到白天的一通絮叨要干什么?”靛青不解。
“阴谋。”
“什么阴谋?如果我们要灭你们上海剩下的几个小鱼小蟹,还需要什么阴谋?”
卅四疲倦地苦笑:“一上来我就说了,日本人的阴谋,很可能是针对你们的阴谋。靛青站长,你零零碎碎也说过那天的大概,就没觉得有什么不对的吗?”
靛青说:“中统是咎由自取。”
“除这个呢?”
“好好的上海,都被他们搞乱了。”
湖蓝终于忍不住拿手指敲了敲桌子:“靛青说点有新意的。”
卅四则在苦笑。湖蓝对诸如此类的平庸推诿只要生了厌离之心便可躲入自己的世界,卅四却得赔了老命去征服:“靛青站长,你袭击我方联络站的目的是什么?”
靛青看湖蓝一眼,看到湖蓝点头。这才说:“其一,我们确认卢站长那天会携带密码;其二,你们有一笔巨款要从上海转道。”
“不是要灭门吧?”卅四问。
靛青又一次急了:“谁他妈的要……”
湖蓝又瞪了一眼:“靛青!”
靛青住嘴,而湖蓝更不客气地转向卅四:“别再做这种明知故问的发问。你清楚得很,国难当头,现在灭共党不是什么大功,大家互相利用,说得过去罢了。”
“是的。我想靛青站长要的是不伤一人,又避免共党坐大,又可以向总部请功,而再见卢戡、北冥之类的旧识又还可以说得过去。这是上海,文明地方,动辄灭门的不是赢家是输家,是不是?”
“是的。”靛青答。
“怎么忽然就成了血流成河?我们可以退一步,死了的同志也就是死了,可你们和中统还是不共戴天。整个上海现在一团混乱,军统中统地下党,个个都自保不暇,再也不能为抗战尽力。那天发生了什么,靛青站长?”
靛青在沉默。
“靛青站长,如果能及早地发现一桩错误。它不是你的错误,是你的功劳。”
靛青于是又看湖蓝。
湖蓝说:“想起来就说。你记得,听你说话的这个人是在我们掌控之中的。”
卅四居然笑了笑:“他说得对。你可以放心。”
“刘仲达。”靛青终于说了一个名字。
湖蓝皱了皱眉:“那是什么玩意?”
卅四解释:“卢戡的助手。”
靛青说:“是中统投靠我们的特工,他多少年前就混进共党内部了。这次行动的情报全是他提供的。事发那天他说中统看出他破绽了,求我们赶快救他。”
湖蓝又开始不屑的神情:“一个长三张脸的家伙?我倒想见上一见。”
卅四笑:“我只怕他还有第四张脸。”
靛青向橙黄递了个眼色。
橙黄点了两名手下,无声地出去。
卅四将疲倦和剧痛着的身躯靠在椅背上,军统们无声地等待,湖蓝则目不转睛地看着卅四。卅四对他疲劳而宽慰地笑笑:“总算快有个结果。”
湖蓝绷着脸:“这事完了我有话问你。”
“我知道是什么。”
湖蓝狠狠瞪了他一眼。
天井里刘仲达正被橙黄几个带过来,一个军统已经抢前几步去开门。报务员抓着一张电文纸,后发而先至,抢到门前。
橙黄有点愠怒:“抢什么?”
“先生电文!”这四个字立刻让橙黄萎了下来,报务员进屋,放眼一望,全屋都是自己人,他立刻开始电文内容:“立止。”
湖蓝吼道:“住嘴!没看见有外人!”
“没了。”报务员说。
“什么意思?”靛青问。
“就是不管在做什么,立刻停止的意思。”湖蓝看着所有人,“明白了?”
有几个正在喝茶的把这话理解成放下茶杯,几个正在抽烟的忙掐灭烟头。
湖蓝气不打一处来:“都给我出去!”
困顿不堪的军统立刻蜂拥向房门。
卅四一脸的无奈和悲悯,苦笑着瘫倒在躺椅上,腹部的血渍迅速扩大。
橙黄仍和刘仲达站在天井里一个不妨事的角落。一个军统过去对橙黄附耳。橙黄向刘仲达说:“去吧。”
“嗯哪。”刘仲达唯唯诺诺,仍是那副不怕烫的死猪样。
卅四在昏沉中勉力看着刘仲达在天井里转了个弯,消失。
湖蓝目不转睛地看着卅四。暴怒地低声嘶吼:“你他妈的是在玩我!”
卅四苦笑:“这么急着和我算账,孩子。”
“你装神弄鬼让我送你到这里,根本不是为了密码!那东西就不在你身上!”
“可是为了你们,不是吗?”
湖蓝冷笑:“谁要相信来自共党的好意。”
“以后你就会知道这个死老头子是为什么来的,那时候,你可能会稍为有一点想这个死老头子。”
湖蓝还想说更狠一些的话的,但看着卅四几乎正在迅速枯竭的生命,只是将头转开。
“今天见到你的同仁,我才知道,你是劫先生唯一的希望。”